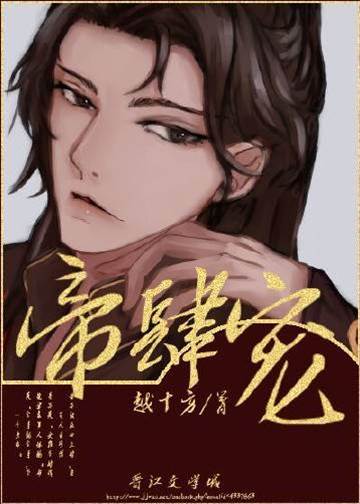《姑母撩人》 第50章 第50章
星見的屋子就在月見隔壁, 月見因屋子被人占了,無可去,便避走到這里來。甫進屋, 兩個外場與姨娘丫頭正收拾案上的殘羹, 碗碟磕磕撞撞間發出叮叮當當的脆響,好像月見著鬢鬟,響了釵環。
踅進臥房, 見星見正在墻兒聽覷,兩個眼一眨一眨的, 靈巧稽。月見笑一笑,捉往榻上坐,“有什麼好聽的?”
“聽桓大爺挨打啊!”星見一步三回頭地走來,揮揮繡絹,眼失,“他姑媽來, 好大的陣仗, 我瞧見手里還著鞭子, 可我聽了老半晌, 沒聽見打,倒似聽見哭起來, 你說怪不怪?”
窗戶上暖融融的太, 罩了半張榻, 月見搦搦腰, 就似有煙塵裊裊從上飛舞起來,“有什麼怪的,人家姑媽教養他長大,聽見考得不好, 自然又氣又傷心,哭一哭有什麼不對?你打聽別人的事兒,我倒要問問你,你這施大人怎麼近些時見來了?可別是你奉承得不好,得罪了他?他也是位揮金如土的爽快爺,你上點子心才好。”
“誰曉得他的?”星見掃掃,不以為意,“我上回問他,他只說在家用功,沒功夫往外跑。他沒功夫往外跑,桓大爺卻有功夫,見天往咱們這里來,這朋友兩個,倒似唱反調一般。”
月見是風月中人,如何不懂?如今猜想,這奚桓必定是日日放縱,故意引這“綢襖”來管一管他,他好趁機與人互通心意。猜定了,面上不顯,舉盅吃茶,笑眼瞧星見鬼鬼祟祟地又側耳往那墻聽。
倏聞“噼里啪啦”呼啦啦連著好幾聲,冷冰冰跌碎了些什麼,將星見的耳朵震了震。
是打了全套的鈞窯青釉茶,花綢留心細數,一只六棱角的壺,配的六只纏枝紋斗笠盅,脆了滿地。奚桓的灰靴就在滿地碎瓷片里怒氣沖沖地游來游去,腳后跟嵌的墨翠投出忽綠忽黑的點,匆匆從這塊碎瓷片,到那塊碎瓷片。
Advertisement
花綢暗里正點算得賠人多錢,冷不防“啪”一聲,奚桓拍在案上,恨得兩眼通紅,咬得腮角發。花綢以為他要像匹狼一樣怒嗥,誰知他卻絞著滿眼的歪出白森森的尖牙笑了笑,把那個名字在齒間磨了磨,“單煜晗……”
“你別沖,”花綢忙拽他坐下,臉上淚漬已干,空留淺淺的脂痕,殘破的,地下白皙的皮卻勢如一場新生,出彩,“你殿試還沒過呢,別惹出事來,給你爹添麻煩。”
香霧沉沉,太也有些沉沉的了。奚桓對眼瞧著,見哭得頭發也有些蓬的,便抬手將幾縷發絞發髻里,“你放心,我曉得道理。”奚桓點點頭,又出手將擱在案上的手握住,“事急不得,我只是急你在單家,終歸不好。”
“什麼不好,”花綢眨眨眼,腮微鼓,有些僝僽之,“是我與單煜晗,有了夫妻之實,不清白了,所以不好?”
奚桓忙瞪來一眼,恨不能指天發誓的狀,“我要是在意這個,就天打雷劈,殛殺我在這里!”
說罷,語輕聲,眼憐將著。“我只是恐怕你在單家過得不好,倘或你過得樂呵呵的,我也就罷了,什麼都忍得。可你這一堆眼淚,不知是忍了多久才忍到今日來哭的,哭得我心也碎了。我得想個法子,先將你接回家去住,過后,再慢慢打算。”
太折著花綢睫畔的淚,急迫地閃一閃,“你別犯傻,我既然嫁了人,長輩在,丈夫在,就沒有回娘家久住的道理。別說久住,就是外頭也要說,嫁出去的姑娘,時常往娘家去,不統。我如今倒不怕人說,只是帶累了奚家與你姑,只恐人說你們家里依勢仗貴,把嫁出去的姑娘又占著不放。我看單煜晗如今與我撕破臉,大約是不會顧忌你爹了,這事,他占理,要是告到順天府,你爹你姑都要纏上司。”
Advertisement
奚桓鼻翼輕輕一,哼出個極為不恥的笑來,“你道他如今為何沒有了顧忌?我告訴你吧,只因戶部有個缺,爹沒給他,他心知就是與咱們做了親戚,爹也不會徇私賣他這個面子,他還有什麼可顧忌的?就是如此,我才要把你接回家來,一則,他哪日要是跟你手,我又看不見,護不了你;二則,他這樣攀權附勢的人,終有一日,會與潘家父子同落,若是到時候牽連了你,就晚了;三則,爹與潘家父子如今已是在打擂臺了,單煜晗又有潘家父子有勾結,若你在他手上,只怕他脅你來要挾。因此你越早歸家越好。”
“說得輕便,”花綢將手蜷在他掌心里,撇撇角,“如今他家太太對我出門屢生怨言,說好婦人家不該時常外出,偏偏我三五夕往外跑,不是回家就是訪友。今兒我往這里來,聽見,三攔五阻,罵了我好一頓。我想來也理虧,的確不該往這里來的。何況如今要說回家住,更不能答應。”
“既不該往這里來,如何又來了呢?”奚桓明知故問地眨眨眼,將杌凳往跟前拽一拽,握下的手來,眼將人瞅著。
“你還好意思問我來?”花綢隨手握起案上的竹鞭子拍一拍,把臉板了,眉稍掛起來,“我還沒問你,怎麼就考了個第二十名?你的文章我是知道的,再不濟,也不至于此,想來是你考試不用心的緣故!我那日就說,考前一日,還吃得醉醺醺的,下了場,那腦子自然就不清醒。我說你,你還不當回事!”
說話間,那睫上掛的點水星被悉數震落下來,被斜照返,落到他心上。他把腦袋湊過去,沒皮沒臉地笑一笑,“我算準了你今兒就得來,不枉我做文章時故意錯寫了兩個字。”
Advertisement
“什麼意思?”花綢杏眼圓睜,珠遏月,“你是故意考得這樣的?”
奚桓把腦袋在眼皮子地下搖搖,又點點,弄得人糊涂了,方笑起來,“誰你心狠得很,又說要嫁人,嫁了人也不理我,真格擺出姑媽的架子來,我心里十分沒了主意,我才想著試一試你心不心疼我,若還心疼我,我就咬死了不松,隨他世道如何禮教怎樣,只要你與我一條心,總會有法子。”
“若我不來呢?”
“若你不來……”奚桓把腦袋低落半合兒,倏地笑嘻嘻抬起來,“那我就再想想別的法子。”
花綢他逗弄一笑,笑過后,又把臉耷下來,“你拿自個兒的前途做堵,里頭才子云云眾多,你努力些也是命運造化險登科,何況你故意不努力。倘或落了第,又等三年,哪里哭去?手來,真是活該要打你!”
說著執起竹鞭,在手上掰得彎一彎。奚桓佯作驚恐,把濃眉大眼得如臨大敵,踞蹐著出手去。花綢一手捉住他幾個指節,一手揮鞭,打得“啪”的響亮一聲,倒把自己嚇一跳。
忙擱下鞭子來,一他的掌心細看,見頃刻便起了一條紅紅的細印子,自己又心疼,“你怎的不曉得躲?人打你,你就白著?”
奚桓覺著手心里的疼已幾個指頭了,歪著臉看,反問:“你小時候也打我,怎麼從前不心疼,如今倒心疼起來了?”
問得花綢蛾眉半蹙,低回婉轉間,流風,“小孩子嘛,打打不妨事,你大了還打你,傷你的面。”
“原來你拿個鞭子是來嚇唬我的。”奚桓取笑取笑,花綢作勢要認真打,陡地被他反撳了手,摁在膝上,俯過臉來親在上,“我親親你,行不行?”
Advertisement
這一個親都親了,還問。那一個也是多此一舉地斜轉秋波,往簾子外頭窺一眼,“不好得,在人家家里。”
奚桓也怕人闖進來,便翛然地揮揮袖,“那就不親了,回家再親。”話如此說,卻倏地又摁下去輕啄了一口,退開了腦袋,腳尖得意地將地上的碎瓷片掃一掃。
叮叮當當地像花綢竊細的笑聲,失而復得的高興蔓延在臉上,如胭脂淡掃,紅杏枝頭籠曉月。朝滿地碎片脧一眼,惋惜輕嘆,“瞧,把人家的東西都砸了,不知要賠多銀子。”
“滿破二三十兩,不值什麼的。”奚桓左右撇一眼,腳尖掃出一條道,拉著往外頭榻上坐,“既然來了,吃盅茶歇一歇,我一會兒送你回單家。”
花綢對面坐定,四下里細細打量一番,連連咂舌,“我倒是平生第一回往這地方來,恐怕此生也就這一回了,與咱們的閨閣繡房倒是沒兩樣,只是姑娘呢,怎麼不見?”
奚桓卻在想事,倏地被問回神來,“大約躲到外頭去了吧,一會兒我請們來唱個曲兒你聽。”說著,他挪坐到邊去,“我有個主意能先將你安安穩穩接回家,還單家沒話說,只是你恐怕要點苦,可忍得?”
頭發,掬出一抹盈盈的目,亮晶晶地著他笑一笑,“什麼主意?你且說來聽聽。”
他附耳過去嘀咕一陣,但見花綢的笑寸寸盛開,往他膝上狠狠一拍,“好!這個主意好,這點子苦我吃得,又沒什麼要。”
“那你過幾日,就按我說的做,只是千萬小心,起了疹子千萬忍著別撓它,仔細日后留了疤,實在不得,就用蜂抹一抹,啊。等回家,三五日咱們就治好了,往后的事,咱們再另想法子。”
花綢抬眼見其蔥倩湑湑的眼,有些莫名安心,知道他說到就能做到,就是在陷囹圄,他也能將拉拽出來。來時的一點鶻突與不安,頃刻在他的笑容里湮滅。
趁著時候尚早,奚桓又請回來月見云見星見三人,吩咐了酒菜,擺得滿當當的油肚、鮮蝦、燉得爛的豬、蒸得白馥馥的鮮魚、另四樣時蔬,其名曰先補償花綢將之苦,關起門來,請三位執琴亮歌與花綢取樂。
花綢將姑娘們細瞧一遍,見那位月見生得海棠扶春,飛燕神,不由將多窺兩眼,又見其下也生了顆小痣,心里倏地有些明白了,只把奚桓暗里掐一掐。
歡歡喜喜鬧了個把時辰,奚桓又與月見招呼,“請將這里的賬清一清,拿來我結銀子,另有上回許下你的頭面首飾,我現使北果往鋪子里定下,請你到日子自個兒去取。”
見他這架勢,像是日后不大肯來了一般,那月見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兒,癟下臉來,“不過是說笑幾句,不敢多要你什麼,你肯來走,就是捧我的場面了。”
“我大約沒空閑……”
奚桓正說呢,花綢見他要傷人心,忙接過話去,“肯來的,往后場面應酬,多請姑娘照顧。”
月見這才有些高興起來,端端正正起朝花綢福致謝,眾人又說笑幾句,便散了局。趁著日近崦嵫,奚桓騎馬送花綢回單家,門前使北果騎馬往金鋪子里去開銷應承的東西。
且說北果往金鋪里來,照月見說下的樣子,定下了一支分心,兩個手鐲并兩顆戒指,付了定錢,往門口出來,偏巧在隔壁裁料子鋪門口瞧見個影子,十分眼,像是施兆庵,卻穿著件苧麻布直裰,頭上也未佩笄戴冠,單用條破麻帶子纏髻。
北果瞧著實在又不像,因此后頭歪著腦袋窺兩眼,疑慮半晌,終沒敢喊。
那人前頭抱著裁裳的板尺,扎著幾塊零碎布料樣子,穿著素麻衫,套棉布鞋,卻難掩宋玉之姿,朗月之,不是施兆庵是誰?
這施兆庵不知才往哪里應酬出來,臉上還有些酒酲輕微,鉆進織霞鋪里換了平頭裳,拿了裁剪的一應家伙事,雙腳走到盧家角門上時,酒已散盡。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8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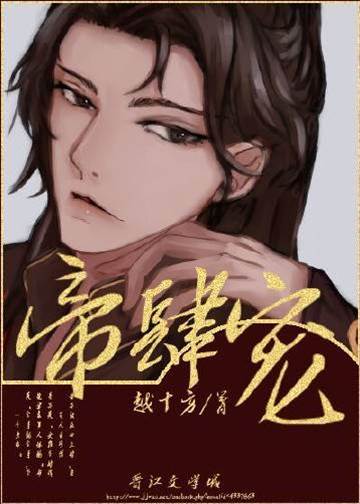
帝肆寵(臣妻)
從軍六年渺無音訊的夫君霍岐突然回來了,還從無名小卒一躍成為戰功赫赫的開國將軍。姜肆以為自己終于苦盡甘來,帶著孩子隨他入京。到了京城才知道,將軍府上已有一位將軍夫人。將軍夫人溫良淑婉,戰場上救了霍岐一命,還是當今尚書府的千金,與現在的霍岐正當…
28.8萬字8 27151 -
完結286 章

韶華為君嫁
感謝膩! 上輩子費盡心機,操勞一世,也沒落著一句讚美! 年紀輕輕就赴了黃泉,沒有怨恨,只有悔恨,為何要為你委屈自己,若能再來一世,一定要變成你喜歡的樣子,然後……不喜歡你! 看文指南:1、女主上輩子嫁過人,這輩子是純潔的。 雷者自帶避雷針。 2、男主的話,按照花叔的尿性,應該是純潔的,不過還沒想好,等想好了再說。 3、女主開金手指,就是重生女的預知吧。 4、這是鐵律:本文蘇爽白,不要過分期待作者的智商上線。 一切為了劇情服務! 5、依舊暫留。 6、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花叔愛你棉~~~這是花叔心中永遠不變的第一口號! 群麼一個! 公告:時三更+,花叔的文一般不會很長,兩三個月寫完,全本看完大概也就十幾二十塊錢,花叔日更六千+,沒日沒夜的寫,可是親們每個月平均下來就只要花幾塊錢,所以懇請大家支持正版,不要為了那幾塊錢去看盜版,給花叔吃上一頓肉,在此群謝一個,麼麼噠! 花叔囧文專欄,歡迎收藏:
85.4萬字8.18 18277 -
完結487 章

隨身醫療系統:醫妃權傾天下
又名:殺手毒醫王妃,帶著炸藥和手槍穿越【女主特工殺手、有仇必報、】+【雙潔、王爺霸甜寵】+【穿越、空間、醫術、權謀】+【熱血、獨立】現代特工女殺手帶著炸藥和手槍穿越至古代,有醫療空間,醫毒雙絕,又美又颯,遇到霸氣冷面傲嬌王爺,成了冷面王爺心尖甜寵。看冷面王爺虐妻一時爽,如何追妻火葬場。一開始像一坨冰渣子一樣的冷面王爺,自愛上王妃后,冷面王爺變得騷包,時時向府里的人炫耀,若兒真是愛慘了本王,衣服是若兒親手給本王做的,若兒天天想著怎麼吃本王的豆腐,若兒還給本王生了兩個軟軟糯糯的小奶團蕭嵐若一個刀眼過...
88.8萬字8.18 113788 -
連載567 章

鳳掌江山
一朝重生,剛睜眼就接到夫君命人送來的休書?楚雲緋不信這個邪,抓起休書找到王爺書房,踹門而入,一巴掌打得戰王不敢還手:“還休嗎?”前世恩愛夫妻一朝反目,楚雲緋以為丈夫薄情寡義,接過休書下堂離去,為此失去了唯一的孩子,心生恨意,卻在七年間發現很多事情跟表麵上不一樣。這一世她定要揭開真相,替前世的孩子討回一個公道。
100.7萬字8.18 6367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