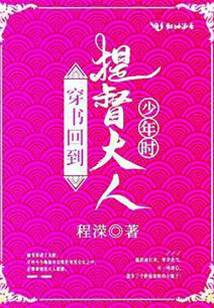《攻玉》 第11章 (1)
段文茵冷哼一聲,要是料到弟弟會陷得這樣深,當初就該做得狠絕些。
雖早就嫁去了,卻也常聽人說起萬年縣董明府的兒。董家這位二千金詩琴雙絕,是長安城有名的才。
弟弟在隴右道從軍三年,回來后在一次正元節燈會上邂逅了董二娘,年男竇初蒙,往往只在一瞬間,暗中來往大半年,弟弟對董二娘已是深種。
無意中得知此事,驚怒之下立即弟弟疏遠董二娘,怎奈弟弟被董二娘弄得五迷三道,甚至萌生了退婚的念頭。
段文茵痛心疾首:“今晚我就不該心答應你把董二娘接到紫云樓。我只當命垂危,怎料別有心腸。
“我且問你,阿娘急需六元丹,為何不堂堂正正找你幫忙?阿爺在圣人面前也算說得上話,要是你打定了主意要替弄六元丹,未必就弄不到,董二娘不來找你,反借著這個由頭三番五次去找王世子,你可細想過其中的緣故?”
段寧遠面霎時變了,段文茵譏諷一笑:“你和玉兒自小訂親,要退婚簡直難如登天,王世子份尊貴,至今未議過婚事,董二娘高自標置,心里怎能沒別的盤算?要不是王世子本不吃這一套,董二娘今晚未必會挑唆你和玉兒退親,哼,小娘子這些彎彎繞繞我可是見得多了。”
段寧遠從齒里出一句:“不是這種人。”
“不是這種人?阿爺和阿兄今晚不在邊,明知那藥不好討要,為何獨自一人跟上去?你一廂愿要救,卻連心里在想什麼都不知道!”
段寧遠臉蒼白,忽然一抖韁繩,段文茵驚道:“你要去做什麼?“
Advertisement
“去京兆府,有些話得當面問個清楚。”
“若還騙你呢?”段文茵冷笑。
段寧遠默了默:“我自有辦法說真話!”
“你給我站住!滕家現在打定主意要退親,苦于找不到你和董二娘有私的證據罷了。你這時候去找董二娘,萬一被人發現什麼,任誰都攔不住滕家了。到那時候,人人都會知道你負人在先,人人都會在背后指摘你。就算你想問個明白,為何不等滕家打消退婚的念頭之后?“
段寧遠生生勒住韁繩,即便不顧及自己,也要顧及鎮國公府的名聲。
“忘了這個董二娘吧。以前你說你不喜武將之,可是今晚你也見了玉兒,雖說遮著頭臉,但就段氣度而言,哪一點不比董二娘強?模樣阿姐也見著了,當真是百里挑一的人。”
段寧遠不耐煩聽這些:“阿姐,二娘的事不能再等了,真等施了杖刑,就算不殘也要傷上半年,趁還未定罪,今晚我必須去一趟,府尹不在,最近正好是孟芳仲當值。”
段文茵一愕,打聽得這麼明白,可見已經提前做了安排。
恨恨地想,弟弟如今泥足深陷,急需一劑猛藥,董二娘鬧這樣一出,未必不是好事,等弟弟看清了董二娘的為人,正好借此機會做個了斷。
段文茵重重嘆氣:“罷了,你非要去的話,我也攔不住你,只是去的時候萬萬要當心,切莫授人以柄。今晚過后你給我忘了這個董二娘,把心收回來,安心等著迎娶玉兒。”
段寧遠沒接話,正是風口浪尖的當口,必須想個萬全之策,他反復在心里演繹一番,終于拿定了主意:“放心,我和董二娘既不會‘面’,旁人也不知我去找過,此事不會泄出去,如何授人以柄?阿姐先回府吧,我去去就回。”
Advertisement
***
滕家的犢車駛出沒多遠,迎面遇見了杜家父子。
兩下里一打照面,車夫率先勒住韁繩:“老爺,大公子。”
父子倆各騎一馬,一路趕來已是汗若濡雨,杜裕知騎欠佳,下馬的時候子還有些搖晃。
滕玉意和杜夫人掀開車簾確認一眼,急忙下了車,走近才發現杜裕知面如金紙,杜夫人慌忙上前攙扶:“老爺不用擔心,蘭兒服了藥,已經見好了。”
杜裕知抓住杜夫人的手,吁吁正待細問,杜紹棠奔到母親跟前:“阿娘,阿姐在何?究竟出了何事,咦,玉表姐?”
杜裕知緩過了勁,也詫異道:“玉兒,你怎麼跟你姐姐和姨母在一?你信上不是說過兩日才到長安嗎?對了,蘭兒現在何,快讓我瞧一瞧。”
滕玉意撿了要的話答道:“姐姐現在車上,剛吃了藥,已經無甚大礙了。”
杜裕知神不守舍,非要上犢車親眼看過才放心,杜夫人隨他上了犢車,把今晚的事大致說了說,悵然握著兒的手道:“也算不幸中之大幸了,遇到這樣的大邪祟,還能撿回一條命。明日青云觀的小道長還會上門探視,估計再調養一回就無事了。老爺你看,蘭兒的氣益發見好了。”
杜紹棠在后頭默默看著,眼中約有淚。
滕玉意瞧著這個表弟,不到十一歲,剛曉事的年紀,量倒是夠高了,只是過于窄瘦,相貌與母親姐姐如出一轍,白明眸,生就一張清秀的瓜子臉,要不是已經束了發,乍一看會誤認小娘子。
杜紹棠小時候常跟在和表姐后頭跑,們秋千,他也秋千,們斗萱草,他提著彩篚替們摘花。
被姨父狠狠打了幾回之后,杜紹棠不敢再膩在宅了,后來進了國子監念書,書是一貫讀得好,就是不夠剛直,遇事總啼哭。
Advertisement
記得姨父曾慨嘆,姐弟兩個換一換就好了,兒簡靜,但骨子里極有主見,兒子這副黏糊糯的子,也不知何時能支撐門戶。
姨母卻說:“誰家的小郎君生來就擎天架海的?往后大了跟你出去走,多歷練歷練就好了。”
前世表姐遇害后,姨母也一頭病倒,滕玉意和杜紹棠不解帶,每日在廊下熬湯煎藥。
滕玉意因為要調查殺害表姐的兇手,背地里奔波不休,杜紹棠卻不同,失去了母親和姐姐庇護的他,好比失去了枝干的藤蔓,萬事拿不定主意,唯知以淚洗面。
前塵影事紛紛從眼前掠過,滕玉意思緒萬千,前世不喜這個怯懦的表弟,今晚見了杜紹棠,腦海中第一個浮現的卻是他年時在后追逐的小小影。
杜紹棠不知滕玉意為何發怔,許久未見了,剛面又讓玉表姐看見他哭鼻子的樣子,他怪不好意思地,了眼淚輕喚道:“玉表姐。”
滕玉意把手絹遞給杜紹棠:“喏,一。阿姐沒事,這下可以放心了。”
杜紹棠臉一紅:“我沒哭。”
滕玉意在自己臉頰上輕輕刮了刮,杜紹棠破涕而笑,杜裕知斥道:“你瞧瞧你,哪有半點須眉之氣!你阿姐不得風,你在這里做什麼,還不快下去開路。”
杜紹棠一聲不敢吭,老老實實下了車,杜夫人隔窗殷殷叮囑:“夜深了,路不好走,騎慢些不打,當心別摔著了。”
杜紹棠悶悶道:“兒子曉得了。”
杜裕知又問了幾句淳安郡王和王世子的事,捋須片刻道:“備份厚禮,擇日登門道個謝也就是了。郡王府車馬盈門,未必肯接我們的帖子,要是郡王殿下不肯見,我們也不必為了報恩一再上門。”
Advertisement
滕玉意就猜到姨父會這樣說,姨父這個人迂腐死板,最不屑與天潢貴胄往來。
其實真要細說起來,杜家百年前也是族,直到姨父祖父一代,杜家才慢慢衰敗下來。
姨父雖說繼承了祖業,但家中境況早已不比往昔,不過好在他有才名,一手詩文冠絕長安。十九歲就中了進士,不久又因考中制舉得授校書郎。
恰逢太原王氏旁系的一支要替兩個兒擇婿,王公因賞識杜裕知的才,便將長嫁給了杜裕知。
當時長安無不稱羨,年紀輕輕就了仕,娶的又是名門之,日后杜裕知必定前途無量,誰知姨父驕狂,很快就把上司同僚得罪了個遍,不久又被人尋了錯,遠遠貶謫到岳州。
一晃二十年過去,姨父越做越小,上的酸腐之氣倒是日甚一日,去年好不容易才調回長安,又因不吏部長的待見,只得了個國子監的閑職。
杜夫人知道丈夫的老病,耐心勸道:“老爺此言差矣,我們既無所圖,何妨再坦些,到時候我們自管遞我們的帖子,若是郡王殿下不見,大不了等妹夫回了長安,我們再同他一道登門。”
杜裕知端坐不語,滕玉意原以為他老人家又要發表一通高論,但或許杜裕知也知道淳安郡王是出了名的謙恭下士,末了只道:
“待我回府寫了帖子,明日就令人送到淳安郡王府,淳安郡王尚未娶妻,府中并無眷,你就不必去了,我帶著紹棠去吧。”
“如此甚妥。”
杜裕知想了想,出些許忌憚之:“至于那個王世子,我們還是招惹為妙,改日去青云觀多奉些香火,謝過他師尊清虛子道長即是。”
杜夫人哭笑不得:“全聽老爺安排。”
杜裕知便要下車:“玉兒回府后好生將歇,出了這樣的事,你阿爺想必掛念得很,明早起來給你阿爺去信報個平安,莫又托辭不寫!”
滕玉意眼下沒心與他老人家拌,耷拉著眼皮做出乖順模樣:“兒知道了。”
今晚不宵,回城這一路,到未設關隘,但畢竟路途遠,等一行人回到杜府所在的親仁坊,早已過了丑時。
滕玉意從揚州遠道而來,行囊就裝了兩大船,到長安后,滕玉意因為要救表姐一下船就往城外趕,仆從們便趁這工夫將行李送往滕府了。
下車后,滕玉意喚了婢綺云到跟前:“我今晚在姨母家住,你帶幾個人去滕府替我取些常用的件,記得別了我的小布偶。”
綺云笑,那是夫人生前親自給小娘子制的布偶,娘子五歲起就每晚抱著這布偶睡覺,若有一晚布偶不在邊,小娘子就睡不踏實。
忙道:“婢子記著呢。”
滕玉意又說:“另外傳話給大管事程伯:挑幾個手出眾的護衛,一撥穿穿常服,另幾個扮西市的販夫走卒,安排好了盡快過來回話,我有用。”
綺云一肚子疑問,卻也不敢多問,應了下去。
到了后院,杜夫人一頭照料杜庭蘭,一頭忙著安置滕玉意的茵褥:“你姐姐知道你要來,頭幾日都打點好了,寢都是現的,這幾件是你姐姐新裁的裳,你梳洗了換這個就是。”
滕玉意湊近看杜庭蘭,表姐氣已經恢復如常,手腳也漸暖。
“姐姐快要醒了,后半夜就由我陪著吧。”
“這半月你一直未曾好好歇息,今晚又一番驚嚇,如何熬得住,你自管去安歇,一切有姨母。”
滕玉意拗不過杜夫人,只得先去梳洗,浴槲里已倒上熱水了,滕玉意卻不急著沐浴,而是站在浴槲邊用帕子輕輕拭翡翠小劍。
碧螺捧著巾櫛近前:“把這寶貝給奴婢捧著吧,省得磕了了的。”
“碧螺,還記得這劍是怎麼來的嗎?”
“娘子怎麼又問這個了?”碧螺小心翼翼用巾帕包住翡翠劍,“半月前我們從揚州來長安,娘子因為染了風寒總在艙里待著,那日歇晌時,娘子說待悶了,看岸上佛寺里的梅花開得好,就說要到寺里賞花散心。下船的時候船突然晃,娘子不慎落水,救起來后娘子手中就多了這柄小劍。說起來,那日岸上的佛寺梅花出現得古怪,小娘子落水落得古怪,這柄劍更是來得古怪。”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22 章

咬定卿卿不放松
這是聰慧貌美的元小娘子,一步步征服長安第一黃金單身漢,叫他從“愛搭不理”到“日日打臉”的故事。 元賜嫻夢見自己多年后被老皇帝賜死,成了塊橋石。 醒來記起為鞋底板所支配的恐懼,她決心尋個靠山。 經某幕僚“投其所好”四字指點,元賜嫻提筆揮墨,給未來新君帝師寫了首情詩示好。 陸時卿見詩吐血三升,怒闖元府閨房。 他教她投其所好,她竟以為他好詩文? 他好的分明是……! 閱讀指南:類唐架空,切勿考據。主言情,輔朝堂。
36.4萬字8.33 22384 -
完結25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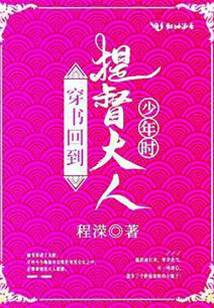
穿書回到提督大人少年時
她書穿成了女配,可憐兮兮地混在公堂的男男女女中,正等著知縣大人配婚。 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長吏配之。 按照劇情她注定是炮灰,超短命的那種。 她不認命,急切的視線在人堆裡可勁兒地扒拉,終於挖掘出他。 夭壽呦,感情這小哥哥,竟是男二! 連女主都無法覬覦的狠人! 這位爺有秀才功名在身,卻被至親算計,入宮成為殘缺不完整的太監。 他生生地熬過種種苦難,任御馬監掌印太監,最後成了人人敬畏的提督大人。 他曾顛沛流離,人人嫌惡,也曾位高權重,人人討好。 成為看盡人生百態,孑然一生的權宦。 但這都不是重點,重點是他壽終正寢! 只要她抱緊他的大腿兒,定能擺脫螞蝗般的至親,待日後做了大宦官之妻,更是吃香的喝辣的,還不用費勁巴拉的相夫教子。 小日子簡直不要太美好,撿大漏啊! 他一朝重生,再回少年時,尚未入宮,更未淨身。 眼下,他還是小三元的窮秀才,父暴斃而亡,母攜家資再嫁。 他浴血歸來,渾身戾氣,可一時善心,就多了個嬌嬌軟軟的小娘子! 說啥他這輩子也不淨身了,好好地考科舉,走舉業,給她掙個誥命夫人做,再生幾個小崽子玩玩兒……
44.7萬字8 23543 -
完結498 章
頂級綠茶的穿書攻略
萬蘇蘇,人送外號綠茶蘇,名副其實的黑綠茶一枚。她寫了一本虐文,傾盡茶藝寫出絕婊女二,不出所料,評論下都是滿滿的優美語句。她不以為恥,反以為傲。然鵝——她居然穿書了!!穿的不是女二,而是活著悲慘,死得凄慘的女主!!事已至此,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逃!可,她卻發現逃不出原劇情,難道……她只能乖乖地順著原劇情發展了嗎?開局一巴掌,裝備全靠綠茶保命攻略,且看她如何靠著一己之力反轉劇情,走上人生巔峰。宴長鳴
89.8萬字8 7026 -
完結1654 章

神醫棄妃:邪王,別纏我!
別人穿越吃香的喝辣的,蘇半夏穿越卻成了南安王府裡滿臉爛疙瘩的廢柴下堂妻。吃不飽穿不暖,一睜眼全是暗箭,投毒,刺殺!冷麵夫君不寵,白蓮花妾室陷害。蘇半夏對天怒吼。「老娘好歹是二十一世紀最牛的解毒師,怎能受你們這窩囊氣。」從此,她的目標隻有一個,誰不讓她活,她就不讓那人好過!誰知半路上卻被個狂傲男人給盯上了?那日光景正好,某人將她抵在牆角,笑意邪魅。「又逢初春,是時候該改嫁了。」 ... 《神醫棄妃:邪王,別纏我!》是小容嬤嬤精心創作的女生,微風小說網實時更新神醫棄妃:邪王,別
171萬字8 9777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