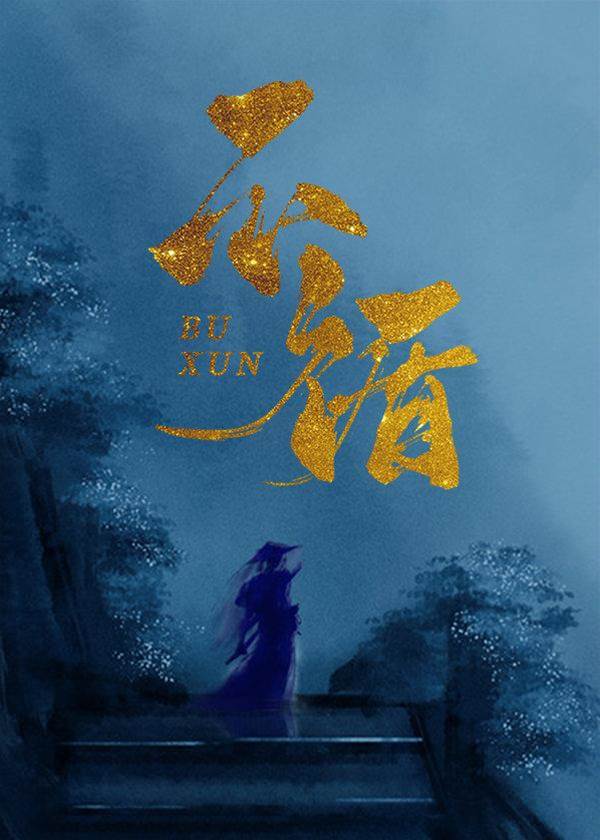《別院私逃後,瘋批權臣怒紅眼》 第46章 他的妻子,隻能是他的
裴硯忱抬步往紫藤院走。
淡聲吩咐季弘:“不必跟著。”
季弘立刻停下腳步。
紫藤院中,老夫人還未大好。
一路舟車勞頓,累又寒,子本就疲乏,這會兒又一怒,忍不住沉沉咳嗽。
裴硯忱一進來,就聽到老夫人抑的咳聲。
他踏進廳堂,接過方嬤嬤手中的溫茶,親自遞去了老夫人麵前。
“祖母。”
裴硯忱是裴家嫡長子,自小穩重過人,本就備重視,更別說三年前裴錚去世後,整個裴府,全靠裴硯忱撐起來,一步步走到如今天子腳下世家之首的高位。
對於這個嫡孫,老夫人向來是讚不絕口,倍欣自豪,更是從不曾對他有過任何冷臉。
可今日,裴硯忱手中的茶水剛遞過來,就被怒一手揮開。
茶水混合著致的茶盞,“啪”的一聲重重砸在地上。
碎瓷片瞬間四分五裂,迸濺開來。
聲音大到,廳堂外一眾婢當即烏泱泱跪了滿地。
就連後麵的方嬤嬤,都嚇了一大跳。
裴硯忱屹然不,對於老夫人的震怒,臉上沒有任何緒波。
他平靜開口,“祖母,氣大傷。”
老夫人重重拍著桌子。
怒氣劇烈在口激。
沉沉看著這個引以為傲、手段過人的嫡孫,頭一次如此盛怒。
“我問你,薑、容兩家的婚約,是不是你出手毀的?”
裴硯忱淡淡抬睫,瞳仁深著翳。
“祖母,薑、裴兩家定親在先,他們那樁親,不作數。”
Advertisement
見他現在連偽裝都不做,老夫人氣火更盛,“薑、裴兩家的婚事,早就作廢了!”
“孫兒未同意。”裴硯忱不避不讓,迎上老夫人的視線,之前他還願意遮掩幾分真實心思,現在,他連丁點都不願再遮。
“祖母,這樁婚事,我從未答應過解除,也從未應允過,將拱手讓人。”
老夫人怒目看著這個孫兒,尾音都有些抖。
“你難道忘了,薑家於裴府有恩,晚晚是恩人之,我們裴府是報恩,不是報仇!”
“晚晚不願繼續與裴家的這樁親,心悅的是容家那位公子,你不顧的意願,強行將留在邊,便是如此還恩的?”
裴硯忱側扯出幾分冷笑。
眼底無半分笑意。
他一字一句開口:
“祖母,孫兒早便說過,若非顧忌兩家恩,和容家連議親的機會都不會有,更不可能出現薑、容兩家定親這種事。”
“薑家於裴家的恩,孫兒謹記於心,先前也已按照薑姑娘想要的方式,將這份恩還清。”
“至於意——”
他慢條斯理挲過拇指上的玉扳指,眼眸沉沉,“皆是培養的,孫兒相信,日久生。”
裴硯忱這番話說得很明白。
在裴家未還清薑家恩之前,他什麽都不會做。
哪怕妒忌極了與容時箐之間的意,他也克製著自己,什麽都不去做。
眼睜睜看著他們議親、定親。
可當這份恩還完,他就沒必要再克製著親眼看著嫁與旁人了。
Advertisement
他的妻子,就該是他的。
不管什麽時候,都沒有資格讓他把自己的妻子拱手相讓。
老夫人怒火更甚。
恨不得掄著龍頭拐杖打他。
但裴硯忱卻什麽都沒再說。
囑咐了一句讓方嬤嬤細心照顧著,便徑直離開。
“近來朝中事務繁忙,孫兒還有公務在,稍後再來陪祖母說話。”
“這幾日天寒,祖母子未愈,不妨先將養子,孫兒先行告退。”
見他頭也不回離開,老夫人氣得又想咳嗽。
方嬤嬤連忙重新端了一杯茶送過來。
輕拍著老夫人的背給順氣。
老夫人重重拍了拍桌子,生氣卻又有心無力,“他現在是鐵了心了!不再偽裝,也不再遮掩,全憑著子來!”
—
碧水閣中。
裴硯忱一進來,就見薑映晚準備往外走。
他看兩眼,往廊下走去。
“去哪兒?”
薑映晚剛出來門,還沒來得及邁下臺階。
見他走來,適時停住腳步。
和他對視一剎,說:
“聽聞老夫人回來了,我想去請個安。”
他目直直落在上。
“是去請安,還是去找祖母求助?”
被說穿心思,薑映晚攥著手中帕子的力道無聲一。
確實不隻是去請安。
當初老夫人能在薑、容兩家定親那天親自出麵,就說明老夫人是讚裴、薑兩家的婚事取消的。
想從裴硯忱這裏麵麵離開是不可能了。
或者說,隻要裴硯忱不同意,別說麵離開,連走出這座府邸的機會都沒有。
Advertisement
若是想離開,為今唯一能求助的,隻有老夫人那邊。
薑映晚麵上不聲。
就連緒,都沒有任何變化。
垂了垂眼,模樣乖巧真誠。
一眼看過去,所言所行仿佛皆是真心。
“老夫人待我慈,聽聞老夫人這次子病恙始終不見好全,我隻是想去看看老夫人如何了。”
裴硯忱打量著片刻。
像是沒有看出來的蒙騙。
神如常地上前兩步,握住的手,說:
“祖母一路舟車勞頓,有些疲累,這會兒需要休息,如果想請安,待祖母休息好了再去。”
尾音落,他了腦袋。
話音一轉,又問:
“今日不再出府了,你是隨我去翠竹苑,還是我隨著你留在碧水閣?”
薑映晚皺了皺眉。
老夫人和陳氏不在府中時也就罷了,他放肆也就放肆了。
如今老夫人和陳氏都回來了,他竟還毫不收斂。
裴硯忱著腕骨側。
他作看似親。
但指骨冰冷,驟然在薑映晚腕上,冰得不自覺往後了下手。
然而不等回去,就被他一言不發地扣住。
他看著眉眼間掠起的折痕。
冷輕扯了扯,“看來是不想去翠竹苑,那就在碧水閣。”
說著,不等薑映晚拒絕,他直接出聲吩咐後麵的季弘:
“去將書房的公務抱來,晚些的安排都推了,今日不再出府。”
——他親自看著。
季弘不敢怠慢。
立刻應聲,快步跑去了翠竹苑。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563 章

丞相府的小娘子
沈梨穿越了,穿到一窮二白,剛死了老爹的沈家。上有瞎眼老母,下有三歲幼兒,沈梨成了家里唯一的頂梁柱。她擼起袖子,擺攤種菜,教書育人,不僅日子越過越紅火,就連桃花也越來越多,甚至有人上趕著給孩子做后爹。某男人怒了!向來清冷禁欲的他撒著嬌粘上去:“娘子,我才是你的夫君~”沈梨:“不,你不是,別瞎說!”某人眼神幽怨:“可是,你這個兒子,好像是我的種。”沈梨糾結:孩子親爹找上門來了,可是孩子已經給自己找好后爹了怎麼辦?
87.5萬字8 21269 -
完結16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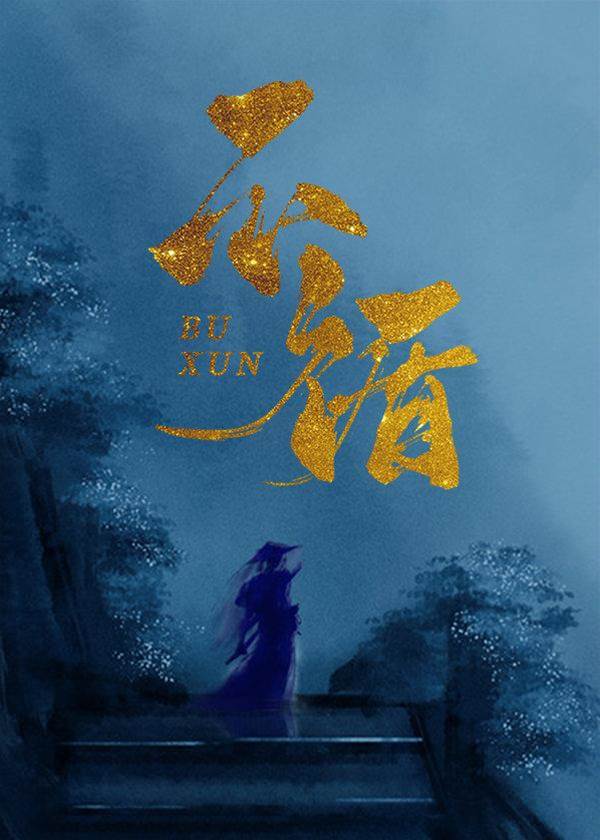
不循(重生)
邵循是英國公府的嫡長女。 父親是一品公侯,母親是世家貴女,宮裡的淑妃娘娘是她姑姑,太子之位的有力競爭者三皇子是她表哥。 人生中唯一的不足就是生母早逝,繼母不親,原本應該榮華富貴不缺,波瀾壯闊沒有的過完一輩子,誰知一場夢境打破了一切—— 邵循夢見自己的堂姑為了給兒子剷除對手,犧牲侄女的名節用以陷害風流成性的大皇子,害得自己清白盡毀,只能在鄙夷中被大皇子納為側妃。 大皇子風流成性,大皇子妃善妒惡毒,邵循醒來後生生被嚇出了一身冷汗。 誰知這夢做的太晚,該中的招已經中了,無奈之下決定拼死也不能讓噩夢成真,為了躲開大皇子,慌不擇路的她卻陰差陽錯的撞進了另一個人懷裡…… * 邵循清醒過來之後跪在地上,看著眼前繡五爪金龍的明黃色衣角,真的是欲哭無淚—— 這、這還不如大皇子呢! * 1雷點都在文案裡 2年齡差大 3請原諒男主非c,但之後保證1v1
49.3萬字8.33 50004 -
完結432 章
舔狗太纏人,王爺他又吃醋了!
前一世,柳落櫻錯將惡人當良人,落得個焚火自戕,慘死在冷宮無人收屍的下場。 重生後,她強勢逆襲! 抱緊上一世兵部尚書的大腿,虐得渣男後悔不已。 鬥惡毒伯母,虐心狠表妹,她毫不留情! 唯有在對待身份神秘的私生子二表哥時,那顆冰冷的心才會露出不一樣的柔情。 哪曾想,報完仇,大腿卻不放過她了。 洛霆:“櫻兒,這輩子,你只能是我的妻......”
76.7萬字8 9086 -
完結207 章

都說她不配,偏偏清冷權臣他超愛
【先婚后愛+古言+女主前期只想走腎、經常占男主便宜+共同成長】江照月穿書了。 穿成男配愚蠢惡毒的前妻。 原主“戰績”喜人: 虐待下人。 不敬公婆。 帶著一筆銀錢,和一個窮舉子私奔。 被賣進青樓。 得了臟病,在極其痛苦中死去。 這……這是原主的命,不是她江照月的命! 她可不管什麼劇情不劇情,該吃吃、該喝喝、該罵人罵人、該打人打人、該勾引男配就勾引男配。 一段時間后…… 下人:二奶奶是世間最好的主子。 公婆:兒媳聰慧賢良啊。 窮舉子:我從未見過這麼可怕的女人! 男配摟著她道:時辰尚早,不如你再勾我一次? 江照月:???
39.5萬字8 13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