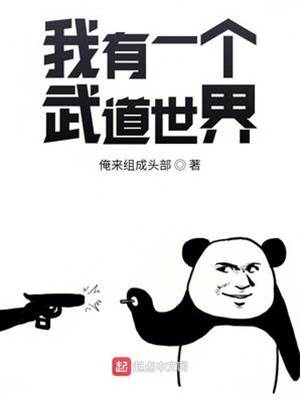《穿成超稀有雌性,被大佬們追著寵》 第361章 太快了……
“年荼。我也年荼”,將難搞的問題糊弄過去,年荼也鬆了口氣,言歸正傳,“我的記憶很,渾渾噩噩太多年,大部分事都記不得了,但醫還記得一點。”
抓起一捧藥,將裏麵的藥材按種類分幾堆,指了指其中兩堆,“就是它們二者相克,長期服用會慢中毒。”
想了想,他又補充一句,“你可以拿去信任的醫師驗證一下。”
觀察灰狼的表,覺得他應該是信了,於是趁熱打鐵,“我能看看你的傷嗎?說不定可以幫你緩解一二。”
考慮到那麽多醫都治不好,沒有把話說的太滿,誇下海口一定能治好,免得給了他希又落空。
聽見年荼提起傷,宗守淵頓時張起來。
他的表變得十分嚴肅,渾繃,似乎下意識地躲閃了一下,沉默著沒有開口。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年荼也覺到些許焦躁不安。
看來還是太過莽撞了……
的份本就可疑,傷又是敏的話題,縱使方才的胡編造灰狼姑且信了,但一聽到想看他的傷,說不定又會重新警惕起來。
道理都懂,可實在等不及了。
之前不知道有敵人,還想著從長計議,這一匣子藥卻讓萌生強烈的危機。
傷是弱點,灰狼上的毒也是弱點,隻要一天治不好,就隨時可能被想要傷害他的人抓住機會。
年荼焦慮地蹙起眉頭,“你……”
要是不信任的話,可以懂醫的心腹手下來監督。
不等把話說出口,宗守淵似是終於下定決心,咬牙點頭,“可以、給你、看。”
Advertisement
“但是、我有、一個、條件”,因為張,他說話又變得磕磕絆絆,低垂著腦袋,雙手攥拳。
年荼微微訝異,“什麽?你說。”
沒想到笨蛋灰狼還學會和談條件了,真是有進步。
不覺得灰狼會提出什麽過分的要求,非常放鬆地托腮看著他。
倒是宗守淵看上去依然張,坐立難安。
“……我的、、很嚇人、很醜”,又糾結了好一會兒,他才結結開口,“你、看了、以後,不可以、嫌棄我。”
說完這些話,似乎就耗了他所有勇氣,昔日意氣風發的宗小將軍此刻低垂著腦袋,像是等待主人審判的小狗,倘若有尾,一定已經夾了起來,不再搖晃。
年荼聽得呆住。
這也算條件???
瞧著垂頭喪氣的年輕雄,的心頭漸漸生出酸楚與難過,抬手囫圇麵前人的頭發,安陷自卑的伴。
“怎麽會嫌棄你呢?”,放緩了語氣,將灰狼摟在懷裏,像是給形順那樣,溫地他的頭發、脊背,忽而靈乍現,湊近他的耳畔,輕聲開口,“我就是因為想嫁給你,才借還魂的呀。”
“?!”,像是打了似的,宗守淵渾鬱悶的氣場陡然散去,一骨碌坐直,“真的??”
是啊!
既然都能投胎了,又為何要借還魂呢?
難道真的是因為想嫁給他??
如此一來,從第一次見麵,年年對他就格外熱的態度便有了合理的解釋——
原本的年荼不喜歡他,但是年年喜歡他。
Advertisement
這個認知一侵腦海,就再也無法清除。宗守淵激得頭腦發昏,麵紅耳赤。
年荼一邊趁機他的子,一邊半真半假地胡謅八扯,“當然是真的,你的我的正緣,是我的命定之人,所以我才舍了投胎的機會,為的就是永遠和你在一起。”
每多說一句,宗守淵的眼神便更亮起一分,全然沉浸在了這甜言語之中。
直到所有子都被扯下去,雙傳來涼颼颼的覺,他才猛然回神,臉紅得幾乎要滴出,“不、太快了……”
他們才心意相通,現在還是白日,真的要這麽快就……
“?”,年荼正俯去看他傷的右,聞言出狐疑表,抬起頭時,目剛巧從興略過,注意到那裏的狀況,一時失語,“……”
沒做什麽吧?
明明隻是安地了腦袋,了後背,說了幾句哄人的話而已,純得不得了,竟然能有如此效果。
十八歲的小雄,真是缺乏自製力。
年荼搖頭嘖嘖,憐惜地瞥了灰狼一眼,“你且先忍一忍。”
沒想到他竟然在麵前承認了自己快,暴了男人最不願意暴的缺點,心裏麵一定很自卑,很難過吧?
醫這項技能過了明路,年荼不再遮遮掩掩,抬手搭上灰狼的脈搏,靜靜分析了一會兒,疑地皺起眉頭。
把脈瞧不出病,那東西看起來也沒問題,一時竟檢查不出問題出在哪,甚至還覺得他有點憋得狠了、補過頭了,過於燥熱了一些。
“沒關係”,年荼斟酌著詞句,小心安伴,“你還年輕,不要太著急。”
Advertisement
還是覺得灰狼的不至於有什麽大問題,一定能治好的。
宗守淵不敢抬頭,聲音細若蚊蚋,“嗯……我不急。”
他才意識到年年隻是想檢查他的傷而已,是他心思不正,想的太多了。
極度的窘令他再顧不得猙獰的傷會不會被嫌棄,隻想遮掩自己控製不了的醜態。
扯過一件裳擋住,尷尬地僵了一會兒,他才漸漸緩過來,略微抬起頭,視線落在年荼的發頂。
約約的,他覺到的呼吸若有若無撲在他的上,掀起陣陣意,一路沿著脊椎骨向上,攻占他的所有神經。
宗小將軍忍不住仰起頭,神思不屬。
“你怕和尚或者道士嗎?”,他忽而沒頭沒尾地問了一句,轉移注意力。
“嗯?”,年荼正聚會神研究他的傷,被問得一愣,搖搖頭,“不怕。”
又不是真的鬼,怕什麽和尚道士?
那短暫的遲疑看在宗守淵眼中,卻像是故作鎮定說了謊話。
他張了張,想安,又覺得言語上的承諾太過單薄,安的話到了邊,沒有說出口。
年荼沒有覺察到他的異樣,也沒分出心神去思考他在想什麽。
所有的關注點都在他的傷上。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連載384 章
龍城
一個冷淡的傢伙,一個冷淡的故事。冷淡.jpg
92.3萬字8.33 7251 -
完結1432 章

無盡武裝
這里是天堂,因為這里擁有地球上擁有的一切。所有你渴望的而又得不到的,在這里都可以得到;這里是地獄,因為每個人都要在這里艱苦掙扎,然后在分不清真假的世界中醉生夢死。這里,就是無限殺戮的世界……
516.7萬字8 17563 -
完結1395 章

我的女友是喪屍
當災難真的爆發了,淩默才知道末日電影中所描繪的那種喪屍,其實和現實中的一點都不一樣…… 原本到了末世最該乾的事情就是求生,但從淩默將自己的女友從廢棄的公交車裡撿回來的那一刻起,他的人生軌跡就已經朝著完全不受控製的方向狂奔而去了。 造成這一切的原因很簡單,他的女友,變異了…… 等等,那隻夏娜,你鐮刀上挑著的好像是我的吧! 學姐!不要總是趁我不注意的時候打我啊! 還有丫頭,你這樣一直躲在旁邊偷笑真的好嗎? 最後……不要都想著咬我啊啊啊啊!!!
324.9萬字8 23661 -
完結88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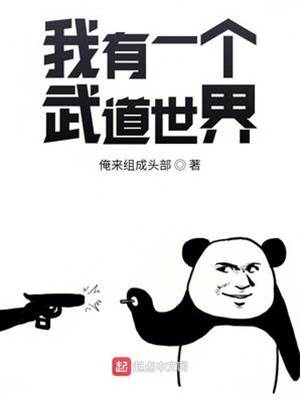
我有一個武道世界
平凡的藍星出現一個超人會怎樣? 雙穿門,唯一超凡。 小目標——硬抗核彈~
162.4萬字8 19491 -
連載2081 章

撿個首富做老公孟靜薇擎牧野
送外賣途中,孟靜薇隨手救了一人,沒成想這人竟然是瀾城首富擎牧野。他亦是商界帝王般的存在,傳聞他心狠手辣、不擇手段,眼中只有利益沒有親情。孟靜薇救他時,他許諾一個億為酬金。可當那一億元變成娶她的彩禮時,孟靜薇恍然大悟:“我只想要一億的酬金,不要你!”“你舍命相救,我擎牧野唯有以身相許才能報恩。”“憑什麼?你娶我,問過我意見嗎?”“那你愿意嫁給我嗎?”“不愿意!”
191.6萬字8 193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