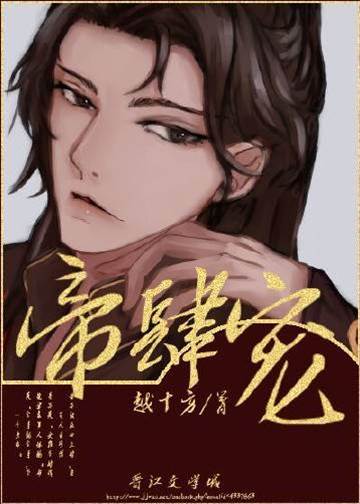《盛寵嫡妃》 第96章 她只是個賤婦罷了
第96章 只是個賤婦罷了
當方立瑾看到忠勇侯的時候便對隨從低聲道:“把這丫鬟也帶上馬車,快!”
燕兒也認出了那人似乎是忠勇侯,愣了片刻后,一咬牙便跟著那隨從快步出了長亭。
一旁的隨從道:“侯爺,那端王這個時辰請您來十里長亭?”
忠勇侯孟括也是不解,他微微點了點頭,“端王素來行事沒個章法,這一回也不知道葫蘆里賣的什麼藥?且去看看就是。”
自己如今是有求于人,只能是聽之任之了,能蓉兒進了宮到底也能更上一層樓不是?
侍衛見到亭子里淹沒在黑夜里的人影,頓時便提高了警惕,“侯爺,那亭子里有人!”
這時方立瑾聽到了聲響,便一手勾著江錦才的肩,一手仍用匕首頂著他,笑嘻嘻地拖著江錦才走出了柱子后的影。
他爽朗一笑,“江兄,我說了這夜里的十里長亭也是景不錯的,你看怎麼樣?這秋風是不是吹著清醒多了。”
江錦才只覺得那冷風往領口里灌,冷的徹骨。
他也看到了馬上的黑男人,那不是忠勇侯又是誰?
他心里一,莫非是方立瑾想對付自己才設了這個局?
不對!
他這樣做就是多此一舉了,到底是誰!
驀地,他頓覺自己的境堪憂了……
他自然不愿意自己被忠勇侯疑心什麼,于是干笑了兩聲,“呵呵,這景致……的確是不錯。”
聽到有男人說話的聲音,孟括凝神沉聲道:“什麼人在那里?”
方立瑾似乎是才看到這麼個人,吃驚地喊道:“喲……這不是忠勇侯孟大人嗎?”
孟括細細一看,這正是前幾日在李都督府的定親宴上見到的方二爺!
Advertisement
這可是李都督的乘龍快婿,自己也得給兩分薄面的。
孟括到底年長,他坐在馬上點了點頭,“原來是方家的二爺,本侯倒是不知道,方二爺有這個雅興?”
說著他掃了眼方立瑾邊的男子,那年輕男子一青,也是個面目俊朗的后生,只是瞧著卻是臉不太好看。
江錦才見他視線掃了過來,只得躬行了一禮,“拜見侯爺。”
那匕首頂著后腰,他蹙了蹙眉,心里卻是轉了好幾個彎,可就像是找不到出路,只能是站在這兒吹冷風。
方立瑾似是慨般說道:“晚輩這是同江兄來此吹一吹這長亭的涼風醒醒酒,不知侯爺怎的這麼晚來這十里長亭?要送行不?”
恐怕是有人故意為之吧?
方立瑾瞥了瞥四周,不管是誰,也沒得平白得了這便宜的說法,這便宜,自己可是盯了許久了,哪里容得下這時候失手。
孟括自然不會多說出端王來,他只似是無意般說道:“這深秋的涼風可是涼的很吶。”
方立瑾自然識趣,更何況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他微微躬道:“的確涼的很,那晚輩就先行告辭了。”
說著他又用刀抵著江錦才,江錦才只好也躬行了一禮。
方立瑾看著隨從趕來了馬車,這才快速地上了車。
燕兒躲在車廂中死死捂著,不敢發出一點兒聲響,那極薄的車簾外就是忠勇侯!若是自己被發現,這條命也就代在這里了!
馬車緩緩離開十里長亭后,附近躲藏的影閃了閃便往王府飛而去了。
等周承瑞黑著臉趕到的時候,只剩下一臉不耐的孟括了。
周承瑞心里大怒,自己設的局竟然就這樣被從中攪了局!
Advertisement
方立瑾!
這個每每都是笑意盎然的書生般的人竟還有這樣的本事!
方立瑾如今已是李讓的婿,自己還不能同他撕破臉,只能忍氣吞聲咽下這口氣了!
送走孟括后,他瞇著一雙桃花眼,在亭子外吹著十里長亭的冷風,灌了一肚子的秋風到底也沒能下那火氣。
顛簸的馬車里,方立瑾一下下地顛著那著寒匕首。
倏地躺著的白凌面痛楚之,竟是悠悠醒轉過來。
江錦才面上一片慌,他自然是知道的,自己那糖蒸栗糕里加了足量打下那孩子的紅花。
他高呼道:“我要下車!”
方立瑾的匕首刷的朝他飛去,釘在了離他耳旁一寸的馬車車廂上。
“江大爺心急個什麼勁兒,忙活了這麼久,今晚的好戲我可是不想錯過的。”
說著方立瑾慢悠悠掀開車簾對前頭趕車的車夫道:“去靖安侯府。”
說著他喃喃道:“我這兒可是有份大禮要給姑父瞧瞧的。”
江錦才聞言便面猙獰起來,額間的青筋直冒,“方立瑾!你到底想干什麼?”
燕兒從沒見過江錦才大怒,被嚇了一大跳,直到聽到白凌的呼痛聲才被拉回了思緒,連忙半跪下來扶起了白凌。
“燕兒!江郎……我的肚子……好疼……好疼!江郎……保住……保住我的孩子!”
燕兒只能地半抱著,低低地哽咽。
江錦才卻顧不得那躺著的虛弱的人,他死死地瞪著方立瑾,轉瞬手便出了釘在車上的匕首,猛地向方立瑾撲去。
方立瑾眉頭都沒皺一下,直接住了他的手腕,再微微使勁兒。
&
nbsp;只聽得咔嚓一聲,那右手的手腕便生生地錯了位!
Advertisement
方立瑾悠悠地說道:“江大爺,我奉勸你省點兒力氣,別總想著和我們這種人。”
他戲謔的笑意刺激到了江錦才,可他卻被那止不住的疼痛一陣陣襲來,只得捂著右手痛苦地跪坐在了馬車上。
一旁的白凌已經疼地冒了冷汗,意識恍惚間似乎見到了江錦才的模樣,出手便要去夠他的臉。
江錦才用左手一把推開了,“你滾啊!都是你這個賤人!我這回要完了!都是你!都是你這個賤婦引我!”
燕兒嚇得驚在了原地。
小姐心心念念的江大爺,就是這副臉?
賤婦?
瞧見小姐痛苦的神,心里驀地涼了大半截。
可……自己又有什麼資格去同?也是自己親手毀了!
方立瑾冷哼了一聲,穩坐在一邊,端詳著手里的匕首。
白凌意識模糊起來,“江郎……”無力地出手,卻最終還是垂了下來。
“小姐!”
江錦才避之不及地著這個人,他痛苦地捂住了自己的頭。
自己怎麼會同如此……自己怎麼會這麼糊涂!自己是被蠱了嗎?
他怔怔地隨著馬車的顛簸一次次地撞向了馬車的車廂。
一切都要完了!
方立瑾瞥了眼哭得哀哀絕的燕兒,不耐煩地手探了探地上那人的鼻息。
“暈過去罷了,看來那孩子是保不住了。”
燕兒似乎是明白了什麼,抬頭看著江錦才,厲聲道:“是那栗糕?是你!是你害了小姐?”
江錦才惡狠狠地著燕兒,“是你們合伙要害我!若不是你們騙我來這十里長亭,又怎麼會這樣!是你們!從一開始就是你們這兩個賤人!是你們!”
燕兒絕地搖了搖頭,“小姐拿你當活下去的念想!你竟然這樣想!你不配!”
Advertisement
“我江錦才這輩子最大的錯誤就是那日進了的宅子!被所蒙蔽!”
江錦才看了眼躺著的白凌,原先的艷和嫵已經然無存,此刻的瘦骨嶙峋憔悴的厲害。
“只是個賤婦罷了!有什麼資格要本爺真心以對!荒唐!可笑!”
梧桐苑,鬧過了一陣兒后氣氛死一般寂靜下來。
江錦言冷冷瞥了眼停下了罵的江錦才,對一旁的徐媽媽道:“去瞧瞧,耳房里形如何了?”
方立瑾此時玩味一笑道:“表妹就是心也忒善了,這可是人家江大爺親手下的藥。”
江錦言也不理會方立瑾這麼個看戲的人,更何況方立瑾是重要的人證,否則早該請出去了。
冷道:“方嬤嬤,去請老爺來。”
方嬤嬤見這形便知道這事是沒法兒善了的了,于是拔腳就往外頭走去了。
江錦才聽到要去請父親,一下子沖到了江錦言的面前,雙眼通紅地怒吼道:“你想毀了我?你想毀了我是不是!這都是你設的局?都是你做的!”
江錦言冷哼了一聲,語氣冰冷至極,“我能做局讓你去看上忠勇侯的外室?我能做局讓有了孕?那我又能怎麼做局讓你一次次地自作孽!”
到底是這江錦才太蠢,才落到了別人的手里罷了,自己不過是不作為地冷眼旁觀了一場,甚至,連推波助瀾都不屑于出手。
江錦才像是被去了力氣,蹲在了地上,瞪大著眼睛不住地對著江錦言搖頭,“不會的!是你!一定是你!”
江錦言不怒反笑,“愚不可及。”
說著低聲在他耳邊道:“你伙同賀易要害我的時候,可曾想過,自己還會有這麼一日?那寶華山一事……我熬了過來,只是不知,你還有沒有這個運氣能躲過這件事,你也該明白的,你的存在總是會讓我覺得不穩妥……”
突然耳房里子尖銳的哭聲劃破了夜際,江錦言眸子更是暗了暗。
親自下手打掉自己的孩子,這江錦才還真是心狠手辣。
暗暗忖度道這白凌一事到底還是牽扯到了靖安侯府,要想開這一事,還得拿住那個丫鬟,找出背后的人才是。
而此時的江錦才卻跌坐在了地上,著眼前的虛無,不住地低吼道:“都是你害了我!都是你害了我!”
江錦言冷哼了一聲,也不知他口中的這個你是誰?
是白凌?還是自己?
此時的燕兒站在耳房的床榻邊,看著一臉痛楚,著深深地絕之的小姐,后退一步,后背抵在了耳房的墻壁上。
心之人和信任之人都親手毀了,又失去了這個孩子。
一向脆弱的小姐又該怎麼活下去……
那兩個婆子著白凌下的跡搖了搖頭,說道:“去大小姐那里回話吧,孩子沒了,也已經都理干凈了。”
燕兒跌坐在了地上,想到小姐原先的話,心里一陣。
等小姐醒來的時候,又會是怎樣的絕……
江士恒在王氏的院子里正要歇息,卻聽說梧桐苑出了事,連忙起往梧桐苑去了。
王氏一臉擔憂地送走了他后,臉上便浮起了笑意。
梧桐苑安靜了這麼多天,出事了才算是讓心安。
笑意俞濃,“去打聽打聽,梧桐苑出了什麼事?居然這麼急……恐怕又是什麼好消息……”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716 章

團寵小師妹是朵黑心蓮
沉穩大師兄為何全身發紅?瘋批二師兄為何深夜慘叫?優雅三師兄為何血流不止?清冷四師兄為何熱情如火?陽光五師兄為何夜不能寐?傲嬌六師兄為何疲軟無力?妖艷賤貨七師姐,又為何頻頻臉紅心跳?這一切的背后,究竟是人性的扭曲,還是道德的淪喪?鹿悠悠吹了一下額前碎發:“都是姐干的,怎麼?有意見?”某人:“悠悠,那些都是不相干的人,你有什麼想法沖我來。”
176.9萬字8.18 25589 -
完結8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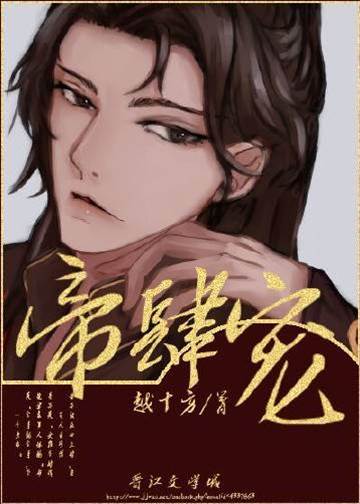
帝肆寵(臣妻)
從軍六年渺無音訊的夫君霍岐突然回來了,還從無名小卒一躍成為戰功赫赫的開國將軍。姜肆以為自己終于苦盡甘來,帶著孩子隨他入京。到了京城才知道,將軍府上已有一位將軍夫人。將軍夫人溫良淑婉,戰場上救了霍岐一命,還是當今尚書府的千金,與現在的霍岐正當…
28.8萬字8 27151 -
完結679 章
相府庶女:王妃不好惹
二十一世紀盛世財團的當家人,含恨而死,穿越成異世相府二小姐。初醒來驚才艷艷,護幼弟,打惡奴,斗嫡姐嫡母,震懾父親。 她囂張,狂妄,卻引來各色優異男子爭相追捧。 天啟國太子,謫仙般的人物,獨對她伸出溫暖的手。“清靈嫁我可好。” 天啟國的殺神王爺,他將她禁錮在懷中,咬著她的耳朵說:“莫清靈,我們才是一個世界的人,我們都屬于黑暗。” 有的人,你認為他才能與你比肩,卻發現,一切只是陰謀。 有的人,你認為你與他只是陌路,卻發現,他才能與你攜手天下。 世間之情孰真孰假,縱使是再活一世,她依然看...
122.2萬字8 33666 -
完結121 章

玲瓏雪
文案:下本古言開《高臺明月(先婚後愛)》不喜棄文即可,謝絕惡言傷害作者。感恩。皎皎明月x野蠻生長1)陳夕苑,帝女,鐘靈毓秀若華光。身有麒麟骨,貴不可言。她自幼聰穎,書畫藥理權術無一不通,提到她的名字無不贊譽有加。顧紹卿和她完全不一樣。西地,乃至整個瀧若最瘋的那只狗,不出聲,一身煞氣就足以叫人膽寒。這樣的人,任誰看都是配不起瀧若明珠的。2)并臻二年,永嘉帝因病去世,長公主陳夕苑成了下一任國君。門閥士族欺她勢單力薄,紛紛而動;北疆異國一再挑釁。衆人皆道:陳夕苑這女帝頂多做兩年。可他們并未等到篤定的場景。朝堂內,女帝手腕強硬,絕不妥協;各地,少年英雄紛紛冒頭堅定為國駐邊,顧紹卿這只瘋狗成了最耀眼的那個。年僅二十的異姓王,戰功赫赫可蓋主。衆人又道,顧陳對峙的時代開始了。3)又一年春至,天下安平。鎮北王回帝都,整個帝都都如臨大敵。一個不留神,這天下就要易主了?誰也想不到,此刻雍華宮內,女帝正在看折子,而鎮北王在不遠處的躺椅上陷入沉睡。睡醒後的第一句話:“陳夕苑,折子能有我好看?”第二句話:“陛下還記得當年偷親臣的事兒吧?如今天下太平,該負責了吧?”雍容絕豔的女帝聞言,忽而笑得像個小孩子。她拿起一份折子丟向顧紹卿:“那就賞三哥一個皇夫當當。”強強青梅竹馬,雙向奔赴。*下本古言開《高臺明月》一身野骨門閥梟雄x溫柔豔極大美人女主視角暗戀成真/男主視覺的先婚後愛/年紀差,大型真香現場1)昭順三十六年,帝王老邁昏庸,內廷四子奪嫡,八方群雄并起,嶺東季與京便是其一。他出身草莽,卻是神力蓋世果斷殺伐。年紀不過二十有四,便手握十萬精兵,牢牢控住嶺東。同一年,家中令他履行一紙婚約。妻子是松陽世家的小女兒--林青黛。據說婚約原先定下的林家嫡長女,因故才換了嫡次女。季與京并不在意這些。娶誰對他而言,沒差。2)林青黛,高臺明月,身嬌體軟貌美如花,琴棋書畫無一不通。她替姐姐嫁到嶺東、嫁給一個上不了臺面的莽夫,整個帝都都在憐惜她,姐姐更是萬分愧疚。林青黛反過來安慰姐姐,“姐姐莫要擔憂,此番,黛黛心甘情願。”有些話她沒說,多年前,她就見過了季與京。至那之後,她就再沒忘記過他。3)幾乎所有人都不看好這門婚事,包括季與京自己。這會兒他怎麽也想不到未來有一日,他會親自折竹造工藝繁複的鳳凰紙鳶,只為搏妻子一笑。起初,季與京的眼裏只有王侯霸業。後來,他的目光總在追尋林青黛。內容標簽:宮廷侯爵豪門世家天之驕子成長正劇陳夕苑顧紹卿一句話簡介:公主x瘋批,青梅竹馬雙向守護立意:相互扶持,終成眷屬
45.3萬字8 114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