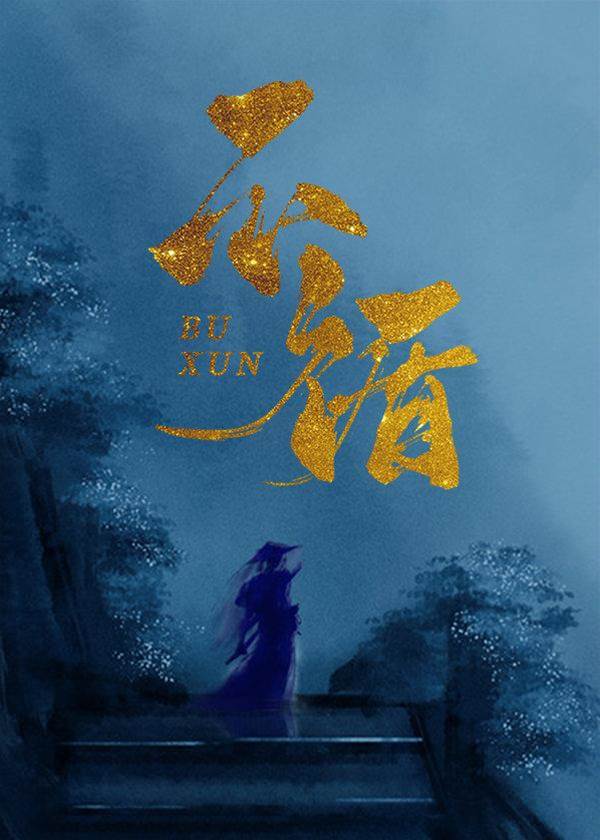《嬌養》 第93章 第 93 章
簌雪院。
阿圓一大早喂花糕和糖吃完早飯,自己也收拾東西出門。
在門口,正巧遇到了姐姐褚琬。
“今日不是休沐麼?”阿圓奇怪看,見眼下烏青像沒睡好似的,便問:“姐姐近日在忙什麼?”
褚琬最近在跟賀璋查天墟易兵的事,整日提心吊膽的,哪里睡得好。不過此事機不能對外宣揚,便只能說:“我最近忙查案子,中午你跟阿娘說一聲,我不回來吃飯了。”
“你不是在戶部收稅嘛,怎麼也查案。”
“案子與收稅有關,”褚琬敲:“我從旁協助,你做什麼去?”
“我去綢緞莊。”
兩人在門口分別,阿圓乘馬車徑直去了城東的綢緞莊。
其實城西也有賣布匹的鋪子,只不過城西大多住著平民百姓,布莊里頭的布料便沒那麼好。阿圓這回是打算買尺布給蕭韞做香囊的,蕭韞用的東西自然不能差,思來想去還是來城東最好的一家綢緞莊子瞧瞧。
綢緞莊生意紅火,阿圓才到就見這里已經停了好幾輛馬車,進門之后,里頭大多是一些夫人們過來扯布。
掌柜見上著布料極好,以為是哪家貴,熱地上前詢問:“姑娘想看什麼樣的?”
“可有雪緞?”阿圓問。
“有有有,”掌柜的說:“姑娘請坐,我讓人把雪緞拿過來給姑娘挑。”
阿圓在一旁坐下,跑堂的過來上了杯茶。
邊上有兩個姑娘正在挑選布料,聽兩人談話,似乎也是來扯布做香囊的。
其中一子道:“我看這個就好,做香囊用這種花合適,上頭的金線細,而且配這富貴卻不俗氣。”
“我怎麼聽說雪緞更好些?近日時興這個呢。雪緞由上好的雪瑩蠶制,是布料中的極品。”
Advertisement
阿圓側頭看過去,認真聽兩人說話。
這時,門口又進來一人。
是個穿著素雅的子,年紀約莫一十歲左右,頭上一累嵌珠珊瑚簪子,襯得皮白皙。
蛾眉靈秀,舉子端莊優雅,姿態輕盈似腳生蓮花。后跟著幾個婢,一進門就問掌柜:“我家小姐上次訂的雪緞可到貨了?”
“到了到了,”掌柜的說:“陸姑娘且上樓稍坐片刻,我這就讓人拿過去。”
那姑娘點頭,款款上了樓梯。
阿圓還在想,這是哪家姑娘,氣質竟如此溫婉大方,實在好看。
隨即,就聽見適才選布料的兩個姑娘小聲議論起來。
“瞧見了嗎?那位就是近日回京的陸家嫡陸亦蓉。”
“何時回京的?我怎麼不知道?”
“上個月,靖海侯府悄悄把人接回來的。”
“啊,可是因為景王?”
“這不明顯是因為景王嗎?如若不然,來這里訂雪緞做什麼?你可知一匹雪緞得多錢,這麼舍得花銀子,想來這位陸姑娘勢在必得了。”
“什麼勢在必得,陸姑娘跟景王本來就有婚約。況且,兩人互相有,這也算苦盡甘來吧。”
“可我前日不是聽說景王帶著個子上街看花燈嗎?”
“那子會不會是陸姑娘?”
“聽說很年輕,應該不是陸姑娘。”
“如此說來,景王變心了?哎呀,看來再堅貞的也容易被時間消磨,我還記得當年景王沖冠一怒為紅的事呢。”
聽到這里,阿圓心悶悶的,覺得周遭的空氣也悶起來。
恰巧這時,跑堂的捧了兩匹雪緞過來。
阿圓瞧了眼,問:“你們這的雪緞就這兩種嗎?”
“一共有十幾樣花,不過其他的被陸姑娘選了。”跑堂的說:“不若姑娘等一等,我上去問問陸姑娘,看是否能勻一兩尺給姑娘。”
Advertisement
阿圓默了默,突然沒了做香囊的心思。
“不必了,”說:“我過幾日再來瞧瞧。”
出了綢緞莊,阿圓深呼吸口氣上馬車,適才那兩個姑娘說的話一直縈繞在心頭。
“兩人互相有,這也算苦盡甘來吧”
“如此說來,景王變心了?我還記得當年景王沖冠一怒為紅的事呢”
這段時日,被蕭韞哄得分不清南北,倒是忘了,他曾經有過這麼一段。
景王和陸家嫡的事,全京城恐怕沒人不知道,當年曾真實意地為兩人過。
沖冠一怒為紅的事,也知道。
聽說陸家嫡出門賞花不慎迷路,卻遇上了鄂國公府的三公子,而那三公子是個混的,頭一回見陸亦蓉就調戲。彼時景王還是太子,恰巧路過便命人把那三公子打了一頓。
這一頓可打得不輕,而鄂國公是個護犢子的,后來在朝堂彈劾太子不仁,結果當堂便被太子毫不留地怒斥回去。
鄂國公是誰人?
三朝元老,連皇帝都得給幾分面,蕭韞這麼與鄂國公撕破臉,可不就是沖冠一怒為紅?
再后來,宮宴上,嘉懿皇后親口夸贊陸亦蓉賢淑端莊、秀外慧中,并有意賜為太子妃。眾人這才明白過來,原來景王喜歡的子是陸家嫡。
阿圓絞著手帕,不知為何,想到他曾經喜歡過別的子,心里就不好。
如今陸家嫡回來,也不知他會如何做。
過了會,婢蓮蓉問:“姑娘,前頭有家綢緞莊,可要去看看?”
阿圓搖頭:“不了,回去吧。”
才不想給他做香囊,一點也不想。
這廂,陸亦蓉選好布料后,徑直回了府。
吩咐:“今日就拿去給柳娘子做裳。”
Advertisement
柳娘子是京城最好的繡娘,手巧,針腳細幾乎看不出線頭,且繡的花也栩栩如生。
“是。”婢應聲,說道:“這些裳做出來想必夠小姐穿一陣子了。對了,昨日夫人還說讓小姐得空了去錦翠閣選幾套頭面,屆時設宴時穿戴。”
說起頭面,陸亦蓉想起一事,前些日子錦翠閣被人買走了幾箱時興的珠寶首飾,價值上千兩。私下有傳言說是景王買的,畢竟有人瞧見景王邊的護衛去抬的箱子。
買這麼多要送誰?
過了會,問:“我讓你去查的人查到了嗎?”
“小姐,暫時還沒有查到。”婢說:“七夕那日,景王邊的子戴著兔子面,誰人也不知長什麼模樣。”
陸亦蓉若有所思,那子到底是誰?蕭韞明知已經回了京城,卻還如此招搖地帶人上街?
“姑娘不必擔心,”婢勸道:“您去廟里禮佛這幾年,景王寂寞不得排解,寵幸個子也有可原。那子戴著面,便說明見不得人,既是見不得人,自然也無足輕重。”
“我倒不是擔心這個。”
若他只是寵幸個子倒是無礙,怕就怕,他對變心了。
“罷了,不提這些。”
陸亦蓉走到桌邊,從書架上取下個匣子,再從匣子里掏出一封金箔撒花香信箋,然后在上頭寫請帖。
婢稀奇地問:“邀請的帖子都用這種信箋麼?”
陸亦蓉出個的笑:“這是給景王寫的。”
雖是辦茶宴,但想請的只有蕭韞一人。此舉算是試探,若是他來,那說明他對自己還有意,若是不來,興許是淡了心思。
這日,蕭韞從宮里出來,天已黑。
“什麼時辰了?”他問。
Advertisement
“殿下,將至亥時。”
默了片刻,他吩咐:“去梨花巷。”
他這幾日忙,算起來,已經有三日沒見阿圓了。罷了,去看看。
等到梨花巷時,蕭韞才下馬車,護衛就匆匆送來兩封信。
“南邊的報?”蕭韞瞥了眼。
那護衛行禮,答道:“一封是報,還有一封是”
未等護衛說完,蕭韞手:“拿過來,待本王回去再看。”
他接過信箋就往袖子里塞,然后足尖一點,翻墻躍進了簌雪院。
此時小院里靜悄悄,只余廊下兩盞昏暗的燈籠。
簌雪院有兩間屋子,一間是阿圓的姐姐褚琬的,一間是阿圓自己的。
他門路地從窗戶進了阿圓的屋子。這會兒,屋子里線不亮,就里間傳出點微弱的。
床幃紗幔朦朧,映出里頭綽約婀娜的姿。走近一看,原來是阿圓趴在床榻上看書,而床頭點了支蠟燭。
小姑娘看得專注,連有人靠近都不知。
蕭韞隔著纖薄的紗幔進去,小姑娘趴著的姿勢,令曲線畢。一頭青散落在兩旁,顯出白凈細膩的脖頸。
也不知在看什麼書,居然還咬手指頭一臉津津有味。
蕭韞勾了勾,等了會,才咳嗽一聲。
阿圓嚇得大跳,利索地把書合上藏進被子里。
“你怎麼來了?”小聲問。
蕭韞掀開紗幔坐在床沿:“過來看看你,在看什麼書?”
阿圓支吾:“就隨便看看。”
“嗯?”
“嗯什麼嗯,我看些閑書打發時間罷了。”
“夜里看書容易費眼睛。”
“我只看一小會的,你若是不來我就準備睡了。”
蕭韞目幽幽地,拆穿:“我若是不來,你就準備繼續看是吧。”
“你姐姐的屋子都熄燈了,就你還跟個夜貓子一樣。”
“難道你不是?”阿圓頂:“這麼晚了還來爬我窗戶,你堂堂景王不害臊的麼?”
蕭韞笑,把扶起來靠在床頭,與他這麼對著坐。
“兩日不見,可想我?”
男人材高大,這麼坐下來,仿佛占了一半的空間。
而此時他上還穿著銀蟒袍,與以前的玄不一樣,襯得他一副玉面郎君風流的模樣。
阿圓歪頭打量了會,手指了他鼻尖,蠻道:“才不想!”
“為何?”蕭韞問:“我這兩日給你寫信也沒見你回,發生了何事?”
自從在綢緞莊聽了那些話,這兩天阿圓心煩悶,就不想給他回信。
此時想起來,連看他這張俊臉都覺得礙眼起來。
心里有氣,便不大想理他。
“怎麼?”蕭韞把的手拉過來,緩緩挲上頭的,問:“誰惹你不高興了?”
“就是你!”阿圓癟。
“我怎麼惹你不高興了?”
阿圓別過臉,不想說話。
蕭韞鉗住下,迫轉過頭:“說說看,我哪里惹你不高興,我這就給你賠罪。”
見癟著,模樣俏,蕭韞拇指捻了捻瓣。
“嗯?我哪里惹你不高興?”
阿圓張了張口,很想問他以前是不是喜歡過陸亦蓉。
可不知出于什麼心理作祟,又偏偏不肯問出來。而且,自己其實也清楚答案,問了只會讓自己難堪。
拍開他的手:“反正我不想你。”
蕭韞莞爾,把小姑娘拉進懷中:“但我想你了,很想很想。”
“我今日在宮里待了一天,理事理得頭疼。”
阿圓沒反抗,任他抱著自己,半張臉埋在他懷中,眼睛睜得大大的,心里糾結別的事。
“這兩日你做了什麼?”蕭韞問。
“看書,去買了匹布給爹爹做裳。本來還想給你繡”
“繡什麼?”
“本來想給你繡香囊,但現在不想了。”
聞言,蕭韞退開些許,仔細打量:“你到底在氣什麼?”
他含著點笑饒有興致:“你是河豚嗎?這麼生氣。”
“”
你才是河豚!
阿圓捶他,卻不小心打到他邦邦的骨頭,哎呦一聲手疼得很。
蕭韞趕幫。
“你到底氣什麼,嗯?為何不肯幫我繡香囊了?”
“我”想了想,阿圓隨意找了個理由:“沒什麼,就是氣你這麼久都沒來找我。”
燭火下,小姑娘的面龐姣好,紅人。且又是穿著寢袍,薄薄的料映出里頭小的花。
而且的閨房總是香噴噴的。尤其床幃,也不知熏了幾種香,被褥上的,裳的,還有上的,很好聞。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563 章

丞相府的小娘子
沈梨穿越了,穿到一窮二白,剛死了老爹的沈家。上有瞎眼老母,下有三歲幼兒,沈梨成了家里唯一的頂梁柱。她擼起袖子,擺攤種菜,教書育人,不僅日子越過越紅火,就連桃花也越來越多,甚至有人上趕著給孩子做后爹。某男人怒了!向來清冷禁欲的他撒著嬌粘上去:“娘子,我才是你的夫君~”沈梨:“不,你不是,別瞎說!”某人眼神幽怨:“可是,你這個兒子,好像是我的種。”沈梨糾結:孩子親爹找上門來了,可是孩子已經給自己找好后爹了怎麼辦?
87.5萬字8 21269 -
完結16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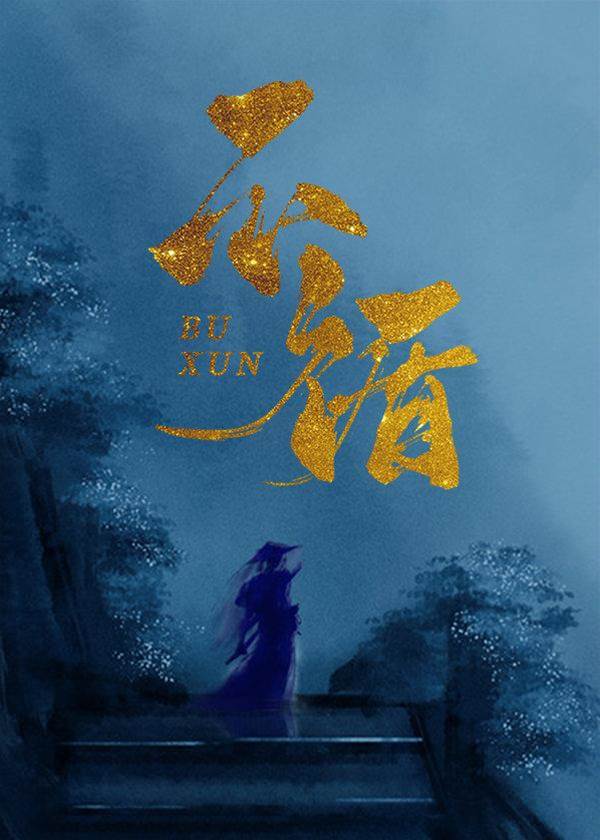
不循(重生)
邵循是英國公府的嫡長女。 父親是一品公侯,母親是世家貴女,宮裡的淑妃娘娘是她姑姑,太子之位的有力競爭者三皇子是她表哥。 人生中唯一的不足就是生母早逝,繼母不親,原本應該榮華富貴不缺,波瀾壯闊沒有的過完一輩子,誰知一場夢境打破了一切—— 邵循夢見自己的堂姑為了給兒子剷除對手,犧牲侄女的名節用以陷害風流成性的大皇子,害得自己清白盡毀,只能在鄙夷中被大皇子納為側妃。 大皇子風流成性,大皇子妃善妒惡毒,邵循醒來後生生被嚇出了一身冷汗。 誰知這夢做的太晚,該中的招已經中了,無奈之下決定拼死也不能讓噩夢成真,為了躲開大皇子,慌不擇路的她卻陰差陽錯的撞進了另一個人懷裡…… * 邵循清醒過來之後跪在地上,看著眼前繡五爪金龍的明黃色衣角,真的是欲哭無淚—— 這、這還不如大皇子呢! * 1雷點都在文案裡 2年齡差大 3請原諒男主非c,但之後保證1v1
49.3萬字8.33 50004 -
完結432 章
舔狗太纏人,王爺他又吃醋了!
前一世,柳落櫻錯將惡人當良人,落得個焚火自戕,慘死在冷宮無人收屍的下場。 重生後,她強勢逆襲! 抱緊上一世兵部尚書的大腿,虐得渣男後悔不已。 鬥惡毒伯母,虐心狠表妹,她毫不留情! 唯有在對待身份神秘的私生子二表哥時,那顆冰冷的心才會露出不一樣的柔情。 哪曾想,報完仇,大腿卻不放過她了。 洛霆:“櫻兒,這輩子,你只能是我的妻......”
76.7萬字8 9086 -
完結207 章

都說她不配,偏偏清冷權臣他超愛
【先婚后愛+古言+女主前期只想走腎、經常占男主便宜+共同成長】江照月穿書了。 穿成男配愚蠢惡毒的前妻。 原主“戰績”喜人: 虐待下人。 不敬公婆。 帶著一筆銀錢,和一個窮舉子私奔。 被賣進青樓。 得了臟病,在極其痛苦中死去。 這……這是原主的命,不是她江照月的命! 她可不管什麼劇情不劇情,該吃吃、該喝喝、該罵人罵人、該打人打人、該勾引男配就勾引男配。 一段時間后…… 下人:二奶奶是世間最好的主子。 公婆:兒媳聰慧賢良啊。 窮舉子:我從未見過這麼可怕的女人! 男配摟著她道:時辰尚早,不如你再勾我一次? 江照月:???
39.5萬字8 13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