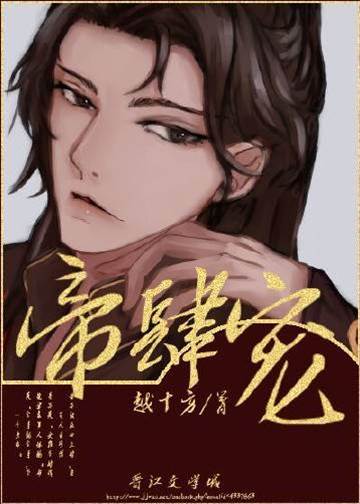《春云暖》 041 風波
湖北岸蘭芷叢生,品種各異,但開得都甚好。
也不知道究竟是水土使然,還是別的原因,這個地方自古以來就多生蘭草。
許多人把這里的蘭草移植回家中去,但無論怎麼心養護,都不如在野外長得茂盛開得妍麗。
石子路狹窄,徐春君和姜暖攜著手在前頭走,四個丫鬟在后面跟著。
姜暖忽然笑了一下,靠近徐春君的耳邊小聲道:“徐姐姐,我說了你不要生氣。我覺得你和陳大人好般配。”
徐春君聽了,卻鄭重其事地對說:“我和他不過是因為柳兒的事多說了幾句話,永遠都只是兩個全然不相干的人。”
“姐姐你生氣了?”姜暖自悔失言,“都是我不好,貧賤舌地胡說一氣,你千萬別往心里去。”
“我沒有生你的氣,”徐春君笑了笑,“只是我和他絕無可能。”
“那……那又是為什麼?”姜暖的心思不夠細膩,但覺得陳思敬明明對徐春君有意。而徐春君又待字閨中,哪里就完全不可能呢?
“將來你會知道的,婚姻這件事,從來都不是只看個人。”徐春君沒又跟姜暖提過自己和鄭無疾的事,這件事目前并未對外公布,又何況里頭牽涉太多。
姜暖嘆息一聲:“徐姐姐,我知道你的意思,像你像我,婚姻的事,從來都是自己做不得主的。”
于是把前日洪家的事說了。
問徐春君道:“姐姐,我這幾日心里頭一直在想。我繼母到底是真的為我好,還是在利用我?他說的那些話聽上去也沒有說不通的地方,可我心里頭還是不太好,是不是我太小心眼兒了?”
徐春君可不似姜暖這般單純,這件事明眼人一見便知。
所以會說的不如會聽的,孟氏巧言令,卻也改變不了要拿姜暖來攀附高的目的。
Advertisement
姜暖比徐春君還要小一歲,且剛剛來京幾個月,為什麼要那麼急著提親呢?
況且洪家的那位二爺若真是已經大好了,又怎肯降低份去和一個五品的兒結婚?
且這兒又是自長在外祖家的,姜家自己尚且未完全了解的品格,怎麼就放心地一見面就要定準了?
可是這些話是不能跟姜暖說的。
不是徐春君想要置事外,更不是要瞧姜暖的熱鬧。
而是知道姜暖心里不藏事,而桑媽媽又是個脾氣急的。
一旦這些話讓們知道了,回去必然不能跟孟氏維持表面上的和睦。
如此一來,姜暖的境只會更難。
何況徐春君看得出來孟氏很在意自己的名聲,那就更不能撕破臉,好歹有這層遮布,總是不好太骨。
于是,叮囑姜暖道:“你要記住,第一不可頂撞你父親,亦不可當著他的面頂撞你的繼母。”
男子不大理會宅的事,姜暖本不寵,若頂撞了父親,就更不待見。
孟氏再吹一吹風,姜暖必然要委屈。
姜暖聽了點頭。
徐春君繼續說道:“第二不可桑媽媽、鈴鐺和墜子這三個人離開你邊。”
徐春君早就懷疑孟氏有意把自己的人塞到姜暖跟前,好更容易擺布。
姜暖苦了臉道:“我當然想讓們常在跟前,可萬一我繼母非要調開們,我又能怎麼辦?畢竟是當家。”
徐春君緩緩道:“依我看來,近期不會有什麼變了。”
因為孟氏要安姜暖,不讓生出回外祖家的心思。
“那麼以后呢?”姜暖追問徐春君。
“你回去可桑媽媽們散布消息,就說你自便有高人指點過,說你克仆人,批了八字才選了這三個人在你邊伺候。先前你們也不大信,但如今有了柳兒事,方知不是兒戲。那些下人們聽了,只怕沒有人再急著往你跟前去了。便是你繼母想要塞人給你,你也可以拿這個搪塞過去。”
Advertisement
姜暖聽了忍不住拍手道:“徐姐姐,你可真是個諸葛!我若是有你一半的聰明,也不會被人拿了。”
“你不要夸贊我了,記住我的話就夠了。第三,若有什麼棘手的事,你記得裝病裝昏,誰也奈何你不得。此外,除了同我之外,無論是誰說起,你都只說你繼母的好,一句壞話也不說。”
孟氏扮賢良,姜暖也要顯得孝順才,不能自壞名聲。
姜暖道:“你說的我都記下了。”
說著又把頭靠在徐春君的肩上,嘆息道:“若你是我的親姐姐該多好,有你這個姐姐,我便沒了長輩倚仗,也不會無依無靠。”
徐春君笑道:“我與你投緣,不是親生的姐妹也可以肝膽相照的。”
姜暖笑嘻嘻地抱住徐春君的腰道:“那咱們就結拜吧!”
徐春君未及開口,忽然聽到后有人笑道:“姜大腳,我說你怎麼不在船上,居然跑到這里來賞花了!你都多大了?還跟人撒!”
小侯爺宗天保從一旁的山石后邊跳出來,嘻嘻哈哈地打趣姜暖。
姜暖先前就已經被他氣著了,如今他還是一口一個姜大腳姜大腳地著,不由得更加惱怒。
“徐姐姐,我們走!”姜暖站起來,邁開步就往前走。
誰想宗天保在后追不放,兀自嚷嚷道:“姜大腳不愧是大腳,走得可真快!”
姜暖本來走得甚急,聽他如此說猛地剎住了腳。
小侯爺收不住步子,跟撞了個滿懷,只覺得姜暖又香又,竟是生平未領略過的妙,不口而出道:“你上好香!”
姜暖見他眼灼灼一副賊像,幾乎不曾氣死!
此時什麼也顧不得了,咬牙罵道:“你給我滾!”
Advertisement
同時手去推他,只聽噗通一聲,宗天保被推得掉進了湖里。
他因為要逗弄姜暖,故而一個人跑過來。
跟著出來的小廝和同游的人都在那邊,見他落水才連忙趕過來。
其中一個著竊藍提花綢的公子哥兒指著姜暖罵道:“你個潑婦!居然敢手,不識抬舉的東西!”
姜暖不客氣地回罵道:“你算哪蔥就來罵我?!這湖邊也無青草,不缺你這多驢!”
那人被罵得臉都白了,上來就要打姜暖。
猜你喜歡
-
連載3575 章

錦鯉棄婦:隨身空間養萌娃
一覺醒來,安玖月穿成了帶著兩個拖油瓶的山野棄婦,頭上摔出個血窟窿。米袋裡只剩一把米;每天靠挖野菜裹腹;孩子餓得皮包骨頭;這還不算,竟還有極品惡婦騙她賣兒子,不賣就要上手搶!安玖月深吸一口氣,伸出魔爪,暴揍一頓丟出門,再來砍刀侍候!沒米沒菜也不怕,咱有空間在手,糧食還不只需勾勾手?且看她一手空間學識無限,一手醫毒功夫不減,掙錢養娃兩不誤!至於那個某某前夫……某王爺邪痞一笑:愛妃且息怒,咱可不是前夫,是『錢』夫。
322.4萬字8.08 312214 -
完結8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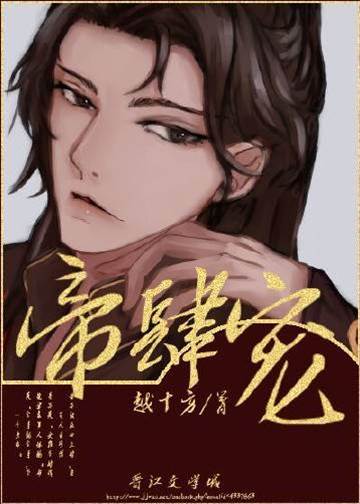
帝肆寵(臣妻)
從軍六年渺無音訊的夫君霍岐突然回來了,還從無名小卒一躍成為戰功赫赫的開國將軍。姜肆以為自己終于苦盡甘來,帶著孩子隨他入京。到了京城才知道,將軍府上已有一位將軍夫人。將軍夫人溫良淑婉,戰場上救了霍岐一命,還是當今尚書府的千金,與現在的霍岐正當…
28.8萬字8 26416 -
完結451 章

歡恬喜嫁
前麵七世,徐玉見都走了同一條路。這一次,她想試試另一條路。活了七世,成了七次親,卻從來沒洞過房的徐玉見又重生了!後來,她怎麼都沒想明白,難道她這八世為人,就是為了遇到這麼一個二痞子?這是一個嫁不到對的人,一言不合就重生的故事。
81.3萬字8 15654 -
完結532 章
醫庶無雙
原主唐夢是相爺府中最不受待見的庶女,即便是嫁了個王爺也難逃守活寡的生活,這一輩子唐夢註定是個被隨意捨棄的棋子,哪有人會在意她的生死冷暖。 可這幅身體里忽然注入了一個新的靈魂……一切怎麼大變樣了?相爺求女? 王爺追妻?就連陰狠的大娘都......乖乖跪了?這事兒有貓膩!
103.5萬字8 19338 -
完結206 章

賠罪
施綿九歲那年,小疊池來了個桀驁不馴的少年,第一次碰面就把她的救命藥打翻了。 爲了賠罪,少年成了施綿的跟班,做牛做馬。 一賠六年,兩人成了親。 施綿在小疊池養病到十六歲,時值宮中皇子選妃,被接回了家。 中秋宮宴,施綿跟在最後面,低着頭努力做個最不起眼的姑娘,可偏偏有人朝她撞了過來,扯掉了她腰間的白玉銀環禁步。 祖母面色大變,推着她跪下賠禮。 施綿踉蹌了一下,被人扶住,頭頂有人道:“你這小姑娘,怎麼弱不禁風的?” 施綿愕然,這聲音,怎麼這樣像那個與她拜堂第二日就不見蹤影的夫婿?
33.9萬字8.18 404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