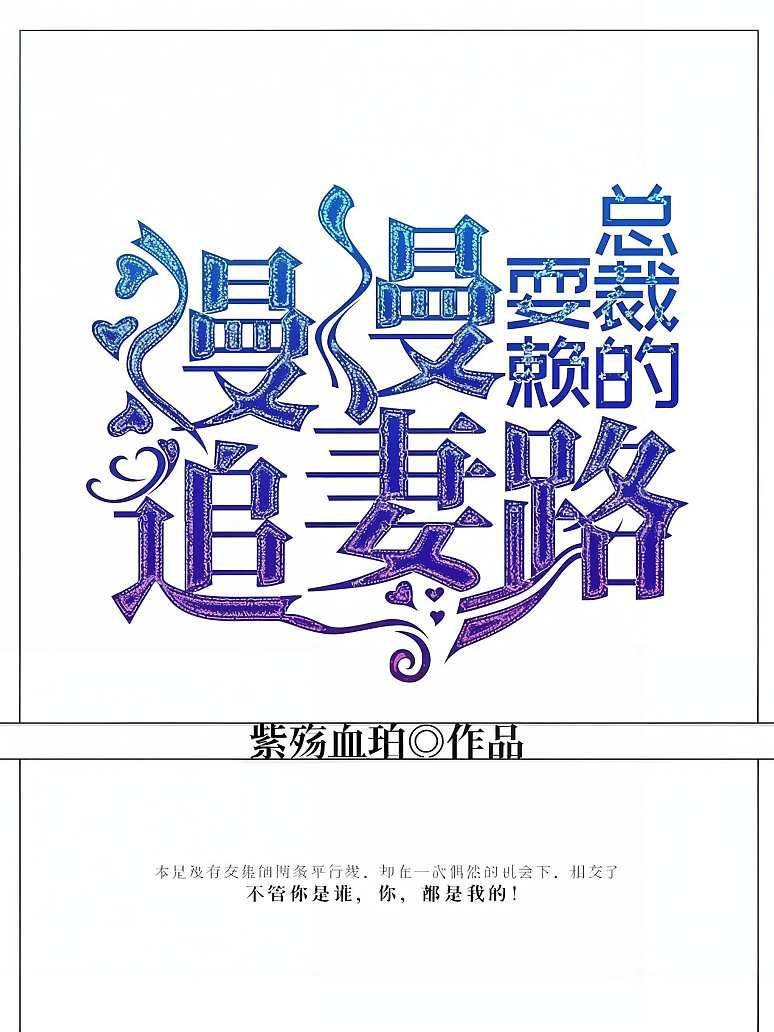《總裁的前妻》 第六十八章
秋如是花其鎮土生土長的孩,以爲世界,就只有花其鎮這麼大,很認份,也很安份,與張舉韶定下親之後,就等著嫁張家,雖然,張舉韶並沒有什麼大的作爲,至,可以安安平平的過完一輩子。
小鎮上的人不求別的,這一點,至關重要。
只不過——一次南部行,改變了想法,也擴大了眼界,原來——世界並不侷限於小小的花限鎮,它可以更大,更廣,事實上,花其鎮實在是太不起眼了。
一百七十七公分的高,高挑苗條的材,一張豔麗的臉蛋——有很好的高攀條件,張舉韶理所當然的不被放在眼裡。
這一次,要不是拼頭男人是黑社會老大的兒,纔不會窩囊的躲回這個窮鄉僻壤,的家人,早就搬離了花其鎮,這裡連個親人都沒有,這裡不是的,但是,除了鄉下地方,也實在想不出有什麼地方可以躲可以藏。
人的妒火是可怕的,特別是那個黑社會老大的兒,恨秋如搶了的男人,一定要將秋如往死裡整。
爲了活命,不得不逃回來。
“來了來了,秋如回來了”。
“瞧瞧的樣子,纔多年沒見,完全像是變了一個人一樣”。
一路上,閒言閒語不斷,秋如卻好似沒有聽到一般。
莫怪小鎮上的人們會奇怪,因爲秋如變得實在是太多了,以前,亦如同小鎮上的姑娘一般純樸善良,現在,只要一眼,就能瞧出,絕對不是什麼善良的角,特別是那一雙妖的眼,活似生來就是爲了勾男人的魂一樣。
“放心放心,徐媽媽已經去告訴張家,秋如回來,真是不明白,怎麼還有臉住張家呢”。開心也是從東部城市嫁到花其鎮這個小鎮上的,不過,可是一點都不像秋如那般,雙眼一瞄,眼中滿是鄙夷之。
Advertisement
人做到這個份上,也算是到頭了。
“開心——”,元布良輕喚妻子,別人家的事,外人最好不要管。
“布良,開心說的對極了,張家對可是一點義務都沒有,舉韶就算回來了,也不會娶,瞧瞧現在這個樣子,配張家門嘛”。開心書屋隔壁開雜貨店的老闆娘輕哼一聲,張家家世清白,秋如這幾年在南部天知道做的是什麼勾當。
聽說秋如的家人就是因爲跟不明不白的人往,早就跟斷絕關係了,不然的話,好好的有家不回,卻偏偏要躲到花其鎮來。
這是無路可走。
開心斜睨丈夫一眼,“聽聽,大家都這麼說”。就他善良,不忍說上一句,難道就眼睜睜的看著張家二老吃啞虧嗎?
“不過,現在有雪歌在張家,諒也不能做什麼”。雜貨店的老闆娘可是鬆了一口氣。
“是啊是啊,雪歌的老公也在哎”。老闆娘的兒子興的說著。
雪歌的老公真的好帥,好酷哦,他長大了一定要跟那人一樣,變得那麼帥那麼酷。
呃——
雖然,他才只有九歲。
“什麼老公,是前夫”。雜貨店的老闆娘低喝自家的兒子,這之間的差別可大了。
“不管是老公,還是前夫了,那男人一看就是個狠角,看來,秋如是不會有好日子過的了”。
大家算是安心了。
至,張家兩老不會被秋如欺。
再說了——
有花其鎮全鎮的鎮民看著,他們也絕對不會允許秋如對張家做出什麼過份的事來。
。。。。。。。。。。。。。。。。。。。。。。。。。。。。。。。。。。。。。。
拓拔殘疼兒子是無庸置疑的,小安理被他抱在懷裡,他就不會捨得放手,不管是誰,一個冷眼,人家再想抱小安理也乖乖的走開了。
Advertisement
可不想被他的冷眼一瞪再瞪。
而且,他不止是用冷眼瞪,兇神惡煞的樣子好似人家搶了他什麼東西一樣的,怪可怕一把的。
連張媽也不敢上去跟他“搶”。
除了雪歌之外——
不會顧及他是不是高興,或是不高興,直接從他的懷裡把兒子接過來。他的一瞪再瞪對雪歌起不了作用,時間一長,他也賴得瞪了。
“幫個忙——”,清澈的眼兒,凝著拓拔殘的黑眸。
“什麼?”。
“爸——呃,張伯那邊有好幾袋花要扛進屋裡,你也知道,他老人家年紀大了,腳不大好,你去幫幫忙,扛一下”。眼兒一撇,那邊空地上,果然散落著幾袋花,在花其鎮,有人家不種花的。
張家也有空出的一個屋子,專門放這些花,剛剛花放在這裡,賣花的人就離開趕下一家了。
拓拔殘瞪著眼,先瞪著雪歌,再瞪著那幾袋散落的花。
瞧瞧他剛剛聽到了什麼,這個可惡的人,要他去扛那種東西。他是誰——他是拓拔殘,他是迷天盟的盟主,現在日月集團的總裁哎,盡敢他去扛那些東西。
輕哼一聲,他掏出隨手的皮夾,“我付錢,讓他請人來扛”。
雪歌緩緩的轉過頭,深深的看了他一眼,然後,什麼也沒說,更不要說,看他的錢。
有錢是很了不起,不過——不是在這裡了不起。
抱著安理,轉,便要離開。
“該死的,你要去哪裡去——”魯的將紙鈔往皮夾一塞放袋中,快速的出手,拉住正要離開的雪歌。
該死的——
他恨了看到那種眼神。
“我想,這跟拓拔先生沒有什麼關係”。淡淡的語氣,著生疏。
Advertisement
拓拔殘用力的爬過烏黑的發,挫敗的低咒一聲,又來了,拓拔先生——這個該死的人,總有辦法讓他滿腦子塞滿了火氣。
“我去——”,低吼一聲,轉,大步朝著那一堆散落的花走去,張伯已經扛了兩袋進去,拓拔殘沉重的腳步聲,蘊含著無盡的怒意,不過——還是扛起花進了屋,剛剛,他看到張伯是進了那間房。
張伯目瞪口呆的看著他怒氣衝衝的一來一回,一來一回——等到張伯回過神來的時候,面前的花已經被扛得一乾二淨,拓拔殘上的休閒裳,已經沾上了不的灰塵。沉重的腳步聲回到雪歌的邊,冷冷的瞪。
“現在你滿意了吧”。
天知道上輩子是什麼東西,如此習慣指使別人做事,而且,還指使的理所當然。
雪歌微微頷首。
白的小臉上,揚著清雅的笑,視線,落在他沾上了灰的肩上,扛一袋花對他而言是輕而易舉的事。
天知道他的力氣已經大到足以單提起。
“昨天的服還沒有幹,進去灰塵吧”。
“就這樣——”,一點灰塵,他纔不放在眼裡呢,長手一,就要接過懷裡的兒子,雪歌皺眉,搖了搖頭,“你上很髒——”。
赫——
消散的怒火再度聚齊。
他的上很髒,到底有沒有搞清楚,到底是誰讓他變得這麼髒的,還站在這裡不嫌腰疼的說著風涼話。
這人果真欠揍的很。
“別惱——”,看著他的俊臉,暴風雨又要來臨,雪歌無奈的搖頭,三十多歲的男人,怎麼就沒有辦法好好的控制好自己的緒呢,“跟我進來——”,話落,先一步,朝著屋裡走去。後的拓拔殘再不願,也只有跟在的後。
Advertisement
進了屋,雪歌將小安理安放好,小傢伙乖巧的睜著眼兒,小臉上笑瞇瞇的神,讓人一看到他也想笑呢。
將拓拔殘拉進洗手間,雪歌讓他先洗過手之後,再用巾沾溼之後,拭他上的灰塵。
兩人的軀因此靠的極近。
近到,拓拔殘能清晰的聞到上的香味兒,淡淡的,像某一種他也說不上名的花香,的上永遠都是乾乾淨淨的,跟的格一樣,能幹淨利落,就絕對不拖的人。
的骨架很纖細,高剛剛好,生下孩子之後,更瘦了些,不過——有些地方倒是一點也沒有瘦,反而更滿了,他的視線,很有自主意識的停留在“某個地方”上。久久未曾移。
纖細的小手,握著雪白的巾,力道不大,輕輕拭他上的灰塵,其實灰塵沾到的地方不多,就是扛花的時候,肩上沾到了些。
拓拔殘很高,高到雪歌必須墊起腳尖,才能拭到他的肩。
一雙大手,驀然環上纖細的腰際,雪歌鄂然的擡眸,清澈的眼兒中,閃著訝異。
“你不累,我都累了——”,惡聲惡氣的低吼,雙眼用力的瞪著的腳,他的手,託著的腰,承了大部份的力道,讓雪歌能更輕鬆的拭他上的灰塵。
很快——
雪歌腳踏實地了,他可以自己,不過,剛剛他的態度已經言明,他賴得去這一點點灰塵。
轉,將巾清洗,擰乾,再度回,才發現,他的手,一直扣著的腰際,不曾放開。
“呃——我現在一點都不辛苦”。雪歌垂下眼兒,指指他的大手,剛剛是幫,現在該不是了吧。
拓拔殘慢吞吞的收回頭,冷聲冷氣的說上一句,“過河拆橋的人”。
呃——
雪歌該怒的,不過,反而笑了,真是稚氣的說法,這句話是怎麼來的都不明白呢,如何的過河拆橋了。
“今天回去嗎?”。率先步出洗手間,拓拔殘跟在的後。
“不回”。
又是冷冷的兩個字。
“那什麼時候回去?”。下意識,接著問道。
後的男人,有著半刻的沉默,雪歌狐凝的回頭,驀然對上他,怒火染紅的黑眸,他的雙手握,咬牙切齒的樣子,好似剛剛做了多麼過份的事。
不解的眨眨眼。
“你怎麼了?”。
“你就這麼不得我離得遠遠,永遠都不要出現在你面前嗎”。他低吼。
雪歌很想頷首,是啊,離婚之後,一直都是這麼希的呀。
不過——
既然已經被他找到,之前的奢,也就是奢了,之後,可不曾再這樣想過。
“你的來去,哪有人能攔得住,別老是讓自己在氣怒之中,對不好,我只是好意的詢問而已,你要是不願意回答也沒有關係啊”。不執著於他的一個答案。
不管他在不在花其鎮。
在不在小安理的邊。
是絕計不會離開這裡,他的存在與否,已經不會干擾的生活,當然,他能平靜一點,的生活也可以過得無風無波一些。
“哼——”。
輕輕嘆息,雪歌再度抱起小安理,提前早就準備好的提袋,回頭,看著那個一臉彆扭的男人,誰說他不是個小孩子呢,敢打包票,小安理再大一些,一定比他更懂事。
“我要到開心小屋去了,你可以到走走逛逛,欣賞一下花其鎮的景,要是無聊的話,可以早些回公司”。代完畢,雪歌便邁步外出。
冷不防——
拓拔殘跟在的後,雪歌回頭,凝著他的眼。
“難道開心小屋只有你能去,我不能去嗎?”。他氣惱的大吼,該死的,那是什麼眼神。
回頭,不再看他。
好吧——
他要去,誰也攔不住。
出了屋,關了門,拓拔殘就跟在的後,纔沒走到三步,他就接過懷中的小安理。
“我來抱”。他的兒子。
兩個大人,一個小孩子,還沒有走幾步,就聽到隔壁的屋裡,傳來吵鬧之聲,雪歌皺了眉頭,沒有急著趕去開心小屋,反倒是轉向隔壁屋裡。
屋裡,已經來了不的人,都是張家左右的鄰居。
站在正中間那個高傲妖豔的人,是在場中,雪歌唯一陌生的人。
張伯和張媽,立在原地,神悲傷無奈,雪歌瞇了眼,不需要多說,知道那個人是誰,轉,將手中的包包往拓拔殘的肩上一掛,進人羣。
“我想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清冷的聲音,讓在場的所有人,都將視線齊聚在的上。
包括那個材高挑的妖豔,高傲的眼,低睨著雪歌,冷哼一聲。
“你又是哪裡冒出來的路人甲?”。
。。。。。。。。。。。。。。。。。。。。。。。。。。。。。。。。。。。。。。。。。。。。。。。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543 章

知性前妻太搶手
小三陷害,前夫指責,林言酒吧買醉。胃病發作撞上薄冷,機緣巧合成為薄冷的“生活秘書”。“你是我的‘生活秘書’,必然要照顧我的所有。”薄冷嘴角邪魅一笑。“‘生活秘書’難道就應該為你暖床麼?”“我的‘生活秘書’,你注定一輩子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 男主是薄冷女主是林言的小說《知性前妻太搶手》又名《婚姻保衛戰》。
97.4萬字8 153039 -
完結558 章
有染
前一晚,他們極盡纏綿,他坐在凌亂的床邊以一副睥睨的姿態望向她,「你愛我嗎?」 「愛」 他淺笑出聲,漸漸的,笑到難以自抑,隨之砸在她臉上的竟是一本結婚證。 而明成佑配偶一欄上的名字幾乎令她崩潰。 那個名字使得她前半生錯了位,竟還要顛覆她的下半輩子。
102.2萬字8 66490 -
完結747 章

我的傾城大小姐
青山埋忠骨,利刃隱于市。退役歸來當了兩年保安的陳今朝,誤與冰山女總裁風流一夜,樹欲靜而風不止,平靜的生活再起漣漪。如若不能和光同塵,便同風而起,扶搖直上九萬里!
140.5萬字8.18 9417 -
完結196 章

今夜新婚
[現代情感] 《今夜新婚》作者:排骨辣醬【完結】 文案 紀荷25歲這年,和高中時的暗戀對象結婚了。 她這個人,循規蹈矩,是父母眼中的乖乖女。 唯一一次叛逆,是偷偷喜歡上高中時桀驁不羈的陸潯之。 有人說:“和陸潯之結婚,你算是撿到寶咯。” 結婚當晚,陸潯之歇在了客臥,在這之后的兩個月里都是如此,紀荷不由得懷疑
30.4萬字8 6137 -
完結12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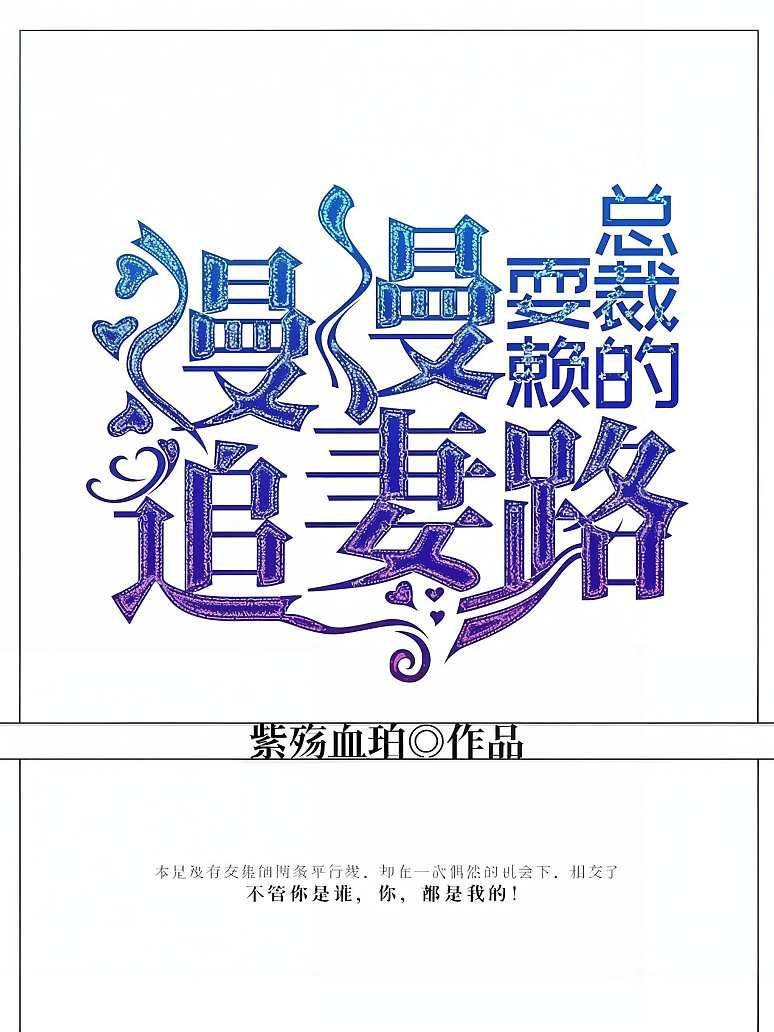
耍賴總裁的漫漫追妻路
本是沒有交集的兩條平行線,卻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事件一:“醫藥費,誤工費,精神損失費……”“我覺得,把我自己賠給你就夠了。”事件二:“這是你們的總裁夫人。”底下一陣雷鳴般的鼓掌聲——“胡說什麼呢?我還沒同意呢!”“我同意就行了!”一個無賴總裁的遙遙追妻路~~~~~~不管你是誰,你,都是我的!
27.3萬字8 17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