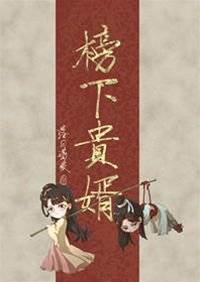《一簪雪》 第5章 第4章
第4章
冬時節,更深重,各家各院都掩門窗,相繼熄了燭火,壽春堂遮掩在一片梧桐綠蔭,兩邊的繁茂枝葉的攀上房檐,夜里顯不出錯落有致,反倒有些森。
朝從別院離開后就一路到壽春堂,用一種相當放松的姿勢蹲坐在房頂上,掏出了冊子和炭筆。
姬府這麼大,不同的院子住著不同人,除非小姐有特別吩咐,否則每日盯哪個是沒有定數的,全憑喜好,不過朝更喜歡壽春堂。
壽春堂的仆人油水多,小廚房的點心都不帶重樣的,濃淡都合的口味,不像沐秋苑的太淡,扶夏苑的太甜,姬崇的書房就更別提,他只品茶。
朝囫圇嘗完一碟糖方糕,往里放了一塊飴糖,悄聲揭開磚瓦,一藥味兒瞬間撲鼻而來——
江氏重病纏許多年,每日藥當茶飲,已經習慣了。
倚在榻前,整個人病瘦得只剩下一把骨頭,裳都顯得空落落,枯枝一樣的手接過藥盞,喝下半碗后便開始咳嗽,旁仆婦忙給拍背。
仆婦姓房,是姬家的老人。
嘆氣道:“這藥方用了半月,也不大管用了,哪日還是要尋個新方子才是。”
江氏只搖頭,說:“別折騰了,一只腳踏進棺材板的人了,神仙方子都沒用——你把佛珠拿來,誦半時辰便歇了。”
江氏信佛,尤其是病重以來,更加看誦經禮佛這事兒,因此壽春堂里還特意劈出了間佛堂,每晚睡前定是要在里頭呆上半個時辰,這比喝那些安神藥的效果還要好。
可前陣子憂思大小姐的婚事,這兩日又頭疼姬家的日后,子顯然更差了。
房嬤嬤給拿了佛珠,但勸道:“要不今夜算了吧,明兒再念也一樣。”
Advertisement
若是平日,江氏定是不肯的,但今日心思太重,只怕沖撞了菩薩,半起的子又坐回去,道:“罷了,老爺回了?”
房嬤嬤道:“沒呢,聽說皇上下令死刑,宮外頭跪了一片,愣是連皇上的面都沒見到。”
都是去替許太傅求的,姬崇亦然。
江氏惋惜,想到這事的始作俑者,不免聯想到姬玉瑤,“今日沐秋苑可還安分?”
用上“安分”兩字,可見江氏對這個兒媳的子多有些不滿。
林嬋是家中最小的孩,生慣養出來的子,難免有些自我和任,當年姬崇娶妻時江氏便有些擔憂,可林嬋的父親那時居閣,很有話語權,又是提拔姬崇的恩師,且江氏想著,子婚后總會長起來……
沒想林嬋十年如一日驕橫,還當自己是林家的小小姐。
但人到這個年紀,再如年輕時那樣任便顯得有些小家子氣了,事事同姨娘作對、時時拿長出氣,這都算怎麼回事?
下人不敢拿面前說,可背地里卻也暗諷心狹隘,蠻不講理。
江氏曾勸過收斂子,尤其是對姬玉瑤,人的容忍都是有限度的,兔子急了還會咬人,若真出了怨懟,日后難免要出事端。
可林嬋不聽,且那個長孫還真是個沒有脾氣的,這麼多年打打罵罵也都沒翻出天去,江氏便也懶得再管,后來久病未愈,更是很久不心這些家長里短的瑣事。
然今時不同往日,不能總由著林嬋的子胡來。
房嬤嬤道:“老夫人寬心吧,夫人也就臉上擺譜,看著勁兒,其實您昨夜說的那番話是真聽了進去,事后還尋老奴剖析了一番。”
江氏聞言,臉好看了些,卻還是不滿意地嗤了聲。
Advertisement
房嬤嬤接道:“大小姐收了那箱頭面,想必這幾日要來請安,是見不見呢?”
壽春堂閉門多年,自江氏病重后便免了小輩的晨昏定省,每日只將養子和吃齋念佛這兩件事,若無大事,連姬崇都鮮迎進門。
所以老夫人若是說不見,也是十分正常。
可偏偏沉默良久,似是怔住了,半響才喟嘆道:“不見了罷……”
江氏呢喃說:“我看著,便要想起另一個……這麼多年,也不知道是不是活著。”
房嬤嬤臉微變,手心一,險些碎了藥盞。
思慮重重,江氏免不得又病了一場,連十五日老太爺的忌日,都無法同去寺里上香。
這日一早,姬崇去上早朝后,林嬋便領著一眾人上了馬車。馬車統共三輛,林嬋與姬嫻與一輛,丫鬟婆子占了一輛,姬玉瑤便只能與姬云蔻同坐,至于顧,是妾室,算不得主人家,沒有資格同去。
然姬嫻與在林嬋冷眼下愣是上了姬玉瑤這輛車,姬云蔻無語,是半點不想看這姐妹兩人在眼前秀深,況且這馬車窄小,如何能乘下三人?
然姬嫻與只抱歉地看向,“二姐姐對不住,你要不同母親乘一輛吧……”
反正是死也不下。
僵持之下,姬云蔻也只好著頭皮同林嬋同乘了。
一行人這就出發了。
馬車途徑鬧市,駛向城門的方向。
車廂里,姬嫻與往姬玉瑤手里塞了個錦囊,道:“聽說近來山路不太平,常鬧山匪,許多人都遭了難呢,雖說今日帶足了護衛,但以防萬一,阿姐將平安符帶上吧,很靈的。”
……姬玉瑤在姬嫻與期盼的目下將錦囊別在了腰間。
扭頭去看車外的繁華景致,沿街店肆林立,人頭攢,晨間是大多人家采買的時辰,是以路上擁堵得很,馬車挪了許久,才挪出人群集的街巷。
Advertisement
在離城門一段距離時,姬玉瑤見出城隊伍竟排了蜿蜒曲折的游龍,稍提了下眉尾,道:“今天什麼日子,出城的人這樣多。”
姬嫻與吃著糕餅,聞言就著熱茶往下咽,說:“不是出城的人多,阿姐你仔細瞧,是出城的速度慢,差查得嚴,一個路引都要來回打量,尤其是子。”
姬玉瑤稍頓,道:“因為上月霍府遇刺的事?”
姬嫻與頷首,沒問姬玉瑤怎麼知道的這事,畢竟這事靜鬧得這麼大,知道也不稀奇。
慨道:“足足一月了,錦衛還在四拿人,因那刺客是個子,他們便挨家挨戶逮著姑娘盤問,鬧得人心惶惶,聽說因為這事,霍大人還被參了好幾本呢。”
說罷,姬嫻與忙止住話,才想起來如今這個被參了好幾本的是未來的姐夫,生怕提及了姬玉瑤的傷心事,于是小心瞥了姬玉瑤一眼。
姬玉瑤神無異,只是用指背支著下頷,隨意問:“霍府往日遇刺,也這樣大干戈?”
“往常倒也沒聽說過……”姬嫻與猜測道:“許是那刺客了什麼寶貝也說不準。”
說話時,人群中忽然一陣,聲音逐漸雜起來,約聽到前頭有人在喊:“讓開,都讓開!”
車夫將馬車趕到一旁,姬嫻與推開車門,探頭道:“怎麼了,發生什麼事了?”
“小姐,好像是許太傅的囚車。”
姬玉瑤挑開簾幔往外看,果然看到一個高高的囚車車頂,人群隙中約窺得車里的一角囚和幾縷白發。前幾日許鶴被關在城外大獄,今日押進城,是要行刑了。
聽說過太傅許鶴。
大周開國以來唯一一個六元及第,多人羨慕都不敢羨慕的功名,是當年顯禎帝,也就是上上任皇帝親定的太子太傅,雖說太子最后未能登基,但后來的先帝也對他相當敬重,還親自去聽他的授課,稱他一句帝師也實在不為過。
Advertisement
這人滿腹經綸,博古通今,唯一不足便是太過心直較真,不知變通,便是皇帝的過錯他也敢揪,全然不記掛自己脖子上還有個腦袋。
遇到心中豁達的君主便也罷了,偏是如今這個,據說很不聽言進諫,恐怕今上對這個心直口快的太傅也是不滿已久,否則怎麼能說斬就斬。
姬玉瑤支頤慢想,倒也沒有生出什麼敬佩惋惜之,確實不能理解這種將自己置于刀尖還企圖匡扶天下的舉措,到頭來不過是一場自我的徒勞罷了。
正想著,城門那端安靜下來。
羈押囚犯的差拔了刀,嘈雜的人群連連退開,一分為二,圍積在兩側,生生騰出條路。只見那囚車里坐著個年邁的老者,他發已半白,凌地披散開,手戴鐐銬,渾狼狽不堪,但依然中氣十足,正仰頭怒喝,字句鏗鏘,讓人聽得分明:
“霍顯!此等險小人,蒙蔽君上,陷害朝臣,乃我大雍之禍啊!枉你霍家乃開國元勛,世代忠將,戰功赫赫,竟出了你這麼個不肖子孫,簡直是造孽!想當年樓大將軍贊你一聲可塑之才,收你為徒,授你武藝,他若泉下又知,怎能心安!……今我雖死,忠義之士不絕,你殺一個殺兩個,還能屠盡天下賢臣?”
“古來佞沒有好下場,你如今也不過是茍活罷了,如此行徑,來日定落得個死無全尸、斷子絕孫的下場!老夫只恨往日太過循規蹈矩,沒能在朝上一刀將你劈了,替天行道!”
他還在繼續罵,這頭姬嫻與已然聽傻了眼,斷子絕孫……這豈非將阿姐一并罵進去了?
忙放下簾幔,好像這樣便能聽不到外頭洪亮的聲音。
姬嫻與安道:“阿姐……這些都不作數的,你別放在心上。”
姬玉瑤朝一笑,道:“你放心,我沒事的。”
可這笑在姬嫻與看來,怎麼都是勉為其難的樣子。
再聽馬車外,怒喊不斷,且有愈罵愈烈的勢態,太傅博學,口才了得,這一番舌幾乎是將霍顯罵了里的老鼠,讓人聽著都覺得惡臭不已。
且他邊罵還邊細數著霍顯近年來的惡行,莊莊件件事無巨細,什麼沉湎聲、強搶同僚小妾;惡意充盈后宮,愚弄帝王,哄得皇上連月不理朝政;目無法紀,不僅佩劍宮,還當朝斬殺了史臺彈劾的言;與閹黨沆瀣一氣禍朝綱,殘害朝臣,更將生人剝皮,手段之殘暴,令人發指……云云如此,數不勝數,若用紙筆寫下,恐怕能著一篇驚世駭俗的萬字問罪書。
姬玉瑤饒有興致地聽著,這些傳言里,有些知曉,有些倒是未曾聽聞,正新奇時,地面遽然,踏踏馬蹄聲隨之而來。
周遭再次嘈雜,有人惶恐道:
“是鎮司,鎮司的人來了。”
“快走快走,明日再出城吧,真是倒霉……”
姬玉瑤微頓,手里把玩的簪子一不留神就劃破了指尖。
短暫的出神之后,抬眸,從簾慢隙中窺見一隊人馬浩浩湯湯自遠疾馳而來,中間那人格外矚目,隔著老遠也能瞧見他那張牙舞爪的麒麟服,這樣帶著冷風直沖過來,袍上的麒麟仿佛盤旋的鷹,氣勢洶洶。
所經之掀起一陣風,簾幔揚起的瞬間,他驟然回首,似是很不經意地瞥了一眼。
猜你喜歡
-
完結295 章

半傻瘋妃
白日她是癡癡傻傻的瘋妃孟如畫,夜晚她搖身一變成了身懷絕技的女殺手。白日他是溫文儒雅的乖王爺諸葛啓,夜晚他成了邪魅的地下霸主。王府內他們互不關心,視而不見,他甚至連她的樣子都不曾見過。府外她是他追逐的獵物,是他眼中勢在必得唯一配得上他的女人,然而某一天,他突然發現,他的瘋妃竟然有一雙和她同樣的眼睛,他開始懷疑,
53.9萬字7.82 82931 -
完結706 章

盛寵小萌妃
【穿越 團寵 奶寶文 虐渣打臉 溫馨甜萌 金手指】穿成三歲半的小奶娃還差點被人害死?穆昭昭抱著異能童話書,拳打惡奴,腳踩渣渣,露出可愛小爪爪:“壞銀!嗷嗚!咬始你~!”反派捂著被揍青的眼睛四處告狀。然而,權臣老爹:“昭兒威武!”潑辣繼母:“昭昭棒棒噠!”心機兄長:“妹妹讓開,讓哥哥來!”反派找來了那位傳說中冷漠無情的鐵血王爺,穆昭昭趕緊賣乖,舉著小手手裝可憐:“夫君,痛痛!”某王爺心疼極了:“竟敢欺負王妃!來人!把這人拿下!”反派,卒。
127.5萬字8 26845 -
完結13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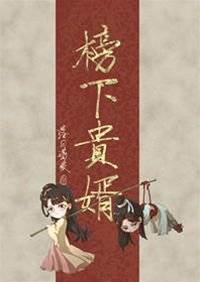
榜下貴婿
預收坑《五師妹》,簡介在本文文案下面。本文文案:江寧府簡家世代經營金飾,是小有名氣的老字號金鋪。簡老爺金銀不愁,欲以商賈之身擠入名流,于是生出替獨女簡明舒招個貴婿的心思來。簡老爺廣撒網,挑中幾位寒門士子悉心栽培、贈金送銀,只待中榜捉婿。陸徜…
46.9萬字8 7765 -
完結704 章

極品老婦要翻身
不過是看小說時吐槽了一句“老太婆活該”,27歲未婚小白領喬玉蘿就直接穿到了書中,一覺醒來實現三級跳:結婚,生子,喪夫當婆婆。 原身是個潑婦,罵遍全村無敵手。 原身還是個極品,惡婆婆該有的“品質”她一樣不落。 望著被原身養歪的四個逆子和一旁瑟瑟發抖的兒媳孫女,喬玉蘿淚流滿麵。 掰吧,為了不重蹈老婦人的慘死結局,掰正一個是一個。
86.8萬字8.33 60686 -
完結389 章

新婚夜之病秧子王爺沖喜后要親親
鬼醫花寫意一穿越,就踹飛了當朝攝政王宮錦行的棺材板,虐白月光,賺金元寶,一路囂張一路掉馬,混得風生水起。 可跟前這一排從天而降的大佬級小弟,令躺贏的花寫意越來越覺得,自己的穿越打開姿勢有點與眾不同。 就憑原主這一身雄霸天下的本事和闖禍屬性,若是不造反掀翻了他攝政王的棺材板,多浪費! 手不能提的病嬌攝政王肩扛青龍偃月刀,翻身上馬,意氣風發:養夫千日,造反有理,是時候讓夫人見識一下本王白天的實力了。
71.8萬字8 1861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