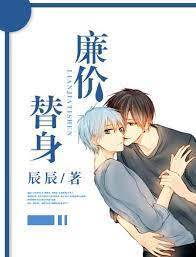《你卻愛著一個傻逼》 第88章
他俯下,掰開了簡隋英的大,最私的部位在他眼前,一覽無。
當簡隋林把沾著他的手指進他後的時候,簡隋英頭一次產生了想在這個世界上消失的念頭。
被自己的親弟弟侵犯的覺,憤怒、恥、憎惡、絕,各種緒撲面而來,他真不知道該如何面對這一切。
簡隋林的眼裡拉滿了,雖然他表面上很平和,但是這掩蓋不了他心的瘋狂。
一想到他在做著他無數個夜晚幻想過的事,他就興得渾發抖,這種覺既刺激,又恐懼,但是他絕對不會停手。
已經走到了這一步,他沒有辦法停手。
簡隋英太久沒有用過那裡,後干不已,再加上他渾繃得死,即使是一手指都出困難。
簡隋林出了手指,附撐開他的大,低下頭,出舌頭去那閉的。
簡隋英就跟過電一樣,瘋狂地掙扎了起來,“簡隋林!你放開我!你瘋了!你瘋了!我你媽你放開我!我要殺了你!”
簡隋英真覺得自己要崩潰了。
他弟弟在做什麼?跟著留著一樣的的親弟弟在對他做什麼?
簡隋林有力的手臂死死住他的,的舌頭在那口肆無忌憚地弄著,甚至在哪裡化之後,嘗試把舌尖進部。
簡隋英被刺激得不住地掙扎著,這時候誰能來一棒子拍死他,他謝那人八輩祖宗。
然而他知道,不會有人來救他。
他眼睜睜地看著他那個面容秀麗地像孩子,一直以來被他嘲笑弱窩囊的弟弟,下了外,出了勁瘦卻非常結實地純男的,然後架著他的,把自己的進了他的裡。
Advertisement
刃侵的那一刻,簡隋英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如果這是噩夢的話……不可能,哪一個正常男人會做被自己弟弟強的噩夢。
他真佩服自己這一刻沒有氣急攻心,吐暈過去,反而是非常清醒地承了這一切。
簡隋林的作其實很溫,似乎非常怕傷著他,而小心翼翼地開擴著那窒的甬道,由慢及快的送著。
他低沉的息聲不絕於耳,似乎得到了無上的滿足,每一下送都進到了那腸道最深,似乎想把自己嵌進簡隋英裡。
“哥……哥……”簡隋林聲著,一聲一聲,到最後甚至有些哽咽,就好像那就是他的全世界。
簡隋英扭過頭,咬了牙關,承著男人的侵,那每一下進出,都如同一把利刃切割著他的靈魂。他的並沒有到太多的疼痛,然而他的思維已經到了混的極致。
他無法接現在正發生在他上的事,因為加注這一切的,是他有緣關系的弟弟,他無論如何,無法接。
簡隋林著有力的腰肢,如同打樁一般一下下撞擊著那,把那窄的腸道擴充到了極致,被壁包圍並急速的快,刺激著他渾的每一個細胞,徹底占有他朝思暮想的人的那種滿足,更是將他的理智通通剝離了。他就如同一只不知疲倦的雄一般,在簡隋英上用力,把自己瘋狂的和無盡的一並宣洩了出來。
這場強制的,仿佛沒有盡頭。每一分一秒的流逝,就代表著他和他大哥相的時間在慢慢減,抱著這樣的心,他沒有辦法停下來,他只能不停地,不停地占有他,期這樣能把自己永遠刻在他的上、心上。
Advertisement
==小番外分割線==
小白參軍淚史
說白新羽是從北京一路哭到青海的,一點兒也不為過。
他被家人掏了上所有的卡,只留了幾千塊的應急錢,然後被塞進了裝新兵蛋子的那節車廂,開始了他痛苦無助的旅程。
他白天對著有別於高樓大廈繁華都市的陌生地風景唉聲歎氣,恨不得拿頭撞玻璃,晚上聞著一車廂的臭腳丫子味兒,聽著沖天響的呼嚕聲,輾轉難眠。
那時候他以為環境不能更糟糕了,然而當他連腳丫子味兒都沒得聞,跟其他地方過來的新兵匯集到另一個破火車上,然後被人兌到離廁所最近的一排座的時候,他才知道自己錯了。
跟一整個車廂的戰友相比,他是那麼地格格不。
其他人都剃了短短地板寸,他還染著栗的頭發,其他人除了軍服上什麼多余的東西都沒有,他手腕上還有六十多萬的表,左耳上還有一排耳釘,其他人多半是曬麥的農家子弟,他還是細皮一輩子沒做過飯的富家爺。
從他踏上火車開始,所有人都拿異樣地眼看他,他也拿警惕地眼看所有人。
沒有人試圖和他說話,他寧願擺弄沒有信號的手機也不想和這群土了吧唧地人說話。
那個時候他覺得自己是被投進了窩的孔雀,他不屑和周圍任何一只土哪怕一丁點翎羽,可他又討厭那種赤地排。
他又悔又恨,他悔他當初欠了賭債,小林子的蠱,冒險了他哥一筆錢,他恨他哥這麼狠心,用這麼歹毒地辦法懲罰他。
沒有人酒豪車洋房的生活,他真是無法想象。
火車不知道當了多天,他恍然中覺得自己骨頭都快散架了。越往深開,他越覺得呼吸困難,以他有限地地理知識,他知道到了缺氧的高原地帶了。
Advertisement
這趟火車有一半的車廂都是裝新兵的,這時候他就聽著有嚷聲從前面的車廂傳了過來,他仔細分辨,似乎是問有沒有人需要吸氧。
這還用問嗎?他看周圍人都暈暈乎乎地樣子,哪個不需要啊。
所以當車廂拉門打開,兩個人一前一後走進來問“怎麼樣,大家……”的時候,他立刻道:“我要,我要,我快不上氣來了!”
一整節車廂的人都轉過了頭來,看著這個坐在臭烘烘地廁所旁邊兒,一路上自命清高,誰都不搭理,卻總在晚上哭的孬種。
走早前面的一個高大的男人,也應聲轉過了臉來,瞇著眼睛看著他。
這人有一張非常年輕漂亮的臉,短短地頭發直愣愣地豎著,看上去英姿颯爽,干淨利落,一綠的迷彩服包裹在他修長結實的段上,別提多帶勁兒了。
白新羽說不上怎麼回事兒,他覺得這個人的眼神太銳利太挑釁了,一被他盯著,心就發慌,不敢再看他。
他發現即使好多人已經明顯呼吸不順了,卻沒人主要求吸氧。
那人微抬著下,說道:“這個車廂有沒有同志需要吸氧?設備有限,大家年輕力壯的,能就一,盡量把設備留給最需要的人。”話雖然是對全車廂的人說的,但他的眼睛卻盯著白新羽,眼裡帶著幾分鄙夷。
不人低聲笑了起來,白新羽的臉一下子變得滾燙。
那人後一個三十多歲的人推了推他,“小俞,往前走,別擋著,去下個車廂看看。”
他把目從白新羽上收了回來,繼續往前走。
在這麼多人面前丟臉,白新羽實在咽不下這口氣,連日來的沮喪,憤恨,惱火,都因為這人的一句諷刺而徹底被點著了,他為自己這些負面緒找到了一個發洩口。
Advertisement
在那人快走到他邊的時候,白新羽騰地站了起來,傲慢地嚷嚷道:“設備一個多錢,我捐你一百臺行不行,幾口氧氣都藏著掖著,既然不讓用,你還問個屁啊。”
整個車廂都靜了下來。
被做小俞的人,又瞇起了眼睛,仔細打量著他。
白新羽一米八二的個子,在這個人面前依然矮了好幾厘米,他又到了那種迫,這種迫跟他最怕的他哥不一樣,他哥再怎麼生氣,也不會真把他怎麼樣,可是眼前這個人,好像真的能掐死他似的,真他的嚇人。
白新羽畏懼地了脖子,但是他已經站起來了,沒臉就這麼坐下,再說這個人好像也沒打算放過他。
他只覺得眼前一花,這個“小俞”已經到了他眼前,也不知道他干了什麼,卡嚓一擰,白新羽兩只手腕都被他寧到了背後,死死固定著。
白新羽驚道:“你要干什麼!”
還沒等他反應過來,小俞已經抓著他的手腕把他往前推,然後踹開廁所的門,一下子把他推了進去。
一惡臭撲鼻而來,他差點兒吐出來。在他急著穩住形,不至於親到廁所牆壁的時候,廁所門在他後一下子砰地一聲關上了。他回撲過去,發現門把手已經被掃帚卡住了。
那人戲謔的聲音從門外傳來,“這裡氧氣多,你慢慢兒吸吧。”
車廂裡傳來一陣哄笑聲。
白新羽哪兒過這種待遇,氣得直接哭了。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70 章
全球高考
全球大型高危險性統一考試,簡稱全球高考。真身刷題,及格活命。 考制一月一改革,偶爾隨機。 梗概:兩位大佬對著騷。 1v1,HE,通篇鬼扯。 因為一個小意外,游惑被拉進一場奇怪的考試中。 暴風雪中的獵人小屋考物理、四面環墳的山中野村考外語、茫茫大海上的礁石荒島考歷史。 一個場景代表一門科目,徒手考試,真身刷題,及格活命。 主角游惑三進三出監考處,因此跟001號監考官秦究結下樑子。 針鋒相對之下,他發現自己似乎早就認識秦究,而考試背後也藏有秘密……
49.3萬字7.67 7509 -
完結42 章

限時占有(ABO)
契約婚姻,限時占有。 顧沉白X涂言 *溫柔攻寵妻無下限(真的寵) *作精受追夫火葬場(并沒有) *攻有腿疾 標簽: 甜寵小甜餅 生子 ABO 先婚后愛
7.1萬字8 5932 -
完結21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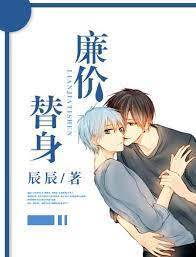
廉價替身
童笙十三歲那年認識了雷瑾言,便發誓一定要得到這個男人。 他費勁心機,甚至不惜將自己送上他的床,他以為男人對他總有那麼點感情。 卻不想他竟親自己將自己關進了監獄。 他不甘,“這麼多年,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麼?我哪里不如他。” 男人諷刺著道:“你跟他比?在我看來,你哪里都不如他,至少他不會賤的隨便給人睡。” 當他站在鐵窗前淚流滿面的時候,他終于明白, 原來,自始至終,他都不過是個陪睡的廉價替身罷了! 同系列司洋篇【壓你上了癮】已完結,有興趣的親可以去看看!
51.1萬字8 938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