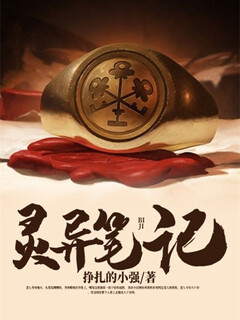《我當道士那些年》 第一百四十二章 雪山一脈的隱秘
待到這幾個人都進屋以后,我才看清楚來人都是雪山一脈的人,其中就包括那個最高中出來的,陪同我師父一起在地下等我的——掌門,或許應該掌門?
進來的雪山一脈的人都穿著雪山一脈獨有的白麻長袍,除了珍妮姐是一個異類不過這一次倒是沒有cos什麼形象,只是穿的比較時尚火就是了。
而來人中,除了珍妮姐和那個掌門,我是一個人都不認得,只是看出來進來的所有人中臉上都帶著疲憊的神。
但就算疲憊,也不能掩蓋這一群人強大的氣場這是一群非常厲害的強者,就算不是個個都是珍妮大姐頭那種頂級強者那一類的,也不是我和師父在平常的狀態下能比的。
之所以說平常的狀態,因為我已經認同了一點,那就是我和師父是‘怪’,總是在看似絕境的局面中,發出難以置信的力量。
看著這麼一群人進來,我做為小輩,自然也是要有禮節的我雖然虛弱,但是站起來還是沒有問題的,這樣想著我又怎麼好再賴著師父,趕從床上爬了起來,四找著鞋子,就準備站起來。
但就在我還在找著鞋子里,這群人,就包括珍妮大姐頭在,竟然齊齊的朝著我一拜然后整齊的對著我喊了一聲:“掌門。”
“啊?”我兀自的還沒有反應過來,整個人都愣住了,連一向厚臉皮的師父面對這個陣仗也有些不好意思,喃喃的說到:“剛才你們才用自己的力量救了承一,怎麼”
是這些人救了我?怪不得我從中出來,如此虛弱混的況,到如今覺也沒過多久,就能醒來出了還有些虛以外,竟然沒有大礙了。
“敲破祈愿鼓,能從雪山一脈地下中走出的人,就是雪山一脈的主人也就是雪山一脈真正的掌門。就算老夫也只能是副掌門,在沒有真正主人的況下,代為管理雪山一脈。只要是雪山一脈的主人,每一句話,雪山一脈的每一個人就算赴湯蹈火也必須做到。這就是祖訓。不用把我們救命之恩記掛在心上,從走出地下那一刻,承一就是雪山一脈的主人,我等盡當盡全力救治,而雪山一脈的資源,也當毫不保留的用在掌門上。我等期待掌門帶領我雪山一脈,再次走向不同的高度和巔峰。”說完這番話以后,之前那個掌門對著我的神更加的恭敬,似乎彎腰也彎的更低了一些。
Advertisement
“我等期待掌門帶領我雪山一脈,再次走向不同的高度和巔峰。”結果,他的話剛落音,其它的雪山一脈的人也是這樣說了同一句話,也同時把腰彎的更低了一些。
這些我和師父徹底的愣在了當場其實,說到底,我本就沒有想要當什麼雪山一脈的主人,我的想法簡單之極,就是希這一次和楊晟避免不了的戰斗,能夠獲得雪山一脈的支持,然后能夠制其它的勢力罷了。
再說,我一個修為悠閑,在修者中還算年紀很輕的小子,又何德何能帶領雪山一脈走向另外一個巔峰?那不是扯淡嗎?我只是有些愧疚的想,一番大戰過后,雪山一脈怕是要削弱不,那
這樣想著,我趕抬頭,也顧不上穿鞋,去一個個的拉那些雪山一脈的長老起來無奈他們本就不,我很急的辯解到:“我敲破祈愿骨只是一個意外,其實我”
“承一。”這個時候珍妮大姐頭站直了,帶著一些嚴厲的看著我,然后再次出的酒壺喝了一口酒。
對于珍妮大姐頭我是十分敬重的,用這樣的樣子看著我,說明是有很鄭重的話要對我說,我哪里還敢做別的事,立刻用同樣鄭重的態度看著珍妮大姐頭。
“呼”喝了一口酒的珍妮大姐頭長舒了一口氣,這才對我說到:“承一,你就不要在推什麼了。你以為雪山一脈如此大的一個世門派,會把自己的命運當做是兒戲,通過兒戲的方式再到一個不可靠的手中嗎?你可還記得山門里的那三座雕像?”
珍妮大姐頭看著我,態度越來越嚴肅。
山門里的三座雕像,我怎麼可能不記得?怕是每一個來過雪山一脈的人,都會印象深刻吧兩道一僧,盡管只是三座雕像,那磅礴大氣的威嚴模樣,自然融合的瀟灑作是那麼的真,僅僅只是從三座雕像上,你就能覺到一種力量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接近天地的力量。
Advertisement
而在珍妮大姐頭的話中,我想起了那三座雕像忽然又想起了在中的一件事,立刻轉在我睡的床上翻找起來還好,那一把我進之前那個守老人給我的銅錢劍還在床上。
我從床上抓起了那把銅錢劍,遞到了珍妮大姐頭面前,有些激的說到:“三座雕像,其中有一個在銅錢劍里。他才是雪山一脈真正的主人之一吧。”
我剛說完這句話,在場所有雪山一脈的人都站了起來,著,大家都哈哈哈的笑了起來我拿著銅錢劍,被笑的莫名其妙,然后之前那個掌門看著我,頗有深意的說到:“既然你還能見到我們雪山一脈的老祖,更加說明你就是那個緣定之人,珍妮這雪山一脈的事還是你簡單的說與我們這個小掌門聽一下吧。我等要先上去,準備一個大典,宣告天下,雪山一脈主人之一出現的事另外,掌門在之中消耗的過多,也需要珍貴的藥材配合一定的方式來彌補,所以你不要耽誤太久的時間,盡快的說明,帶著掌門上來吧。”
說完這番話,雪山一脈的掌門就要離去而我心中一,忽然想起了一件事,立刻開口說到:“那個掌門。”
那掌門回過頭來,無奈的看著我,說到:“你才是掌門。”
我有些心急的抓了一下頭,說到:“先別管這個了,我是想說,如果有什麼大典,可不可以延續到三天以后再舉行?”
那個掌門頗有深意的看了我一眼,竟然很簡單的沒有問為什麼,只是說到:“一切但憑掌門吩咐。”然后就離開了。
我松了一口氣,如果他要問起為什麼,我反倒不好解釋想著這件事,我心中又有些傷起來,道子說過,只能憑借自己的力量,保證我三天的意志獨立,而在三天以后,融合的過程就會不可避免的開始在這個過程中,無論我和道子都不可能再是獨立而完整的意志而在這之后,我是注定失敗那個,能留存下來的一定是道子。
Advertisement
也就是說陳承一只有3天的時間還能完整的在這個世上,剩下的道子將帶著我的‘愿’,姑且就稱之為‘愿’吧,繼續完我未完的事。
試想,如此寶貴的三天,我怎麼能浪費在那什麼所謂大典的上?
“為什麼是要三天以后?”那個掌門沒有問我什麼,反倒是師父不放心的追問了我一句我嘆息了一聲,對著師父說到:“師父,三天后,承一一定會給你一個答案,你放心就是了。”
師父的眼神中流著憂郁而我不想再在這三天時間中浪費一分一秒,不想再提起這麼傷的一件事,趕轉頭著珍妮大姐頭說到:“珍妮姐,你說說雪山一脈的事吧?”
珍妮大姐頭倒是沒有想那麼多,著我很直接的說到:“實際上敲破祈愿鼓,走出地下之人,為雪山一脈之主這件事,就是雪山一脈的創立者,三個老祖留下的訓啊這兩個條件,無論是哪一個都是苛刻之極,我們沒認為會有人會完這兩個條件!卻不想在很多年前就是大能的人,留下的話果然是簡單的說,承一,你只是雪山一脈其中的主人之一你看雪山一脈是兩道一僧在當年創建的那麼雪山一脈新的主人,自然也當是兩道而他們應命在大時代而生,每一個人的出現就伴隨著一個大劫而兩道出現以后,一僧也就會出現,到時候會用無邊念力,為天下蒼生洗滌一定的罪孽。”
我愣愣的聽著珍妮大姐頭的訴說我覺就像是在聽神話。
3846417.html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