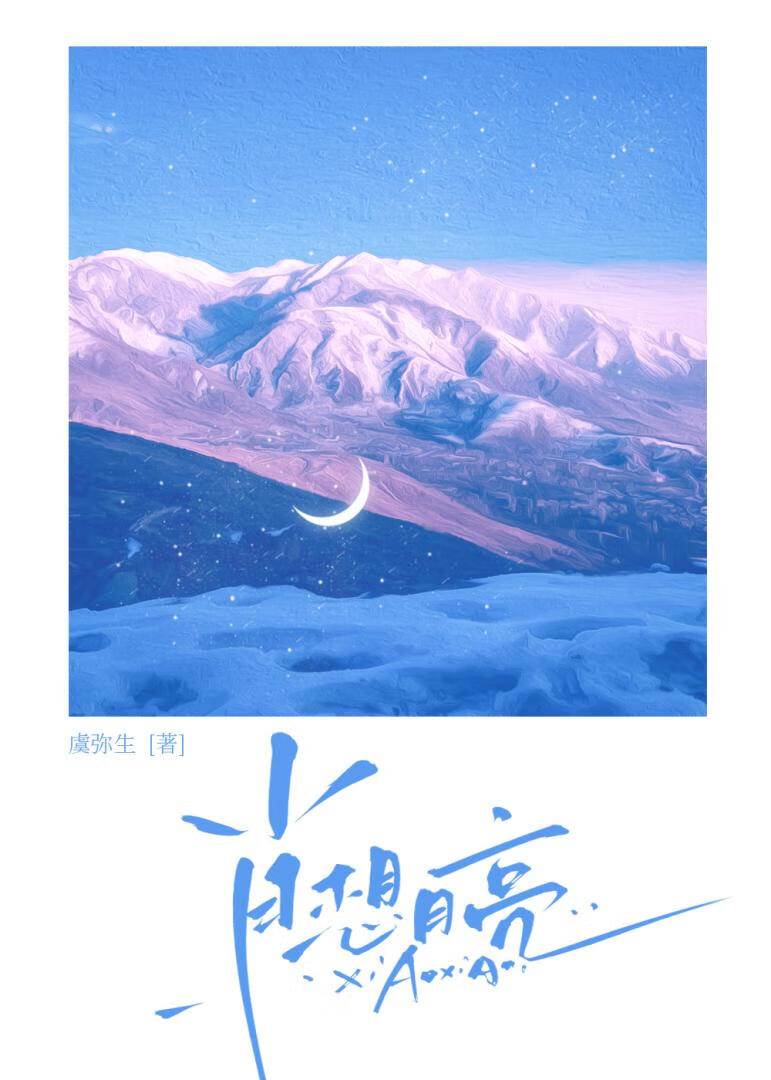《棄妃不承歡:腹黑國師別亂撩》 第144章 野蠻生長
君天瀾默默注視著,那麼小一團,在暗的角落裡,雪花落了滿頭滿,那雙眼倒映出燈籠的亮來,像是世最無邪清澈的明珠。
莫名的,心跳了一拍。
他拿過夜凜手的大傘,大步走向那團一團的小丫頭,“人有無數種生長方式,有的人像是大樹,迎著風雨,無畏生長。”
“有的人像是藤蔓,依附著大樹,盡管羸弱,卻也終會有枝繁葉茂的一天。”
他聲音淡漠,走到跟前,傘麵在頭頂傾斜,將雪花和寒冷都隔絕在外。
沈妙言緩緩抬頭,對那雙燦若寒星的狹眸。
“藤蔓從不必在大樹麵前自卑,因為所有的生長方式,都隻是最適合自己活下去的方式而已。起那些經不起風雨璀璨的弱花朵,本座更喜歡,在下野蠻生長的藤蔓。”
他說著,朝沈妙言出手來。
沈妙言注視著那隻骨節分明的大掌,小心翼翼地出自己小拳頭,放在了他的掌心。
君天瀾收攏五指,的手那麼小,他輕而易舉將那小小的拳頭包覆在掌心。
大雪紛紛揚揚地夜幕起舞,君天瀾一手撐傘,一手握著沈妙言的小手,目視前方,緩步往衡蕪院而去。
沈妙言提著盞羊角流蘇燈籠,仰頭著他的側臉,但見他眼滿是堅定。
寒風將他的大氅吹得獵獵作響,他腳下步子不不慢,那樣睥睨一切的姿態,似是將一切都掌握在手的帝王。
像是到影響般,懦弱的心逐漸堅強起來,同他一道注視著黑暗的前方,尚還稚的小臉,呈現出一有的堅定。
國師啊,再弱小的藤蔓,卻也有一顆變強的心。
總有一天,會不再以依附的形式同他一起,而是以,並肩而立的姿態。
Advertisement
到了衡蕪院,拂接過君天瀾手的傘,抖了抖麵的雪。
君天瀾正要進去,沈妙言拉了拉他的袖,目往院子裡瞟。
他看過去,瞧見院子央,堆著個大雪人,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的,還像模像樣。
“國師待我好,我也想回報一二。這個雪人,送給國師!”
沈妙言麵頰微紅,垂著頭抓了抓擺,最後害般跑進了東隔間。
君天瀾站在屋簷下,看了那雪人良久,想起昨晚答應過陪堆雪人,後來卻又爽約的事,不走下臺階,手拾掇起院的落雪來。
拂和添香愣了愣,瞧見他一臉淡漠地滾了個小雪球,又跟著滾了個更小的雪球,堆在那大雪人邊。
“主子這是在做什麼?”添香好。
拂眼閃爍著點點芒:“在做一個像沈小姐的雪人。”
“啊?!”添香吃驚地看去,果然瞧見君天瀾拿了兩捧雪,在小雪人腦袋一邊兒按了一個,像是沈小姐的倆發團子。
而君天瀾麵無表地在小雪人麵前蹲下,用樹枝畫了個笑瞇瞇的表。
想了想,他又折下一朵梅花,嵌進了那發團子裡。
做完這一切,他退後一步,視線,兩個雪人站在一塊兒,莫名的……
般配。
在拂和添香呆愣的表,他漠然地進了屋子。
良久之後,添香回過神,向那倆雪人,不住捧腹大笑:“主子好可!”
拂嚇了一跳,連忙捂住的,張地朝屋子裡了一眼:“小聲點兒!若是被聽見,又有好果子吃了!”
添香笑嘻嘻的,雙手捂臉,整個人都熱沸騰起來:“啊啊啊,好激,原來這萬年冰山,也有融化的那天!原來老鐵樹,也會有開花的一天!”
Advertisement
而東隔間裡,沈妙言盤坐在小床,雙手捧著七彩玲瓏珠子,圓圓的眼睛裡滿是迷茫。
剛剛國師在門口的那番話,是表白嗎?
是不是呢?
——起那些經不起風雨璀璨的弱花朵,本座更喜歡,在下野蠻生長的藤蔓。
聽起來,明明是表白啊!
臉頰發燙,將珠子拋起來又接住,可是,國師那樣的人,真的會喜歡一個小丫頭嗎?
會不會,隻是單純地說,他喜歡有強韌生命力的人?
珠子拋起來又落下,最後“砰”的一聲,將那珠子丟到床頭,苦惱地鉆進被子,國師他,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夜深了,君天瀾躺在床,在黑暗盯著帳幔頂,狹眸有疑慮浮現。
他是不是,真的太過關心那丫頭了?
他雖不是無無的人,可如欽原所說,他要走的路,常人艱難坎坷百倍千倍。
他,不能讓那丫頭,為他的肋。
這一晚,沈妙言乖乖在自己的被窩睡覺,拂為準備了兩個小暖爐,一個暖手一個暖腳,倒也能踏實睡到天亮。
起床洗漱後,站在窗邊,對著窗臺的銅鏡梳頭。
剛綁好發團子,瞧見院子裡有兩個雪人。
愣了愣,連忙跑出去,一個小小的雪人立在的大雪人邊,發團還簪了朵梅花。
好可!
連忙跑進屋子:“國師,有人在院子裡堆了個好可好可的小雪人,一定是照著我的樣子堆的!”
君天瀾穿大氅,瞥了一眼,聲音淡淡:“沒見過這樣誇自己的。”
沈妙言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國師,你知道是誰堆的嗎?”
“不知。”君天瀾表淡定,繞開抬步往外走。
沈妙言歪了歪腦袋,盯著他的背影,雖然他表現得很平靜,可為什麼怎麼看,怎麼覺得可疑呢?
Advertisement
追去,拉住他的袖:“國師,是你堆的雪人,一定是你!”
“不是。”
“是你!”
“不是。”
“是你是你!”沈妙言嚷嚷著,一邊跟著他往前走,一邊將小腦袋靠在他手臂,“國師最好了!”
君天瀾心微,低頭看了一眼,原想推開,卻忽然抬頭,沖他齜牙一笑。
“笑得真難看,改日請個教習嬤嬤,好好教導你子的禮儀。”君天瀾冷聲。
“不想學。國師昨晚才說,藤蔓有藤蔓的生長方法,很明顯,那些個花朵的養方式不適合我。”
棄妃不承歡:腹黑國師別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480 章
首輔家的美食小辣妻
現代女強人,21世紀頂級廚神,一朝穿越成了軟弱無能受盡欺負的農婦,肚子裡還揣了一個崽崽? 外有白蓮花對她丈夫虎視眈眈,內有妯娌一心想謀她財產? 來一個打一個,來一雙打一雙,蘇糯勢要農婦翻身把家當。 順便搖身一變成了當國首富,大將軍的親妹妹,無人敢動。 但是某個被和離的首鋪大人卻總糾纏著她...... 寶寶:娘親娘親,那個總追著我們的流浪漢是誰呀? 蘇糯:哦,那是你爹。 眾侍衛們:...... 首鋪大人,你這是何必啊!
90.3萬字7.73 79420 -
連載227 章

訂婚被拋棄,她和京圈太子閃婚了
【先婚後愛 追妻火葬場 甜寵 雙潔】訂婚前三天,陸承澤拋下簡瑤去找小白花,揚言訂婚當天趕不回來。簡瑤一夜宿醉後,攔住了路過的京圈太子爺,“和我訂婚吧。” 所有人都知道陸承澤是簡瑤的命,認為簡瑤隻是賭一時之氣,等著簡瑤低頭認錯,委屈求全的時候。她低調的和顧知衍訂了婚,領了證,不動聲色的退出陸承澤的生活。再次相見,昔日的天之驕子跌落神壇。陸承澤將簡瑤堵在走廊,眼眶發紅,“瑤瑤,我知道錯了,再給我一次機會好不好?”簡瑤來不及說話,纖細的腰肢已經被人攬住,男人目光清冷,聲線冷寒,“抱歉,陸總,我太太渣男過敏,不方便開口。”
40.8萬字8.18 18753 -
完結211 章

歲晚新婚
宋唯被裁員回到家鄉,親戚馬不停蹄介紹了個相親對象,叫陳橘白,說是容貌上乘收入可觀,溢美之辭張口即來。 見過幾面,彼此印象還行,親戚竄掇着再接觸接觸,宋唯無奈應下。 陳橘白其實不太符合宋唯的擇偶標準。 她希望另一半能提供陪伴、照顧家庭,但創業期間的陳橘白似乎壓力很大,時常加班。 她希望另一半溫柔體貼、耐心細緻,但陳橘白好像沒談過戀愛,不會哄人也不體貼。 痛經痛到起不來床的那個晚上,本應在外地出差的男人趕來,笨拙又慌張地問:“是不是要多喝熱水?我去燒。“ 宋唯一愣,接着抿起脣笑,“陳橘白,你好笨吶。” …… 後來某天宋唯終於想起,他是她高中學長,入學那年是他幫搬的行李,他當時要了聯繫方式,但他們從沒聊過天。
31.1萬字8 8544 -
連載374 章

京圈太子爺天生絕嗣,我一胎三寶
【霸總+先婚后愛+一見鐘情+甜寵+小可憐+一胎多寶】京市人人皆知,豪門繼承人蕭雪政清心寡欲,潔身自好,二十八歲身邊從沒有女人,被人詬病是不是性取向有問題。 可誰知一夜錯情后,他身邊多了個小嬌妻,小嬌妻還懷了他的寶寶! 一開始,嘴硬的蕭大太子爺:“你不需要避孕,我絕嗣!” 懷了崽還是一胎三寶的施潤潤委屈地哭了。 后來,化身妻奴的蕭太子爺:“寶寶,是我不對,是我錯了,你打我罵我,就是別打掉孩子,別和我離婚……” —— 蕭太子爺抱著小嬌妻日日夜夜寵,因此施潤潤也收獲了一批小黑粉。 小黑粉們造謠著她在蕭家過的怎麼悲慘,生下孩子后就會被掃地出門。 施潤潤表示真的是冤枉啊! 結婚第一天,爺爺奶奶就送上了上億房產和傳家寶,更放話出去日后蕭家的一切都是她肚子里的小金曾孫的! 她在蕭家也沒被打罵,生下三胞胎后更是被某人抱著親著寵著,揚言要多生幾個孩子!
67.6萬字8 159 -
完結178 章

被渣后,和前任的千億小叔叔閃婚
秦霓裳婚前一個月將自己的繼姐和男朋友季長風捉奸在床,情緒崩潰的秦霓裳撞上了季斯年的車,季斯年看她情緒不好,反問她要什麼補償,秦霓裳驚訝之余隨口說需要一個老公,季斯年當天就和秦霓裳領證結婚,從此前男友成了自己的侄子……秦霓裳冷靜過后自己的莽撞和季斯年道歉,并主動要求離婚,季斯年冷笑:“這可由不得你……” 婚已經結了,季少怎麼可能輕易放她走呢?
29萬字8 87 -
完結21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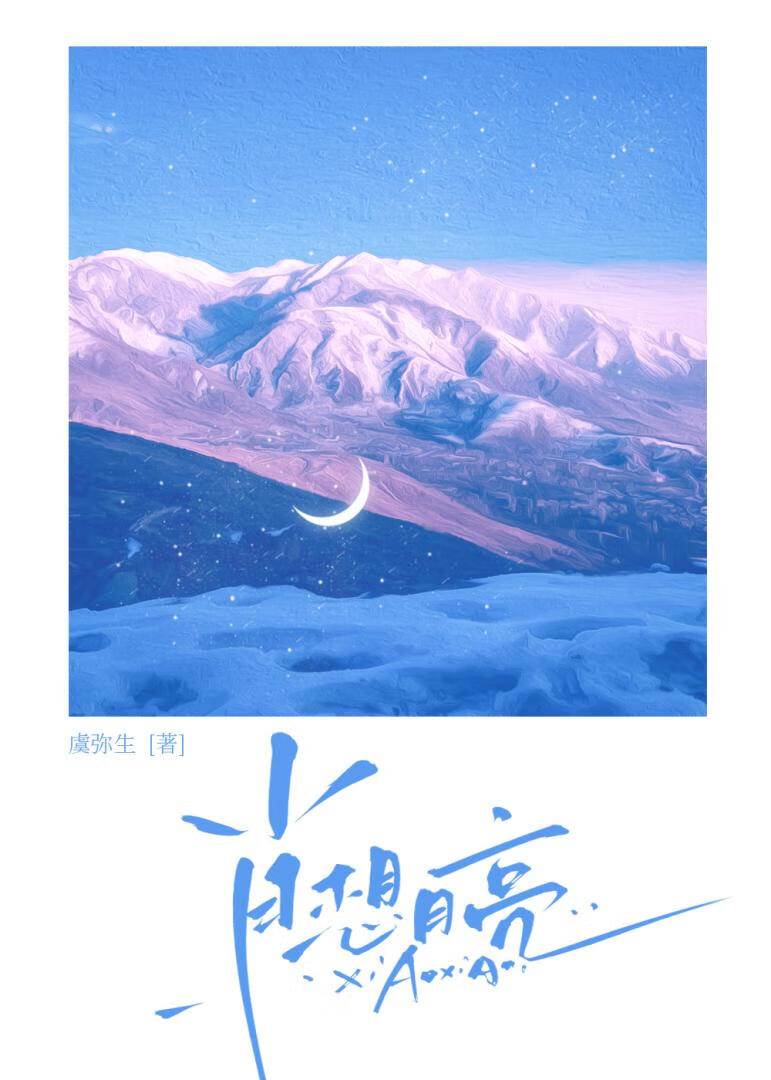
肖想月亮
林應緹第一次見江席月是在養父母的倉庫裏。 少年清俊矜貴,穿着白襯衫,雙手被反捆在身後,額前黑髮微微濡溼。 他看向自己。嗓音清冷,“你是這家的小孩?” 林應緹點頭,“我不能放你走。” 聞言,少年只是笑。 當時年紀尚小的她還看不懂江席月看向自己的的淡漠眼神叫做憐憫。 但是那時的林應緹,沒來由的,討厭那樣的眼神。 —— 被親生父母找回的第九年,林應緹跟隨父母從縣城搬到了大城市,轉學到了國際高中。 也是在這裏,她見到了江席月。 男生臉上含笑,溫柔清俊,穿着白襯衫,代表學生會在主席臺下發言。 林應緹在下面望着他,發現他和小時候一樣,是遙望不可及的存在。 所以林應緹按部就班的上課學習努力考大學。她看着他被學校裏最漂亮的女生追求,看着他被國外名牌大學提前錄取,看着他他無數次和自己擦肩而過。 自始至終林應緹都很清醒,甘願當個沉默的旁觀者。 如果這份喜歡會讓她變得狼狽,那她寧願一輩子埋藏於心。 —— 很多年後的高中同學婚禮上,林應緹和好友坐在臺下,看着江席月作爲伴郎,和當初的校花伴娘站在一起。 好友感慨:“他們還挺般配。” 林應緹看了一會,也贊同點頭:“確實般配。” 婚宴結束,林應緹和江席月在婚禮後臺相遇。 林應緹冷靜輕聲道:“你不要在臺上一直看着我,會被發現的。” 江席月身上帶着淡淡酒氣,眼神卻是清明無比,只見他懶洋洋地將下巴搭在林應緹肩上。 “抱歉老婆,下次注意。”
33萬字8 6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