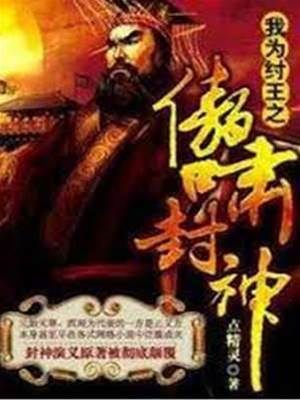《鳳逆九天:一品毒妃傾天下》 第三百九十七章包紮傷口
外麵的雪不知何時停了,月映著皚皚白雪從軒窗投進來,落下一片清亮。書趣樓()這樣萬籟俱寂的夜,一極其細微的聲音在窗欞外麵響起。
即便再困再嗜睡,前世培養了二十多年的警醒意識深固到了的靈魂,水凝煙原本閉的眸子陡然睜開,眸幽寒,側頭睨了一眼軒窗的方向,畔勾起一抹若有若無的弧度,既而再次闔上了眼睛。
頃,窗欞被緩緩開啟,一道黑影從外麵躍進,悄無聲息地來到床榻邊,停駐半晌。黑暗中約可以看到子線條的麵容,麵板瑩白如玉,瑤鼻拔,秀可餐。
水凝煙假寐許久,見對方一直沒有下一部作,心裡疑究竟是何人三更半夜潛房間,又是何目的?
心裡正胡思想著,那道黑影似乎按耐不住,一隻手向床榻之人去,中途似乎又想到了什麼,剛打算撤回,誰料異變陡生。隻見那原本安然睡著的床榻之人忽地起,出手如疾風一般,又快又狠,下一瞬原本靜謐的房間發出一聲慘。
剛喊了一聲,那黑影似乎意識到什麼,強忍住刺骨難當的痛楚,竟是生生地咬牙止住了聲。
「是你?」黑暗中,當水凝煙看清來人那張因過分疼痛而齜牙咧的俊臉時,驚得角狠狠。
「煙兒,你竟然對本太子下如此狠手,嗚嗚。」皇甫鈺頓時可憐兮兮地控訴水凝煙。
水凝煙哀嘆一聲,起,點燃蠟燭,房間瞬間被燭打亮,燭火微微弱弱,輕輕跳躍,卻足以看清房間裡的一切。燭閃爍下,便看到皇甫鈺的手心上赫然多了五繡花針。
「煙兒,若是本太子這隻手廢了,你可得負責了。」皇甫鈺賴皮地往床榻邊一坐,挑著二郎,無比幽怨地說道。
Advertisement
水凝煙看了眼自己的傑作,冷嗤一聲,「皇甫鈺,你還好意思問罪本小姐,三更半夜你站在我的床邊企圖對我手腳的,就算我殺了你,也不為過!」
皇甫鈺不滿地反駁,「什麼手腳的,本太子是看你沒有蓋好被子,所以日行一善,想替你掩好被子,但中途又想到男授不親,所以正猶豫著就被你行兇了。」
水凝煙白了對方一眼,嘲諷道:「皇甫鈺,你三更半夜闖到一個單人的房間,怎麼不想著男授不親了?」
「本太子……」皇甫鈺理虧,被水凝煙一時間堵得無話可說。
說話的空當兩人剛才都沒有注意,水凝煙的目無意間轉悠,登時大驚失道:「哎呀,你的手流了,皇甫鈺,快起來,不要弄髒本小姐的床榻!」
皇甫鈺下意識地去看自己傷的手,臉上的表登時比哭還難看。誰能告訴他,他的手上隻不過捱了五針,怎麼就可以像小噴泉一樣的往外噴呢!
殊不知紮針刺的學問可大著呢,水凝煙原本以為夜闖之人對心懷不軌,所以下手自然就不會輕了,不過好在針上沒有沾什麼見封的毒藥,否則皇甫鈺這會都做了冤死鬼了。
「果然是最毒婦人心,嗚嗚,我的手!」皇甫鈺一陣哀嚎。
「閉,快過來本小姐給你包紮傷口!」
雖說皇甫鈺半夜不請自來,但自己無心傷了皇甫鈺,水凝煙多有些歉疚。於是翻出藥箱,坐在房間的圓桌前開始給皇甫鈺拔針,理傷口。
「喲!」水凝煙每拔下一繡花針,皇甫鈺就誇張地怪一聲。
水凝煙沒好氣道:「有那麼疼嗎?」
皇甫鈺用力地點點頭,水凝煙忍住翻白眼兒的衝,「活該,誰讓你半夜不請自來。幸好我在這針上塗些腐蝕的毒藥,否則你現在整條手臂都得骨架了。」
Advertisement
「你這人怎麼如此狠毒啊!」房間裡明明碳火燒得極旺,皇甫鈺卻到後背一陣冰寒。
水凝煙理所當然道:「三更半夜不請自來,難道我需要客氣?幸好我早有準備,否則要真是遇到什麼歹人,我一個弱質流如何是好?」
皇甫鈺角狠狠一,立即抗議道:「你是弱質流?一百個男人加起來估計也不是你的對手,你是本太子見過最兇殘可怕的人。」
水凝煙說出一句絕對可以氣死皇甫鈺的話,「多謝誇獎。既然如此,你還不離我遠點兒?」
果然,下一刻,皇甫鈺氣得額頭青筋一凸一凸的,恨恨道:「好了,本太子犯賤,自己喜歡找,可以了吧?」
「可以,我沒有乾涉別人的權利。」水凝煙十分平靜地說著,瞥了一眼氣急敗壞的皇甫鈺,聲音依舊無波無瀾,「瞧你眼睛赤紅,肝火旺盛,我這有個方子告訴你,夏枯草二錢、桑葉一錢、花一錢,將夏枯草、桑葉加適量的水浸泡一小會,再用文火煮半個時辰,最後加花小煮片刻,即可代茶飲。可用冰糖或蜂調味。做為老朋友,本小姐就不收你的診金費了。」
皇甫鈺又不是傻子,馬上就明白了對方話中的深意。於是嚷嚷道:「水凝煙,有你這樣的老朋友嗎?大過年的給我送什麼藥方子,你是不是存心咒我呢!」
水凝煙不不慢道:「有病就得治。」
那我有相思病,你給治不治?皇甫鈺了,這句話卻沒有說出來。五年來,這個人在他的記憶裡一點兒也沒有消退過,反而一日一日更加迫切地想要見到。那種想見無關佔有,隻是想看到過得好不好。如今看起來,他暫且可以放心了。
Advertisement
這個人比他想象的還要堅強。五年前承了多大的災難,五年後依舊可以這麼風輕雲淡。越是如此的堅韌不摧,越是激發了他心中的保護。
他派人一直打探,既沒有回到段扶蘇的邊,也沒有去南越國找東方烈,東璃國也沒有見到的影,更沒有再和司徒恭有一糾葛。就像是從整個雲天大陸蒸發掉了一樣。他心裡十分好奇,這五年來這個人究竟在哪裡,又忙些什麼。但是他卻不忍詢問,他怕話一出口,破壞了眼下這份安靜的好。一時間皇甫鈺眼神複雜地著眼前的人。
燭火閃爍下,小心地為他拔針,細心地為他撒葯,心地為他包紮,蛾眉淺蹙,神專註。水凝煙垂頭之際,的青不經意湊近他,鼻息間便縈繞著淡淡的清雅的香氣,不知名的,卻甚是好聞。
都說專註工作的男人看起來最迷人,人又何嘗不是。
燭下給的側鍍上一層淡淡的橘黃暈,如同是筆下繪畫出來的廓,從這樣的角度看,皇甫鈺驚覺,這個人得宛如畫中人。飽滿的印堂下,翠眉優,深邃的眼眶之中,烏眸亮燦。燭在牆上投下迷人的剪影。
皇甫鈺不覺看得有些微微的失神。明明近在咫尺,為何覺他卻覺得離自己那般遙遠,彷彿手一,的眉,的眼,的,的一切便瞬間化空氣。
「喂,好了。」包紮工作告一段落,水凝煙大大地吐出一口氣,出聲道。
皇甫鈺聞聲急忙移開凝視的目,因為害怕被某人發現的緣故,這一舉竟然出了一狼狽。下一刻連自己也意識到了,他不由好笑:想他皇甫鈺風流,即便在公開場合溫香玉在懷,他也是一派從容,如今反倒是越老越純了。
Advertisement
「哦,這就好了啊!」
皇甫鈺聲音裡出一不易覺察的失落,他還想多地看幾眼。低頭看了一眼手背上被包紮的極好看的蝴蝶結,下一瞬角綻開一抹溫暖如的笑意。
水凝煙被無端擾了清夢,此刻哈欠連連,剛準備下逐客令,誰想到房門忽然「吱呀」一聲開了。
房裡的兩人皆是一愣,轉頭看去,隻見有個小傢夥闖進來,圓溜溜的眼珠子瞪著水凝煙和皇甫鈺半晌,目最後又落到了床榻上,有些難過道:「娘親,你是要和這位叔叔生小寶寶,不打算要翎兒了嗎?」
此話一出,水凝煙和皇甫鈺有種被雷劈到的覺。水翎話落,憋著十分委屈地掉眼淚。
「咳咳……小姐。」
這時,青檸從外麵著頭皮進來,抱起水翎安了一番。皇甫鈺回過神,有些驚愕地向水凝煙問道:「這個小鬼剛才你什麼?」
水翎聞言,皺起小臉,十分挑釁道:「是我娘,我是兒子,我水翎!」
皇甫鈺張得極大,水凝煙向他點點頭,表示水翎沒有說謊。皇甫鈺雖然震驚,但是很快便接了接這個事實。他著水翎,故意放聲音道:「水翎是吧?告訴叔叔,你剛才一進門說什麼娘親不要你了?」
剛才水翎開口喊的那聲「娘親」,宛如巨石將他砸得腦袋嗡嗡響,以至於後麵的話他真沒有聽清楚。水凝煙聞言,頓時滿頭黑線,還不及阻止水翎,那小傢夥已經委屈地控訴皇甫鈺的罪行。
「你看,床上都有落紅了,還說你不是欺負娘親,讓娘親給你生小寶寶……」
「噗……」
皇甫鈺瞬間毫無形象地大笑起來,手舞足蹈的。傷的手拍到桌上,痛得他又咧著,卻依舊沒有止住笑意。
青檸也想笑,卻得忍著。今晚伺候小爺安寢,誰想到剛才聽到小姐房間傳來聲,小爺非要也來檢視,誰想等聽到房間裡傳出鈺太子悉的聲音時,想要帶走小爺,小爺卻不依了,趁不備就闖了進來。沒想到小爺的一番話真人啼笑皆非。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367 章
大明最後一個狠人
魂穿越到大明最後一個皇太子朱慈烺的身上,以一個狠字貫穿一生。殺建奴,滅流寇,斬貪官,開海禁,揚國威。這個太子很兇殘,打仗比建奴還可怕,剿匪比流寇還折騰,摟銀子比貪官還徹底。我大明,將士鐵骨錚錚,文人傲骨長存!——大明天武大帝朱慈烺
278.6萬字8 66901 -
完結1548 章

放開那個女巫
程巖原以為穿越到了歐洲中世紀,成為了一位光榮的王子。但這世界似乎跟自己想的不太一樣?女巫真實存在,而且還真具有魔力? 女巫種田文,將種田進行到底。
302萬字8 24526 -
完結49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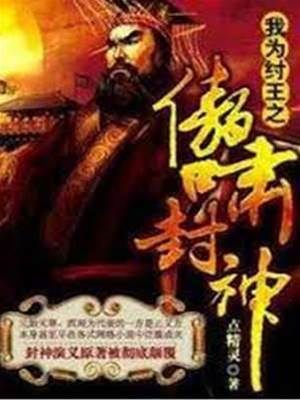
我爲紂王之傲嘯封神
二十四世紀的科學家張紫星在一次試驗意外中穿越時空回到《封神演義》中的殷商末年,以紂王的身份重生,爲改變未來亡國的命運,在超級生物電腦"超腦"的幫助下,新生的紂王展開了一系列跨時代的變革,巧妙地利用智謀和現代科技知識與仙人們展開了周旋,並利用一切手段來增強自身的力量,他能否扭轉乾坤,用事實徹底爲"暴君"紂王平反?楊戩,你的七十二變並不算什麼,我的超級生物戰士可以變化成任何形態!燃燈,你這個卑鄙小人,有我這個敲悶棍的宗師在,你還能將定海珠據爲己有嗎?
190.3萬字8 16803 -
完結442 章

快穿之這任務沒法做了
周幼晚出車禍死了,意外綁定了心愿系統,從此開始了做任務的悲慘生涯。 先有偏執的殘疾王爺,后有不能說一說就炸毛的反派大boss,還有不想談戀愛一心學習的校草。 周幼晚仰天長嘆,這日子沒法過了!
39.2萬字7.73 10308 -
完結1028 章
八零暴富小辣椒
許然太慘了,一場車禍,她從歸國植物學人才變成了八零鄉村小媳婦,新婚當天就差點拿剪子把丈夫給串了血葫蘆! 丈夫老實巴交,有年幼弟妹要照顧,家裏窮得叮噹響,屋頂都直掉渣,關鍵還有奇葩親戚攪合,這農門長嫂真不是人當的! 許然培育果園,研究稀有果蔬品種,她沒有別的念想,只想暴富! 原想做著假夫妻,有朝一日各奔東西,可是沒想到這鄉村愛情津津有味,讓她欲罷不能!
157.1萬字8 5600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