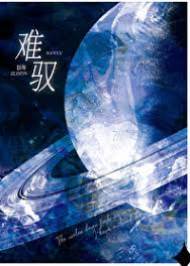《在前夫他心口上撒鹽》 第91章 看他愛不愛得起來
我說:「你們會瞞著我丈夫嗎?」
蘇憐茵肯定代了。
郝院長笑了,圓地說:「不是瞞著他,而是,你有檔案,表示這件事不準告訴任何人。」
郝院長走後,我下床搜尋了一番,隻在櫃裡找到了自己的外套,手機皮包自然不知所蹤。
肯定是繁華拿走了。
剛躺回床上,門就響了。
來人一白,手中端著托盤,赫然是餘若若。
我不由得渾僵直,餘若若則施施然坐到了床邊的椅子上,放下托盤說:「我是來給你送飯的,穆姐姐。」
我說:「謝謝,請你離開吧。」
「怎麼能立刻就離開呢?」笑瞇瞇地起了護欄上的白布條,「我決定餵飽你再走,你自己看,是你自己乖乖配合呢,還是……我費點事,把你綁在這裡?」
我掃了一眼托盤裡的盤子,盤子隻是普通的醫院餐,裡麵放著菜和粥。
以我的視力剛剛當然看不清,這會兒才忽然驚覺,粥碗裡白白的東西正在蠕.!
我連忙扯下懸在上方的呼電話,還沒按下去,手腕就被攥住。
是餘若若。
力氣奇大,作也極快,縱然我拚命反抗,還是被綁在了護欄上。
按病床遙控,擺好姿勢,施施然拿起了粥碗,盛了一勺。
離得近了,那蟲子的模樣更清楚了,是蛆!
剎那間,我的頭湧起了強烈的噁心。
餘若若用勺子攪合著粥,笑瞇瞇地說:「大米粥沒什麼營養,隻有水跟糖,是窮人的東西。所以呀,我特地給穆姐姐帶來了『珍珠米』,這蛆呢,營養富,適口好,吃到裡呀,Q彈,最適合孕期滋補……」
說著,盛起一勺,作勢就要送進我的裡。
Advertisement
我拚命閉,搖頭試圖避開。
勺子被我的得一偏,蛆蟲劈裡啪啦地往下掉。
我能清晰地覺到它們掉進了我的領,順著我的麵板下。
我的頭腦幾乎陷空白,拚命地提醒自己不要尖,因為絕對會直接塞進我的裡!
我能做的唯有咬牙關。
耳邊傳來笑聲。
是餘若若。
「嗬嗬嗬……」笑得得意又燦爛,「至於這麼害怕麼?你知不知道人死了多久會生蛆?」
我不知道。
強忍著尖跟嘔吐的念頭。
「三天啊……隻需要三天,一個活生生的人,就會淪為這些小東西的食。」餘若若的聲音幽幽的,如霧林中冷笑的惡鬼。
「無論你生前多漂亮、多聰明、多能幹、有多人你……都無法阻止你變一灘臭,被它們咬爛,為它們的食跟糞便……」
說著,將勺子放回碗裡,緩緩站起。
然後猛地出手,一把攥住了我的頭髮。
我搖頭掙紮,但無濟於事。
餘若若的力氣太大了,我又如此虛弱。用力一提,我便隻能到劇痛,不得不仰起臉按照喜歡的姿態著。
餘若若瞧著我,臉上帶著笑。
的確長了一張極好看的臉,天真無邪,清純可,笑瞇瞇地看著我,圓圓的大眼睛半彎著,眼中流淌著毒的暗。
與我對視了一眼,然後,舉起了粥碗。
頭頂上傳來溫,白的蛆蟲一腦地掉了下來。
順著我的臉頰下,掉進我的襟裡,在我的上蠕。
溫熱的粘滲進了頭髮,我再也忍不住,張口用力地吐。
耳邊傳來餘若若的聲音,幽幽的,如霧林中的幽靈,「好好跟你未來的夥伴們玩一會兒吧。像仙一樣好的人……真該讓他看看你現在的德行,看他還不得起來?」
Advertisement
說完,丟開碗,轉了。
與此同時,門口突然傳來聲音:「你在幹什麼!」
我吐得眼前發暈,起初無法分辨聲音的來源是誰,直到他忽然來到了我的邊。
我再也聞不到他的氣味兒了,四周隻有那噁心的蛆蟲和嘔吐的槍斃味道。
後麵的事我沒有太深的印象,再醒神時,是因為頭皮上再度傳來了黏!
那黏從頭皮上淌到了臉頰上,順著我的臉頰流過脖頸,最後流進了前襟。
如一隻隻黏的蛆蟲。
我整個人都是懵的,心臟彷彿卡在了嚨裡,震、跳,卡住了我的氣管。
我不上氣,條件反地用手去抓頭髮、抓臉。
抓了不知多久,突然,一隻手握住了我的手臂,耳邊傳來聲音:「別怕,沒事了,已經洗乾淨了……」
那聲音重複了不知多遍,加之我的子被控製住了,漸漸地,被迫冷靜下來。
這才發現,我正站在花灑下。
上的服不知去向,那順著我的髮流到臉上的,是水。
水從我的臉上流到上,最後匯聚到地板上。
混著殷紅的。
水中除了我的赤足,還有男人的皮鞋。
我愣怔地轉過頭,看了過去。
是繁華。
就是他剛剛用手臂箍住了我。
此時他和我一樣站在花灑下,滿臉是水。
我看他的同時,他騰出手來捧住了我的臉,吻了吻我的額頭。
他的冰涼、,吻慢慢地從我的額頭上下,經過眼瞼,來到邊——如一條蜿蜒的蠕蟲。
我開始劇烈抖,反胃陣陣上湧。
我的樣子一定很明顯,繁華鬆開了手。
我推搡了幾下,沒力氣推開他,更沒辦法說話,一張口,隻能幹嘔。
可能是吐到了他上吧……
Advertisement
混合著水流,也看不出什麼。
隻覺到他攬著我,用手掌著我的背,聽到他在我耳邊說:「沒事了,菲菲……」
沖了好久,那種特別噁心的覺總算逐漸消退。
繁華取了塊浴巾裹住我,將我抱出了浴室,放到病床上,解著的襯衫,說:「我去換件服,馬上就回來。」
我低頭看著病床,被褥是新的,但隙裡呢?
一想到這個,就又忍不住開始噁心。
這時,頭頂上覆來一隻手,我僵住,這時,耳邊傳來繁華的聲音:「病房換了,不是那張床了。」
我轉頭看向他。
醋溜兒-文學首發、 他垂眸瞧著我,在我看他的同時,彎下腰,吻住了我的。
猜你喜歡
-
完結91 章

樑少的寶貝萌妻
【暖寵】他,宸凱集團總裁,內斂、高冷、身份尊貴,俊美無儔,年近三十二卻連個女人的手都沒牽過。代曼,上高中那年,她寄住在爸爸好友的兒子家中,因爲輩分關係,她稱呼樑駿馳一聲,“樑叔”。四年前和他的一次意外,讓她倉皇逃出國。四年後,他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而她歸國後成了正值花樣年華。樑駿馳是她想拒絕卻拒絕不
14萬字5 38723 -
完結517 章

婚不設防:帝少心尖寵
日久生情,她懷了他的孩子,原以為他會給她一個家,卻冇想到那個女人出現後,一切都變了。靳墨琛,如果你愛的人隻是她,就最好彆再碰我!
92.1萬字8 67364 -
完結2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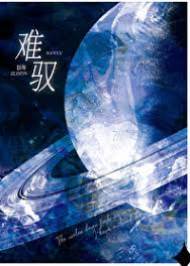
難馭
檀灼家破產了,一夜之間,明豔張揚、衆星捧月的大小姐從神壇跌落。 曾經被她拒絕過的公子哥們貪圖她的美貌,各種手段層出不窮。 檀灼不勝其煩,決定給自己找個靠山。 她想起了朝徊渡。 這位是名門世家都公認的尊貴顯赫,傳聞他至今未婚,拒人千里之外,是因爲眼光高到離譜。 遊輪舞會昏暗的甲板上,檀灼攔住了他,不小心望進男人那雙冰冷勾人的琥珀色眼瞳。 帥成這樣,難怪眼光高—— 素來對自己容貌格外自信的大小姐難得磕絆了一下:“你缺老婆嘛?膚白貌美…嗯,還溫柔貼心那種?” 大家發現,檀灼完全沒有他們想象中那樣破產後爲生活所困的窘迫,依舊光彩照人,美得璀璨奪目,還開了家古董店。 圈內議論紛紛。 直到有人看到朝徊渡的專屬座駕頻頻出現在古董店外。 某知名人物期刊訪談。 記者:“聽聞您最近常去古董店,是有淘到什麼新寶貝?” 年輕男人身上浸着生人勿近的氣場,淡漠的面容含笑:“接寶貝下班回家。” 起初,朝徊渡娶檀灼回來,當是養了株名貴又脆弱的嬌花,精心養着,偶爾賞玩—— 後來養着養着,卻養成了一株霸道的食人花。 檀灼想起自薦‘簡歷’,略感心虛地往男人腿上一坐,“叮咚,您的貼心‘小嬌妻’上線。”
34.9萬字8.18 1070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