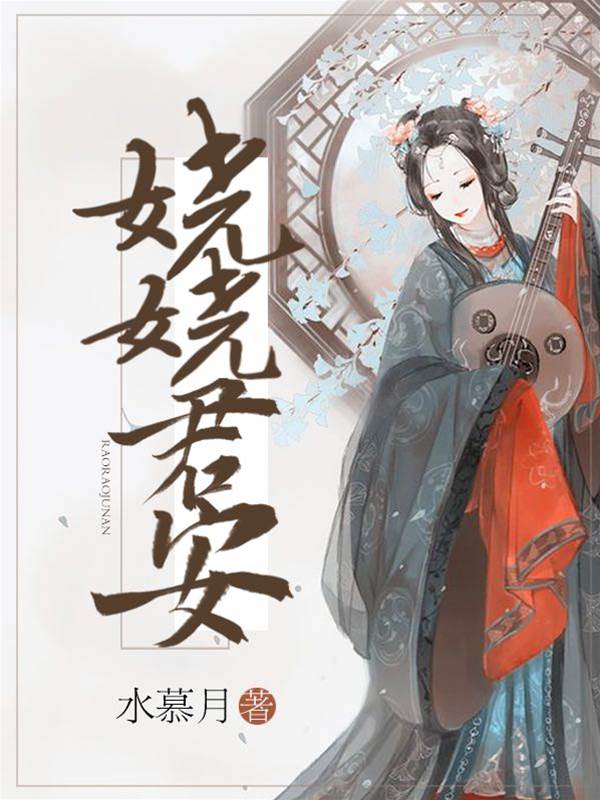《重生妖女策天下》 第六百零八章:孫誌安的瘋魔(洛穆番10)
孫誌安冷哼一聲「幹什麼?你我是夫妻,這六禮之中的敦倫之禮,可是一直都沒有行過呢,夫人不是著急麼?不是急的都忍不住去爬床了麼?為夫哪能讓夫人這麼一直急著呢,當然要來好好伺候夫人!」
孫誌安說的每一個字,都像從牙裡出來的一般,讓梓伊覺膽戰心驚。
「孫誌安!你能不能講講道理,事我已經解釋過了,本不是我說的!現在這青天白日的,你……」
孫誌安冷笑著打斷了梓伊的話「白天怎麼了?白日宣別有一番風味!」
梓伊算是明白了,這孫誌安就是要辱!
梓伊咬了咬,起往外走,沒興趣跟孫誌安在這件事上爭執。
然而梓伊剛走了兩步,就被孫誌安扯著胳膊用力推搡到床上!
咣當一聲,摔的梓伊忍不住頭暈眼花!
「走?!你嫁我孫府,生是我孫誌安的人,死也是我孫誌安的鬼!你想去哪?找平南王麼?對啊……你還是個黃花大閨,確實有資本去爬平南王的床,可過了今日……桀桀桀桀……你就沒這個資本了。」
孫誌安的表仿若瘋魔了一般。
梓伊張的看著他,心驚的問著「你……你要幹什麼?你打也打了,罵也罵了,你到底還要做什麼!」
孫誌安一邊拿起放在一旁的錦盒,一邊獰笑著緩緩開啟,示意梓伊看。
梓伊下意識看過去,頓時滿眼驚恐,麵無。
那是……那竟然是一盒大小不一的玉,勢!
孫誌安開口道「這可是好東西啊,是為夫著頭皮去花樓裡為夫人買的,瞧瞧,這大號的,小號的,中號的,足足有六個尺寸。今兒個,為夫一定將你這個賤人,伺候的服服帖帖的!」
Advertisement
「你瘋了嗎!」梓伊從床榻上站起來,一手揮落了孫誌安手上的錦盒。
錦盒裡麵的東西摔在地上,碎了個七七八八。
梓伊滿眼難以置信看著孫誌安,知道他們之間沒有什麼鶼鰈深,更加沒有什麼相濡以沫。可是在一起生活這麼多年,難道連一點點同住的分都沒有嗎?
他竟然……他竟然敢這樣辱?他竟然要用這種東西來跟行敦倫之禮?
「孫誌安,你這個王八蛋!」梓伊平生第一次罵人,被罵的人麵無表,可自己卻氣得全發抖。
孫誌安看著地上碎了一半的東西,立刻手扣住梓伊的脖子,咬牙切齒道「我想給你留條活路,是你自己不想好,可別怪我手段毒辣!」
「殺了我!你有本事殺了我!士可殺不可辱!」梓伊死死的咬著牙,這一刻似乎恨不能咬的是孫誌安的脖子!
孫誌安獰笑著「殺了你?殺了你我拿什麼去結平南王?殺了你我拿什麼墊腳往上爬?殺了你我拿什麼去賭上外麵那些悠悠之口?梓伊,別做夢了,你死不了!你讓我麵盡失,我就讓你生不如死!哼!」
孫誌安將梓伊甩開,讓重重的摔倒在地麵上,地上那些碎瓷片,不意外的割破了梓伊的手心。
可此時此刻的梓伊,似乎完全覺不到痛楚一般,神獃滯目空。
……
孫誌安摔門離去,滿戾氣的離開了後院。
看到孫誌安一臉不悅的的走進前廳,胡溫連忙圍上來「哎呦老爺,您這是怎麼了?快喝杯茶消消氣。」
胡溫是孫誌安從前的書,一同跟隨孫誌安下任到風南縣之後,在風南縣縣衙做師爺。
去年胡溫剛娶了一房媳婦兒,今年媳婦兒就給生了兩個大胖小子,看到孫誌安眼紅的不行。
Advertisement
孫誌安就算上罵梓伊,心裡也遷怒於梓伊,可他卻不得不承認,他們沒有子嗣的原因,追究底,還是在於他。
而這件事對於外人來說是,對於胡溫來說卻不是。
孫誌安推開了胡溫遞過來的茶杯,開口道「走,去悅來居,喝點酒。」
胡溫連忙陪著孫誌安去往風南縣最好的酒樓,悅來居。
……
悅來居。
胡溫點了幾個小菜,給孫誌安滿上酒,主僕二人把酒暢談。
「老爺,要我說啊,這事兒不能怪夫人,這麼多年來,夫人是什麼樣的人,老爺您還能不清楚麼。夫人勤儉持家,平日裡大門不出二門不邁。這外麵對夫人的風評,都是謠言。您想啊,夫人攏共也沒見過平南王幾次不是?」胡溫開口勸說著。
孫誌安一口飲盡杯中酒,然後將酒杯重重的放下,滿腹怨氣混著酒,辛辣苦,沒有半點香醇。
「你知道什麼,那平南王是什麼人,出了名的不近人,他手下跟他出生死的兄弟那麼多,各個都想順著平南王的路子回京述職,可是你看看,平南王去哪家赴宴了?我也沒什麼本事,也沒有在他手下做出過什麼政績,可是我隻是開口客套客套,他就同意來風南縣赴宴,這是為什麼?為了我麼?這是為了那梓伊啊!」
孫誌安說道這裡聲音忍不住拔高幾分。
胡溫連忙開口勸說「老爺,您也說,那是誰啊,那是平南王的,多人想爬床的平南王,遠了不說,就平南王府的左二小姐,就是個難得的清秀佳人,平南王連左二小姐都沒看上,能看上嫁了人的夫人麼。」
孫誌安冷哼一聲「別人不知道,你還不知道麼?你老爺我啊,就是個沒用的人,讓那梓伊做不了真正的人。那梓伊現在還清白著呢,怎麼就沒有一爭之力了?」
Advertisement
胡溫嘆口氣,左右看看低聲音道「老爺,上次的藥方,還是不好使麼?」
孫誌安皺眉搖搖頭,他都喝了多個藥方了,沒有一個能治療他的不舉之癥。
胡溫繼續道「老爺,那……那玩意兒,試過了麼?這敦倫之禮,也未必非要真刀真槍的來!」
原來孫誌安今日拿去嚇唬梓伊的一盒子玉是是胡溫送給他的。
說起這個孫誌安臉不痛快的神加劇「碎了,都讓那個賤人給摔了!」
胡溫角了「是屬下考慮不周,夫人書香門第,定然於用那些東西。唉……」
孫誌安一杯酒接著一杯酒的喝著,口中喃喃道「的心啊,早就不在我上了,如今的人也快不是我的了,胡溫,你說說我娶有何用啊!」
胡溫抿了抿,想開口勸說兩句,卻也知道自己這個老爺是個偏執的人,本不會聽勸的,便岔開話題道「老爺,如今外麵都在傳老爺是天閹之人,這事兒……」
孫誌安苦笑「這事兒我能怎麼辦?除了厚著臉皮撐,我還能做什麼?現在隻盼著那平南王真的對梓伊有心思,這樣說不定,我還能利用,讓自己離開這個鬼地方。」
胡溫眼珠子轉了轉開口道「老爺,這麼多年來,您都守著夫人一個人。您有沒有想過,會不會是您對夫人不興趣啊?要不咱麼換個試試?」
孫誌安抬眸看向胡溫,有些疑道「何意?」
胡溫笑了笑「老爺,這家裡老婆啊,就像這一桌酒席上的白米飯,不可或缺,卻食之無味。外麵的姑娘呢,就像這滿桌佳肴,各有千秋,都是珍饈味啊!」
孫誌安立刻明白了胡溫的意思,可是……
「本是風南縣的父母,豈能去那煙花之地,若是被旁人瞧見了,外麵的風言風語指不定更難聽!」在風南縣的這幾年,孫誌安還是十分潔自好的,生怕自己的一時疏忽,影響了仕途。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042 章
農家小少奶
穿越成小村姑?好吧,可以重新活一次。 吃不飽穿不暖?沒事,姐兒帶你們發家致富奔小康。 可是,那個比她大七歲的未婚夫怎麼破?本寶寶才八歲,前不凸後不翹的,爲毛就被看上了? 退婚,他不肯;想用銀子砸他,悲催的發現,她的銀子還沒有他的零頭;想揭秘身份以勢壓他,那曾想他隱藏的身份比她牛叉一百倍!婚沒退成,反被他壓… 本文一V一 求收藏求抱養 已有完結文(親孃不
96.7萬字8 235303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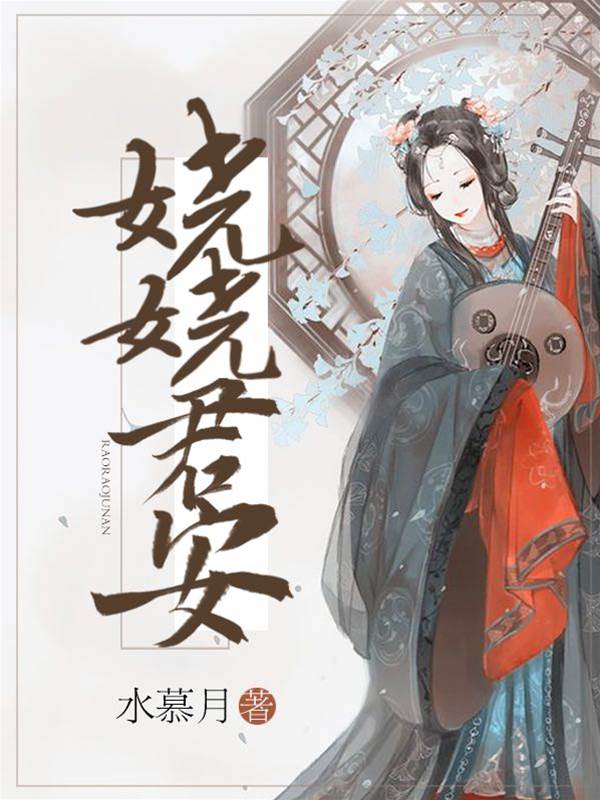
嬈嬈君安
原想著今生再無瓜葛,可那驚馬的剎那芳華間,一切又回到了起點,今生他耍了點小心機,在守護她的道路上,先插了隊,江山要,她也絕不放棄。說好的太子斷袖呢!怎麼動不動就要把自己撲倒?說好的太子殘暴呢!這整天獻溫情的又是誰?誰說東宮的鏡臺不好,那些美男子可賞心悅目了,什麼?東宮還可以在外麵開府,殿下求你了,臣妾可舍不得鏡臺了。
16.6萬字8 14823 -
完結152 章

本王在此/與鳳行
身為魔界銜珠而生的碧蒼王,沈璃的一生是璀璨而奪目的但在她千歲誕辰之際,政治聯姻的魔爪劈頭蓋臉的撓過來九十九重天上的帝君一紙天書頒下著碧蒼王與帝君第三十三孫拂容君定親拂容君早年便因花心而聞名天外她堂堂魔界一霸,一桿銀槍平四海戰八荒,豈能嫁給那種花心草包!這婚必須逃!沈璃不想,這一跑還真碰上了那個不屬于三界五行的男子那男子,當真……奇葩
25.2萬字8 2610 -
完結137 章

乖!嬌嬌別逃!瘋批暴君低啞纏哄
【又名《嬌鳳歸鸞》】【雙重生+雙穿越+病嬌+雙強+團寵+甜寵爽文】 前世慘死穿越去現代后,云梨竟又穿回來了,睜眼便是洞房花燭夜! “阿梨……你為什麼不能試著愛我?” 病嬌攝政王掐著她的腰,眼尾泛紅,發誓這一世也要用命寵他的小嬌嬌! - 世人皆知,暴戾攝政王娶了個草包。 卻沒料到,夜夜在王爺榻上撒嬌耍賴的禍國妖妃,對外卻是明艷驕矜的打臉狂魔! 翻手為醫,覆手為毒…… 不僅前世害她滿門覆滅的人要血債血償,天下英才更是對她甘拜下風! 就連小皇帝也抱緊她的大腿,“嬸嬸如此厲害,不如將那攝政王丟了吧。” 某攝政王:? 他不悅地將小王妃摟入懷,“聽聞我家小阿梨想造反,從此妻為夫綱?” 云梨摟著病嬌夫君的脖頸,“有何不可?畢竟我家夫君的小字比阿梨還要可愛,對吧……容嬌嬌?” - #夫君總把我當小嬌嬌,怎料嬌嬌竟是他自己# - 封面底圖已獲授權:十里長歡-瑞斯、儲秀云心-蟬火。
23.5萬字8.17 113 -
完結107 章

困春鶯
溫幸妤打小就性子呆,脾氣軟。 唯一幸運的,是幼時蒙定國公府的老太君所救,成了貼身婢女。 老太君慈和,經常說:“等幸妤滿十八,就許個好人家。” 溫幸妤乖乖應着,可目光卻不由看向了窗外那道神姿高徹,瑤林玉樹的身影。 那是定國公府的世子爺,京城裏最矜貴多才的郎君,祝無執。 也是她註定靠不近、撈不着的寒潭月影。 —— 溫幸妤出府不久,榮華百年的國公府,一夜傾頹,唯剩祝無執被關押在大牢。 爲報老太君恩情,她千方百計將祝無執救了出來,頂了將死未婚夫的身份。 二人不得不拜堂成親,做了對假夫妻。 她陪他復仇雪恨、位極人臣,成了人人欽羨的攝政王夫人。 可只有溫幸妤自己知道,祝無執一直對她頗爲嫌棄。 她雖委屈,卻也知道假夫妻成不了真,於是放下和離書,遠走高飛。 —— 祝無執自出生起就享受最精細的侍奉,非白玉地不踏,非織金錦不着。 他是目下無塵的世子爺,是孤高自許的貴公子。 直到家族傾頹,被踩入泥塵後,救他的卻是平日裏頗爲嫌棄的呆笨婢女。 爲了掩人耳目,他成了溫幸妤的假夫君。 祝無執看着她掰着指頭算還有幾天口糧,看着她面對欺凌忍氣吞聲,唯唯諾諾。 一副沒出息的模樣。 他嫌棄她粗鄙,嫌棄她呆笨,嫌棄她因爲一捧野花就歡欣雀躍。 後來他做探花,斬奸佞。先帝駕崩後,挾幼帝以令諸侯,成了萬萬人之上的攝政王。 世人都說,他該娶個高門貴女。 可祝無執想,溫幸妤雖呆板無趣,卻勝在乖巧,他願意同她相敬如賓,白頭到老。 可等他收復失地回府,看到的卻是一封和離書。 —— 小劇場: 在外漂泊的第二年,溫幸妤累了,決定在雪城定居。 那夜大雪紛飛,寒風肆虐,她縮在被窩裏怎麼也睡不着。 忽而聽得屋門被人敲響,她恐懼之下提了刀,眼睜睜看着劍尖入縫挑開門閂,門倏地被風吹開。 冷風夾着細雪灌進門內,她用手擋了擋,擡眼看去。 只見那人一身與雪同色的狐裘,提燈立在門外,眉睫結霜,滿目偏執瘋狂。 “敢跑?很好。”
39.7萬字8 9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