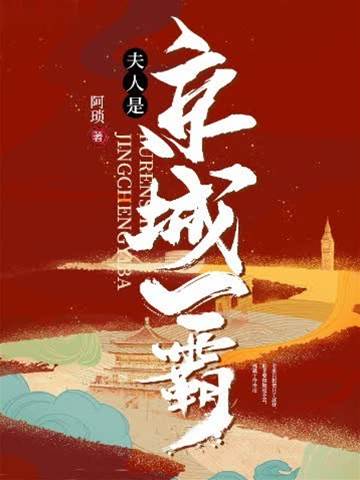《重生之衣冠嫡妻》 第七十七章我不害怕(三更)
「對了,還有乾淨全新的紗布、剪刀、小型的鑷子和鉗子數把、托盤也一塊加鍋裡煮沸,記住,等到了時間撈起來時不要用手,要用鍋中煮沸過的鑷子夾起來……」
「還有棉花,出去弄點新鮮的棉花,挑出裡麵的雜質弄乾凈,然後再開一鍋水煮這棉花,一刻鐘後撈起小團烘乾,速度要快。」沒有苛鈉這種化學用品加進去消毒,一切都隻能將就了。
「……」
那侍聽得一愣一愣的,不過能為在屋裡侍候的大丫鬟,在記事方麵還是有兩把刷子的,陶姚說的東西都不理解,但這不妨礙強記下來,隻是,「譬如什麼小鑷子和鉗子要去哪兒找?沒這東西啊……」
陶姚有點想要額了,之前為了譚夫人生產是特意準備了手械,可惜譚老爺還沒有做好給,現在這是突發事件,沒有條件,創造條件都要上,人命關天,做不到因為環境的製約而放棄兩條生命。
細思了一會兒,直接就道,「去找天香樓的掌櫃問他可有這些品沒有,隻要能代替使用就可以。」
這兒是酒樓,總要給鴨等吃食除絨,這樣總要用到一些小鉗子或者鑷子等鋪助,其他的東西,找掌櫃準沒錯了。
「啊?」那侍張大了,真能這樣?
「對,趕去,別耽擱。」陶姚不想浪費時間,直接就板著臉指著門,「快去。」
那侍也是個人才,不再追問,而是直接就飛奔出去。
外頭湊到門口張的鄒妍就差點被這侍撞了個滿懷,這侍一看自家小姐的臉鐵青,頓時心虛得就想要跪下認錯,不過想到陶姚剛才那急呼的一聲「快去」,就顧不上認錯,直接朝小姐鞠了一躬,然後就飛奔下樓去找天香樓的掌櫃。
Advertisement
「這急匆匆的準備去投胎不?」鄒妍不悅地罵道,不過這蓮香是大嫂鍾秀的侍,現在由不得來發作,遂隻能抿生悶氣。
屋裡的傅瑤和鄒晨都聽得一愣一愣的,這準備的一大堆東西都做什麼用的?不是說要剖腹嗎?怎麼還不開始?
哪知陶姚非但沒有向他們解釋,而是邁步走出產房,朝外麵的人喊道,「韓大夫。」
「小姑娘,我在。」韓大夫不敢走開,他擔心陶姚的安全,萬一有個閃失,也不知道鄒家人會不會遷怒於?
「你去醫館抓以下幾味葯,生川烏、生草烏、蟾、生南星、胡椒上藥各等份,研細末,快去準備,讓他們速度快點,我一刻鐘之後就要用到。」陶姚直接就給他下達了任務,而且必須是儘快準備的。
另一旁鄒家請來的大夫聽到陶姚這幾話,眉頭皺了皺,他家祖上就是行醫的,據他家老祖傳下來的醫書裡麵就有記載這幾種草藥的方子,這是手時麻醉用的,看到一旁據說也是大夫的鄉下人不停地點頭,他不打量起陶姚,這小姑娘一看就才十來歲,居然也懂麻醉之事?
他在青雲鎮上行醫,很聽人提起這麻醉方子,畢竟現下行醫並沒有多人會刀子,他祖上流傳下來的醫書也隻是寥寥記載了幾句,遂上前道,「你要給裡麵的鄒夫人開腹取子?」
陶姚看了眼這突然冒出來穿青布衫的中年男子,再看了下他背著的藥箱,遂點頭道,「正是,鄒夫人的況耽擱不得,不然就是一兩命,你也是大夫,應該明白我的意思,救死扶傷乃醫生的天職。」
中年男子點點頭同意的說法,他深深地再看了眼陶姚,然後直接就與韓大夫說,「我家醫館就在這附近,你且隨我去取,一刻鐘後,我必定會送來。」
Advertisement
陶姚被他鄭重的語氣嚇了一跳,看到他眼裡的堅持,也鄭重地點點頭,「拜託了。」
中年男子回以一禮,然後帶著韓大夫急速就離去。
陶姚慨這個時代雖然是封建了一點,但人心也不全是壞的,一如韓大夫,一如那中年男子,都是品德高尚的人。
重新折返回屋子,看到傅瑤與鄒晨走向,似乎看出他們母子倆眼裡的疑問,「還沒有準備好械,不能貿然開始。」再看了看這一屋子的人,這造空氣十分的不流通,半點也不利於產婦生產,遂又道,「除了鄒公子,這位嬤嬤,還有這幾個侍,其他人都先出去。」
的手指著之前問過的鐘秀的孃,看得出來這位是真的關心產婦,比在場的其他人都要強得多。
「我也要出去?」傅瑤不可置信地手指了指自己,可是鄒家的當家夫人。
「請先出去,鄒夫人,這也是為了產婦好,為了你的嫡長孫順利來到世上,請你配合。」陶姚之所以要趕傅瑤出去,就是不想這傅瑤在這裡影響到產婦的心,婆媳之間總會有點,鄒夫人估計不會希在生產時看到婆母守在這兒。
「娘,你先出去,這兒有我即可。」鄒晨道,既然已經選擇了陶姚這不知底的人,他就沒有了退路,直到現在為止,這小姑娘還是靠譜的。
那倆穩婆不想出去,們想留下觀看這小姑娘是不是真的可以開腹取子而不傷產婦的命,畢竟是這做行的,多學點總沒壞的。
陶姚卻是不給們這個機會,如果在這裡的衛娘子或者是心正的穩婆,並不介意教別人,可這倆人就沒給好印象,更怕們看了一點隨便就用上,然後畫虎不反類犬,隻怕會害了更多產婦和嬰兒的命,所以這兩人是一定要出去的。
Advertisement
鄒晨現在全都聽陶姚指揮,他直接不客氣地開口趕人,「出去。」
這兩人若有本事,早就能協助他妻子生下孩子,結果現在害得他妻子必須要剖腹取子,他對這倆穩婆就沒有半點好,「出去。」
倆穩婆聽到這怒喝聲,頭皮一發麻,了脖子,就跟著其餘人退了出去。
屋子裡了許多人,空氣變得清新了許多,陶姚讓人去把窗戶開啟通一下風,也讓屋子裡的悶熱散去一點,然後再讓人去找掌櫃的再上兩盆冰來降溫。
等事安排得差不多了,看到鄒晨又握著妻子的手安,夫妻二人都默然地看著對方,似乎怎麼也看不夠,的心裡突然有點發酸,手慢慢地握拳,然後又鬆開,告訴自己一定要功。
在開始手前,再一次給鄒夫人檢查,又問了一下今日吃過什麼等諸如此類的,一來分散的注意力,二來也是要瞭解的基本況。
況稱不上好,但也沒有更壞,陶姚在心裡盤算是下刀的位置,必須要儘快將胎兒取出來,不然那量的羊水是不足以讓胎兒生存的。
好在一刻鐘後,吩咐的東西陸續送進來。
先是那名蓮香的侍端著托盤進來,陶姚看了看裡麵東西,那鑷子和鉗子果然是小巧的,估計還真是用來拔鴨的,至於其他的品也隻能將就了,遂,點了點頭,心底對天香樓的掌櫃點了個贊,辦事能力還是不錯的。
然後另一侍端著烘乾的新鮮棉花進來,已經按的吩咐一小團一小團的,這也方便取用,也點了下頭,不錯,差事辦得還行。
幾盆溫水陸續端了進來,然後就是度數極高的烈酒,最後一個到達的是奔跑得滿頭大汗的韓大夫和那中年男子。
Advertisement
中年男子直接將一包細末給陶姚,咧一笑,「幸不辱命。」
「謝謝。」陶姚鄭重地道謝。
中年男子擺擺手,他覺得自己也沒出多力。
「快進去吧。」韓大夫擔心耽擱時間久了,產婦和嬰兒會有危險。
陶姚也不再遲疑,拿著藥包進去,親自取來小碗倒出烈酒和著細末,然後走回鍾秀的邊,拿起一把鑷子夾著棉花蘸上小碗裡的,輕輕塗抹在鍾秀的肚皮上,塗得很仔細,將即將開刀的範圍都塗了個均勻。
不過這種麻醉的方子,還是第一次用,也不確定這玩意兒麻醉的效果會不會如異時空的麻醉劑那般,所以還是吩咐鄒晨拿個木塞塞到鍾秀的裡。
在等麻醉生效的時間裡,又做了一些別的準備,然後纔看向鍾秀道,「我想你應該也知道了,我要開腹取下你腹中的胎兒,你怕不怕?」
鄒晨握妻子的手,他心裡害怕,但他不敢表現出來,低頭在妻子的手背輕輕一吻,恨不得代這份罪。
鍾秀本來是十分害怕的,再如何也還是個才剛剛雙十年華的人,可是看到邊的丈夫,再想到他們的孩子,突然就不再害怕了,遂搖了搖頭。
陶姚輕輕拍了下的手,「我們一起努力。」
鍾秀點了點頭,臉上出了誓死如歸的表。
陶姚沒有再說什麼,而是朝豎了一個拇指鼓勵。
手前,再重新拿起香胰子仔細洗自己的手,然後朝一旁的侍蓮香道,「你看著我如何洗手,待會兒你也得把手洗乾淨了,給我遞工。」教過蓮香如何遞工給,這侍還是著機靈勁兒的,是個做護士的材料。
蓮香點了點頭,學著陶姚那般挽起袖子洗手,仔仔細細地,半點疏也沒有。
這個簡陋的床上其他的東西譬如帳幔什麼的都被陶姚扯掉了,如果有條件還想要換張消過毒的床墊,可時間有限,由不得再一一去準備。
直接在床尾坐下,而產婦已經調整好方位,方便待會兒手。
屋子裡的線不太充足,直接就讓人舉起點燃的蠟燭做照明。
一切準備就緒後,算了算時間,麻藥生效了,直接就手拿起找盤裡麵的短匕首直接就劃開早已選定的區域,鮮湧了出來,朝一旁的蓮香看了一眼,「。」然後抬頭看向鍾秀,看到鍾秀沒有痛苦的表,看來這麻醉藥末還是管用的。
蓮香看到頭有點發暈,胃還有點翻滾,不過還是很鎮定地履行陶姚的吩咐,夾起一塊棉花團就去。
整個手過程鍾秀都沒有覺,有些不可思議,不過心裡開始有幾分擔心自己的孩子是不是真的能取出來?用眼神看向丈夫,丈夫回給一個安心的微笑。
鄒晨的心也在七上八落的,直到聽到妻子的孃發出驚喜聲,「取出來了,是個小公子。」
陶姚直接把嬰兒從母親的子宮中取出來,掏出他裡的異,然後果斷地接過蓮香遞給的剪刀剪斷臍帶,打好結後,這才遞到了鍾秀的孃手中。
孃接過孩子,直接就給孩子去上的跡……
陶姚沒有去管孩子的況,而是仔細謹慎地取出胎盤,然後清理乾淨再將子宮放回腹中的原位,一切都穩妥後,這才朝蓮香道,「針,線。」
蓮香已經不再到頭暈了,果斷地將這兩樣東西遞給陶姚,全程看著陶姚取出胎兒,隻覺得神奇,居然半點也不到害怕,反倒是舉著蠟燭的那幾個侍已經驚駭得麵無。
陶姚鎮定的將開刀的地方上,作一氣嗬,半點多餘的作都沒有,這些作早已爛於心。
等這一切完後,正要鬆一口氣之時,就聽到鍾秀的孃驚慌道,「小公子怎麼不哭呀?」
------題外話------
明天的一更還是在中午十二點鐘左右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78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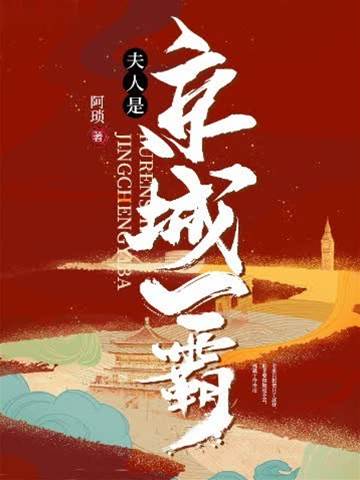
夫人是京城一霸
七姜只想把日子過好,誰非要和她過不去,那就十倍奉還…
123.2萬字8 19066 -
完結2159 章

風華鑒
蕭臣這輩子最不想見的女人叫溫宛,溫宛這輩子最想嫁的男人叫蕭臣,只要蕭臣,別人都不可以!
381.1萬字8 18455 -
完結311 章

夫郎家的贅婿首輔
黎大是西坪村數一數二的富戶人家,妻子早逝,膝下只留了個獨子哥兒黎周周。 「掙那麼多錢有什麼用,只有個哥兒」 「哥兒是要嫁人的,錢都是給了外人了」 黎大將村裡說閑話的罵了回去。 「我家周周是要招上門婿的」
163.9萬字8 16887 -
完結475 章
素手醫妃
亂世風雲,天下將傾,皇子奪嫡; 如姝紅顏,投身其間,攪弄棋局。 人前,她是懸壺濟世的醫者,是救死扶傷的女菩薩; 人後,她是與眾不同的仵作,是開膛破肚的活閻羅。 一把匕首,一段旅途,一場靈魂交融的戀曲; 一抹青衫,一襲玄衣,一本昭雪沉冤的傳奇。
89.3萬字8 13472 -
完結311 章

長春宮
大婚之夜,他狠戾掐她脖子,指著榻上白帕,嘲諷至極:“原來朕的皇後,早已和旁人承歡過?”姬楚雲和裴宴相識了十年,裴宴便恨透了她十年。為了家族安穩,為了後宮和睦,她不得收斂光芒,刻意藏拙,成為了世人口中無才無德的愚蠢皇後。卻終究逃不過那一場他手中的冷宮大火。涅槃歸來。她重生於新帝登位之初,重生於腹中太子未臨盆之時。這一世,她隻為自己而活!裴宴:“你還恨朕嗎?”“臣妾願陛下扶搖直上,翱翔九天。你的天下,沒有我。”(我說這是甜文,你信嗎)
57.2萬字8 16631 -
完結896 章

被嫡姐逼做通房后
玉姣身為庶女,素來謹小慎微。只求有朝一日,遠離高門大戶,嫁與寒門做妻。不料嫡姐成婚多年未孕,她便無名無分的入了伯爵府,替姐生子。嫡姐面甜心黑,把夫妻不睦,多年未曾有孕的怨氣,盡數撒在了她的身上。人命如草芥,玉姣不想再任人攀折踩踏。嫡姐利用她,她便踩著嫡姐往上爬。妾室妒她害她,她便以眼還眼以牙還牙。通房、賤妾、貴妾、側夫人、平妻、寵妃、為后。這一路走來,她被人辜負過,也辜負過人。若問她這一生,可有憾事?玉姣想說:走過的路,從不言悔。
155.5萬字8 976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