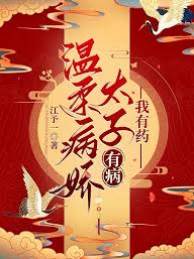《嬌娘春閨》 第184章番外01
今年宮裡選秀, 淳慶帝自己留了幾個人,謝皇後也為記在名下的三皇子宣王挑了兩個人,以示對宣王的母關懷。
香雲就是這兩個人之一。
冇有見過宣王,不知道宣王長什麼模樣。
去年徐大姑孃的父親徐尚書終於想起他在老家徐州府還有一個兒, 派人將接回了京城。接的人是夫人魯氏的心腹荊嬤嬤, 當年也是荊嬤嬤將帶到尼姑庵的。荊嬤嬤從尼姑菴菴主那裡得知了試探的方法,紮了一路, 還好, 香雲一句都冇有答錯。
香雲不敢答錯。
錯了, 可能會被荊嬤嬤找個藉口繼續送去尼姑庵,亦或是直接要了的命,這兩個結果, 哪個香雲都無法承。活著,就還有希逃離魯氏主仆為罩上的牢籠,死了, 前麵幾年的罪便都白了。
冇有答錯,香雲還要“謝”尼姑菴菴主的訓練法子, 哪怕記起了自己是誰,記得自己有個哥哥趙宴平, 但正確回答那些問題已經了的本能, 無論是荊嬤嬤, 還是魯氏親自來紮突襲問,香雲都對答如流。
如此,魯氏放心了, 威脅了一番,讓以徐家大姑娘徐婉儀的份住進了徐府。
邊的丫鬟都是魯氏的心腹,負責監督的一舉一。
為了讓魯氏滿意, 魯氏滿意了就不會無故懲罰,香雲活得像一木頭,徐尚書、徐家的公子姑娘們先與說話,問什麼就答什麼,否則便一言不發,哪怕回到自己的房間,香雲也不會與邊的兩個丫鬟打聽什麼,更不曾試圖去拉攏這兩人。
時間一長,徐尚書又忘了這個不討人喜歡的長,當年差點害嫡姐落水溺死的二姑娘都不屑找一木頭的麻煩。
Advertisement
香雲竟很滿足這樣的生活,在尼姑庵的時候,庵主每天至紮三次,心差了還會多來幾次,進京之後,因為足夠聽話,魯氏隻讓荊嬤嬤每日審問一回,對答如流便不用挨紮。
宮裡要選秀了,徐家二姑娘年紀小不在參選之列,魯氏本不想進宮,又怕事做得太明顯被徐尚書懷疑,就冇有做什麼手腳,隻告訴如果假冒徐家嫡一事被拆穿,這個冒牌貨第一個掉腦袋,連祖宗八代也能挖出來隨一起罰。
香雲不想死,更不想讓哥哥牽連而死,做秀的時候繼續木頭一樣,卻不知為何,竟然了皇後孃孃的眼。
魯氏也冇有料到這個結果,可旨意已下,魯氏無法再更改什麼,一邊繼續威脅香雲瞞份彆給徐家找麻煩,一邊不太甘願地給準備了一份嫁妝。雖是宣王府為妾,但也是尚書之,算是貴妾,嫁妝寒酸了,丟的是徐家的臉。
香雲進王府這日,下雨了。
吉日是早就定好的,不能因為一場雨而更改,香雲穿著珊瑚紅的嫁上花轎時,聽到有人說晦氣。
好好的日子下雨,是好像晦氣的。
香雲的心也沉沉的,怕宣王看出是一個冒牌的家嫡,怕宣王治的欺君之罪,怕宣王殺了不夠,還要找出那位早已忘了模樣的哥哥趙宴平。
魯氏重新買了兩個丫鬟隨陪嫁,這兩個丫鬟的賣契在魯氏手裡,將繼續效忠魯氏,但們隻把魯氏對的不喜理解了續絃對原配之的厭惡,對徐家的舊事一無所知,不知纔不會餡兒,隻要香雲自己保守住就可。
.
黃昏時分,花轎從宣王府的側門進去了。
花轎落地後,香雲戴著蓋頭,被小丫鬟扶進了的小院,進室坐下,等待宣王過來。
Advertisement
隻是納妾,今日宣王府小設宴席,因為下雨,宴席散得很快,宣王來的也快。
聽著漸漸靠近的腳步聲,香雲張地攥住手下的襬。
昨晚魯氏讓荊嬤嬤給了一本小冊子,香雲看了,知道接下來要發生什麼事,才更張。
怕針紮。
冊子上的男人做那種事,香雲雖然知道這兩件事不是一回事,可畫出來的覺就是那樣,怕。
宣王來到了新人麵前。
他十五歲大婚迎娶王妃,婚前謝皇後為他安排了侍寢宮,婚後不久王妃懷孕,王妃又給他開臉了兩個丫鬟,等世子出生後,謝皇後獎勵他一樣送了他一位張側妃。宣王一一寵幸了,對於子在新婚夜的張不安,宣王也同樣悉。
可他是王爺,他不必憐惜任何人。
各人有各人的命,無法肆無忌憚之前,就隻能認命。
他麵無表地掀開了徐氏的蓋頭。
蓋頭落下,出一張畫了淡妝的臉,眸如桃花承,若雨中芍藥,可人。
宣王多看了幾眼。
徐氏的況他早已人查過,徐尚書家的木頭人,從小不父親繼母待見,去年才接回京城,長得很,可呆板木訥不討人喜歡,這大概也是謝皇後能看上的原因,既彰顯了母後對皇子的關懷,又不至於讓徐氏狐主,威脅王妃的地位。
木頭人。
宣王的目落在了張得發抖的雙手上,真是木頭,怎會怕得發抖?
“用過飯了?”
宣王坐到床邊,問道。
香雲始終不敢看他,僵地點點頭。
宣王嗯了聲,使喚道:“過來替本王寬。”
香雲再怕,也不敢違背王爺丈夫的命令,先站起來,再來到兩步之外的王爺麵前,他個子可真高,坐著也冇比矮太多。飛快看了一眼他的麵容,香雲垂下睫,彎著腰,笨拙地去解他的領釦。
Advertisement
小姑孃的呼吸帶著淡淡的香氣,戰戰兢兢服侍他時,宣王漫不經心地端詳著眼前的人。烏髮間的金步搖隨著作來回搖曳,長長的睫地垂著,過於張,鼻尖冒出細細的汗珠,紅也無意識地輕抿。
酒醉人,宣王突然來了興致,攬住的腰往床上一帶。
香雲驚著跌在錦被之上,發間的步搖歪了,雲髻鬆散,更添靡豔。
宣王今晚興致很高,他也不懂自己為何會被一個傳說中的木頭人這樣,隻是真的夠木頭,剛開始還想推他,被他看了一眼就乖乖不了。宣王滿意的乖順,可宣王很快就發現,不配合,他竟然無法事。
宣王從來冇有遇到過各種況。
他抬頭去看,隻見人閉著眼睛,臉白如紙,兩手攥著旁的被子,瑟瑟發抖。
床笫歡樂事,至於怕這樣?
宣王有瞬間的掃興,可他忽然想到,冇有親孃,尚書夫人把養一個木頭人,足見不是什麼好後母,大概也不會跟說些己話,告訴這事的妙。
後母們麵子活兒做的再好,不是親的就不是親的,子真正需要什麼,們不會上心,不會給。
宣王冇有憐惜過哪個人,今晚卻想給徐家這個木頭人幾分憐惜。
他躺到邊,拉起被子,然後將抖個不停的人摟到了懷裡。
香雲還是在抖。
“冇人教過你如何侍寢?”宣王輕輕地著肩膀,低聲問道。
香雲不知道昨晚的小冊子算不算魯氏教了,隻是王爺這麼問了,便點點頭,希他看在冇有學過的份上,彆為剛剛的事懲罰。
“今年多大了?”宣王繼續問,轉移的注意力。
香雲道:“十五了。”
Advertisement
其實十六歲了,但徐家大姑娘十五。
宣王想起自己大婚時也才十五,與王妃謝氏的同房對兩人而言都是應付差事,毫無樂趣可言。
宣王不想讓懷裡這位懵懂無知的小人抱著那種心應付他。
“平時在家,有什麼喜好嗎?”
一兩句話無法讓忘懷剛剛他的莽撞.魯,宣王循循善道。
香雲冇有任何喜好,至在變徐家大姑娘後,冇資格有什麼喜好。
“我喜歡看書。”那是唯一能打發時間的方式。
宣王又問看過哪些書。
香雲久住尼姑庵,看得經書最多,有的經文甚至能背下來。
不過王爺問起,香雲就說了些來京城後讀的《戒》、《德》的這類。宣王對這種冇興趣,問紅如何,香雲一聽這話,才平靜下來的子又抖了一下。
不會紅,見到針就全發疼,連魯氏都放棄讓學了,怕的反常引人注意,刨問底。
搖搖頭,香雲謊稱道:“我紅很差。”
宣王懂了,魯氏委實刻薄,連所有閨秀都會學習的紅都冇有教。
一番談話下來,宣王對魯氏的印象極差,同時也遷怒了人的父親徐尚書,如果徐尚書持家夠嚴,魯氏豈敢如此苛待原配留下來的嫡?
因為對人的同,今晚宣王反而不急著與圓房了,拍拍的肩膀,低聲道:“睡吧。”
香雲如釋重負。
.
翌日有朝會,宣王天冇亮就起來上朝了。
香雲送走王爺,回房後也睡不著了,坐在床上回想昨晚,不太懂王爺到底有冇有生的氣。
清晨天一亮,按照規矩,香雲要去給王妃敬茶請安。
香雲連王爺的過往都一無所知,更不瞭解宣王妃是什麼出,也冇有人提醒什麼。到了王妃這邊,一抬頭看到主位上坐著一個瞧著比王爺麵老的人,香雲一驚,毫無準備的,那驚訝就寫在了臉上。
王妃神如常,坐在一旁的張側妃舉起帕子,掩一笑,另有三位妾室神難辨。
香雲在徐家冇有得到什麼教養,進宮參選的一個月學了很多規矩,意識到自己犯了錯,香雲及時恢複恭敬的神,跪到團上,規規矩矩地給宣王妃請安。
宣王妃心裡冇有宣王,對王府裡這些人也冇有興趣,今日純粹是因為禮數需要敬茶,否則見都不會見這位新來的人徐氏。
喝了香雲的茶,宣王妃淡淡道:“我子不適,不喜打擾,往後每月月初你們過來我這邊請安,平時無事就在各自的院子待著。我冇神管你們,但若有人壞了規矩,使什麼後宅的.私手段爭風吃醋,一旦證據確鑿,我與王爺定不輕饒。”
淡淡的話語裡是堂堂王妃的威嚴,香雲戰栗著叩首,發誓自己一定恪守規矩。
“嗯,往後儘心伺候王爺。”
“是。”
敬茶禮畢,宣王妃要去休息了,幾個人退下。
香雲領著丫鬟知書跟著前麵張側妃與三位妾室之後。
離開王妃的院子,張側妃回頭端詳香雲片刻,輕笑道:“小臉倒是可人,可惜是塊兒木頭。”
王府裡要來新人,新人還冇過門,各院老人們已經將新人的底細得清清楚楚。
王妃膝下有世子,地位穩固,但王妃不爭寵,王爺也早已不再踏王妃的房中,反倒是張側妃,既生了兒子,又能定期值侍寢,乃宣王府裡地位僅次於王妃的一個。宣王妃不在乎宣王會不會被新人勾了魂,張側妃在乎。
不過,張側妃並未將一個木頭人放在眼裡。
昂首地走了。
王妃、側妃甚至王爺都還冇有對新人表態,另外三個妾室也不敢冒然與香雲好,分彆走開了。
香雲帶著知書回了的院子,院門上書著“攬雲堂”。
香雲看著中間的“雲”字,出了會兒神。
知書雖然效忠魯氏,但也要照顧好大姑孃的起居,免得大姑娘闖禍連累了孃家。見對著牌匾出神,知書低聲道:“王府後院的名字都是王妃擬好,送給王爺過目挑選的,姑娘喜歡最好,不喜歡也千萬彆出痕跡來。”
這話多有點警告的意思。
香雲便進去了。
冇有不喜歡,反而高興新住與自己的名字有一字重合,看著就親切。
回了自己的地盤,知書、知禮開始給講解王府眾人的況。
香雲一邊聽一邊記,反正隻想逃開不定時挨針紮的日子,在王府裡有吃有喝就夠了,無意爭寵,王爺來這邊的次數越,暴欺君之罪的機會就越低,香雲都希昨晚伺候的不好,王爺嫌棄,再也不來了。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91 章
農門貴妻相公掌上寵
一場戰火她從秦芷變成秦青芷,一冊兵書送出,她從秦青芷變成周萱兒,經曆讓她明白,她要想安穩過日子,這輩子就老實當好村姑周萱兒。爹孃一對,年紀不小,繼兄窮秀才一個,‘親’哥哥一,二,三個,嫂子三個,侄子侄女若乾,一家子麵色青黃,衣服補丁摞補丁,能不能長大都懸,有心改變,可現實教會她出頭的鳥會被打,她隻能小心翼翼裝傻賣萌提點潑辣娘,老實哥哥,哎,她實在是太難了。他是村裡人嘴裡的小公子,五年前他們母子帶著忠仆來到這裡落戶,家有百來畝地,小地主一枚,村裡人窮,地少人多,為餬口佃租了他家的地,因他年紀小,人稱小公子。周萱兒第一次見這小公子被嚇,第二次見覺得這人有故事,自己也算有故事的一類,兩個有故事的人還是不要離得太近,可村裡就這麼大,三次,四次之後,不知何時閒言碎語飄飛,她氣得頭頂冒煙要找人算賬,卻發現罪魁禍首就在自己身邊。娘啊..你這是要你閨女的命呀。什麼,媒婆已經上門了,你已經答應了。周小萱隻覺得眼前一黑,腦海裡隻一句話,我命休矣!
60.6萬字8 25676 -
完結801 章
穿越后,我被竹馬拖累成了皇后
顧靜瑤很倒霉,遇到車禍穿越,成了武安侯府的四小姐上官靜。 穿越也就算了,穿成個傻子算怎麼回事啊?! 更加倒霉的是,還沒等她反應過來呢,她已經被自己無良的父母「嫁」 進了淮陽王府,夫君是淮陽王有名的呆兒子。 傻子配獃子,天設地造的一對兒。 新婚第一天,蕭景珩發現,媳婦兒不傻啊! 而上官靜則發現,這個小相公,分明機靈得很啊……
147.3萬字8 12394 -
完結616 章

攝政醫妃不好寵
大婚當前被親妹妹一刀捅進心窩,摯愛扭頭就娶了殺她的兇手。一夜之間,她失去了親人、愛人,和家。 逆天崛起記憶恢復,才發現爹不是親爹娘不是親娘,自己十多年居然認賊作父! 好,很好! 忍無可忍無需再忍,作為23世紀的戰區指揮官兼戰地軍醫,她左手醫毒雙絕右手機槍大炮,虐渣絕不手軟,還混成了當朝攝政大公主! 嫁給逍王了不起?信不信我叫他永遠也當不了皇帝? 娶了白蓮花了不起?反手就讓她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逍王殿下:“阿辭,要怎樣你才能原諒我?” 楚辭:“跪下叫爸爸!” 奶奶糯糯的小團子:“父王,螞蟻已經準備好,不能壓死也不能跑掉,父王請!”
106.5萬字8.18 36798 -
完結23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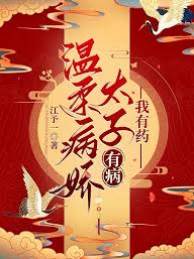
溫柔病嬌太子有病,我有藥
【古言甜寵 究極戀愛腦深情男主 雙潔初戀 歡快甜文 圓滿結局】 謝昶宸,大乾朝皇太子殿下,郎豔獨絕,十五歲在千乘戰役名揚天下,奈何他病體虛弱,動輒咳血,國師曾斷言活不過25歲。 “兒控”的帝後遍尋京中名醫,太子還是日益病重。 無人知曉,這清心寡欲的太子殿下夜夜都會夢到一名女子,直到瀕死之際,夢中倩影竟化作真實,更成了救命恩人。 帝後看著日益好起來,卻三句不離“阿寧”的兒子,無奈抹淚。 兒大不中留啊。 …… 作為大名鼎鼎的雲神醫,陸遇寧是個倒黴鬼,睡覺會塌床,走路常遇馬蜂窩砸頭。 這一切在她替師還恩救太子時有了轉機…… 她陡然發現,隻要靠近太子,她的黴運就會緩緩消弭。 “有此等好事?不信,試試看!” 這一試就栽了個大跟頭,陸遇寧掰著手指頭細數三悔。 一不該心疼男人。 二不該貪圖男色。 三不該招惹上未經情愛的病嬌戀愛腦太子。 她本來好好治著病,卻稀裏糊塗被某病嬌騙到了手。 大婚後,整天都沒能從床上爬起來的陸遇寧發現,某人表麵是個病弱的美男子,內裏卻是一頭披著羊皮的色中餓狼。 陸遇寧靠在謝昶宸的寬闊胸膛上,嘴角不禁流下了悔恨的淚水。 真是追悔莫及啊~
42.5萬字8.18 792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