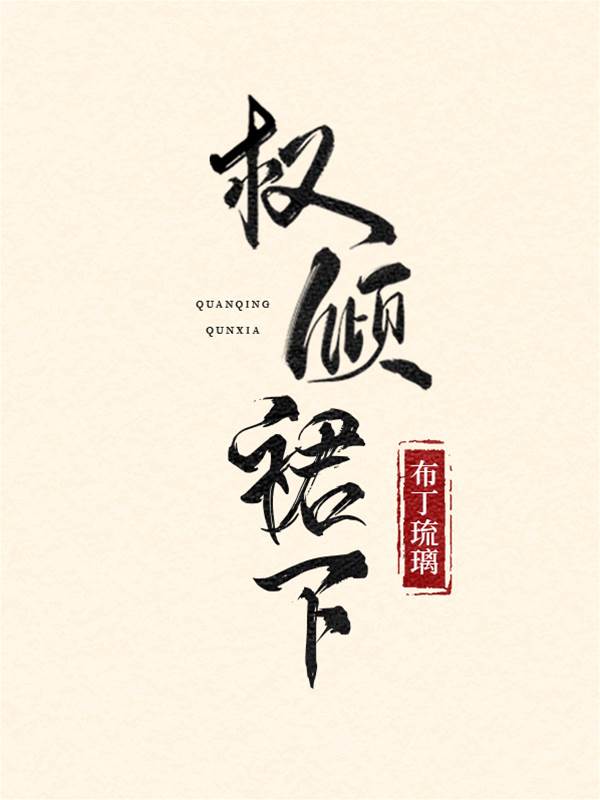《被太子搶婚之后》 第12章 吃醋的姑娘,他還真沒有……
明珠蒼白,低眸輕聲詢問:“你派人跟蹤我了嗎?”
懶得同他說謊,也心知肚明他既然問了就是知道了些什麼。
的聲音近乎低的聽不見,倒不是小心翼翼怕他生氣的語氣,而是有些難以忽略的低落和難過。
好像是被折斷羽翼的籠中雀,翅膀落在他的掌中。
明珠抬頭看他,眼前的男人低垂眉眼,和的影均勻灑在他漂亮的眉眼,角噙著淡淡的寒意,平添了幾分侵略。
趙識盯著的瓣瞧了好一會兒,目緩緩上移,撞一雙漉水潤的眼眸中,看見眼底深的難過仿佛有些不忍,“沒有讓人跟蹤你。”
明珠忍不住松了口氣。
沒有跟蹤就好,若去當鋪的事敗,那麻煩可就大了。
明珠任由男人用胭脂在自己的上擺弄,耳連帶因為他的作而發,臉頰艷滴,散發著怯。攥袖,抬眸著他問:“那您怎麼知道我今日出門了?”
誰給他打小報告了嗎?碧瑩?
不對不對,碧瑩也沒發現今天溜出門了。
趙識舒展眉眼,單手摟住的腰肢,手掌的溫度穿過單薄的料在的上蔓延,勾著腰的指骨稍微用了點力氣,摁著的腰,著自己的。
明珠有些難為,耳子紅了紅,撇開臉,不敢看他。
趙識倒是很自然,在房中他向來肆無忌憚,全然沒有方正端莊的君子模樣。男人低下頭靠近,咬住的瓣,一點點品嘗上的胭脂。
明珠往后倒退了幾步,撞上后的桌子,幸好有他的手擋了擋,才沒有撞到桌角。
實在不懂趙識這是什麼惡趣味。
明珠臉頰發燙,眼角水霧彌漫。
Advertisement
趙識親夠之后饜足抬起頭,他才不徐不疾解釋說:“你回來的時候恰巧被章回看見了。”
明珠知道章回是趙識的心腹,聽說武功很是高強。
“哦。”
“還穿著男裝?”
明珠的心提了起來,打起神說:“這樣穿出門方便。”
趙識倒也沒說別的,只是囑咐,“下次出門記得提前跟我說,外邊不安全,多帶幾個人。”
這種時候順著他比較聰明,明珠應聲說:“好。”
皇城腳下,每條大街都有管治安巡邏的侍衛,怎麼可能會不安全?無非就是趙識不想讓出門的說辭而已。
明珠以前很老實,他說什麼都聽,又乖又聽話,而今早已學會了奉違。
趙識又問:“今天出門做了些什麼?”
像隨口一問。
明珠不善撒謊,想了想,搪塞道:“給你買點東西。”
“我看看。”
明珠艱難找出一樣男子用的東西,是從前買的玉冠,玉質渾濁,匠人的雕工也十分一般,將玉冠放在他的掌心,忍痛割:“送你的。”
這是一年多以前買的,那時待嫁閨中,上沒有什麼錢,攢了月銀,給衛池逾買的禮,可惜,后來沒機會送出去。
玉冠已經送出去,還眼著。
趙識收了起來,噙著淡淡的笑意,心似乎不錯。
他的眼神忍不住停留在紅的小臉上,又瞥見方才作間弄的襟,眼神暗了一暗,隨后面不改替整理好裳,過的手指頭,“你最近很乖。”
明珠心不在焉,“嗯。”
確實要在他面前表現的更乖巧一點,這樣才能神不知鬼不覺辦事,等他發覺就晚了。
暮西沉,窗外的天漸漸黑了下去。
Advertisement
趙識好像還沒打算離開,說不準就要留在這里過夜。明珠多穿了件襖,看著霸占自己書桌的男人,不不愿慢吞吞走過去。
明珠不想留他,只得用笨法子將他主氣走才好。
問:“殿下,聽父親說您和我姐姐是不是很快就要親了?”
趙識從不在面前提別的人,也裝聾作啞當傻瓜,絕口不問。
男人緩緩抬起頭,沉默了一陣過后,他說:“你不用多想,我會照顧你一輩子。”
明珠聽見這句似是而非的話,抿著低下臉,他不僅不會照顧一輩子,還會要了的命。
趙識放下手中的筆,眼神復雜著,張了張,“我……”
這是第一次,他不知道該對說什麼。
垂著小臉,看不清表,形單影只站在燭火下,影纖瘦弱小。
趙識咽了咽,靜默許久。他的確喜歡,到濃時也控制不住會考慮娶為妃的事,但不過一瞬,這個念頭很快就被打消。
他走上前,握住的雙手,“你母親……”
明珠打斷他,“我知道,您別說出來。”
母親是青樓花魁,賣藝不賣,后來被父親從青樓贖回當了小妾,才有的。
趙識繃著臉,輕嘆了一聲,安靜很久,說不出別的話。
其實不僅是因為如此出實在不好只是一部分的原因,趙識這人想事周全,明珠子太弱,哪怕是側妃的份都撐不起來,也擔不了事。
趙識要的是合適的妻子,上得了臺面,辦得了事。言行舉止都能經得起打量和推敲。太子妃不是那麼好當的。
“即便有太子妃,你也無需擔心什麼。”這是趙識能給的承諾。
明珠微笑著點頭,“嗯,謝過殿下的厚。”
Advertisement
趙識卻不這個笑容,覺得這抹笑極度牽強,輕描淡寫好似也不是很在乎他的婚事。
趙識輕皺著眉,往深了想,這是醋了?亦或者是擔心他會喜新厭舊始終棄?他并不是那樣的人。
“別多想了,歇息吧。”
明珠是真的不在乎,落在趙識眼里好像就不是這麼回事。屋里僅剩的兩盞燭火都被吹滅,床帳擋住了從窗外鉆進來的月。
明珠背對著他,閉眼準備睡覺。
趙識從后抱住,“已經困了?”
這幾天晚上和他都不曾歡好過,明珠約約有預,后背僵了僵,略有些張,“嗯。”
趙識忽的摁住的肩,讓轉過子面對他,他的手指從的發慢慢往下落在尾椎,凜冽寒冷的氣息蹭著的頸窩。
明珠輕聲抗拒,“家里不好煎藥。”
簡單幾個字,就把趙識的興致敗的一干二凈。他的眼神漸次冷卻,握的手指骨間泛著白,他邦邦地說:“睡吧。”
明珠睡了個好覺,趙識第二天心就沒那麼好。
趙識進宮之前,沒忍住問了章回:“你說,是難過還是生氣?”
章回眼中疑,“殿下,您說的是?”
趙識閉上眼,眉心,“沒事。”
應該是都有吧,
他本不打算讓知道他要娶誰的事,趙識的心切開確實有點黑,起初明珠迫不得已跟了他的那段時間,確實三分不愿七分不。
趙識自認有幾分貌,除了不讓見外人這點,其他方面事無巨細,待已然極好。又不會藏也不會騙,仰慕從眼睛里溢出。
所以昨晚那是醋了嗎?
吃醋的姑娘,他還真沒有哄過。
下朝之后,安寧王世子同趙識并肩走下白石玉階,走了半道,真忍不住了:“太子,你今兒戴的玉冠屬實磕磣了些。”
Advertisement
趙識反應平平,“是嗎?”
安寧王世子說:“是啊,這玉雜質太多,不純。”
“我知道。”
趙識目過的珍寶百上千,昨天明珠將玉冠送到他手中的時候,他便瞧出來不是多好的東西。
但他并不在意好壞,多是的心意。
安寧王世子見他眉舒展,就明白了是送玉冠的人,在太子心中地位不一般。
“敢問這是哪位姑娘贈予的?”
“無可奉告。”
太子不說,他也知道,早先就有聞,太子也干了金屋藏的事。想必就是那位所贈。
“太子殿下,以前怎不見你戴過?”
趙識懶得理他,甚至嫌他話有點多。
盛文林哪怕沒有人理也能怡然自得說話,“這樣式,瞧著有些過時,怎麼今天就舍得拿出來用了?”
趙識腳步稍頓,“過時?”
盛文林哈哈笑了聲,很得意地說:“您日理萬機,想必是不關注京城時下流行的樣式,這種雕竹刻繡的款,一年前倒是風靡。”
趙識也沒多想,冷冷淡淡回復了一個:“嗯。”
剛出宮門,盛文林巧又遇上了他的同僚,他十分熱同馬車旁的男子打招呼,“池逾兄,好巧啊。”
衛池逾轉過,回了一禮,抬頭就看見了他側的男人。沉默幾許,衛池逾垂下眼睫,雙手作揖,“太子殿下。”
盛文林覺著衛池逾這兩年真是越來越孤僻,他同他早些年就已相識。
衛家落魄,他也很窮,不過聽說他有個貌如花的未婚妻。
盛文林和衛池逾師出同門,以前就知道衛池逾拼了命的讀書掙銀子,是為了能讓和他的未婚妻過上好日子,不必再貧寒之苦,后來不知怎麼,婚事說取消就取消了。
衛池逾也消沉許多。
“池逾兄,我聽說老師有意將他的小兒許配給你,你可真是艷福不淺。”
“假的。”
“你在我面前就別裝了,今兒也巧,太子也在,保不齊將來還能給你們做個。”
衛池逾盯著趙識的眼睛,他說:“我心有所屬。”
“不就是你之前那個未婚妻嗎?人嫌貧富,你又何必念念不忘。”盛文林也是為他好。
趙識冷嗤了聲,“衛大人還真是癡。”
衛池逾尚未出聲。
趙識又冷冰冰地說:“世子說的不錯,即是嫌貧富之人,你若是給不了一輩子的滔天富貴,不如就死了心。”
衛池逾忍了又忍,“多謝太子提點。”
趙識腔里憋著無法發泄的氣,眼睛里寒意攝人,他諷刺了這兩句后,怒氣逐漸平緩。
方才是他沒有氣量,這一年里,趙識都不曾在明珠口中聽見衛池逾這三個字,現在喜歡的是他。
趙識上了馬車,“我先走了。”
“殿下不妨搭我們一程?”盛文林不要臉地說。
“滾。”
盛文林驚了驚,轉過頭看著衛池逾:“你剛才聽見了嗎?”
“……”
“太子殿下我們滾?!”
“……”衛池逾說:“我也先回去了。”
盛文林看著他的雙,“你就走回去?我府上的馬車應該快到了,我搭你一程?”
“多謝,不用。”
從宮門口走到后巷,衛池逾花了兩炷香的時辰。
他鬼使神差走了后門,站在屋檐下靜靜等了很久,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麼。
天漸沉,黑云了過來,快要下雨了。
明珠打開后院的小門,抬頭就和一雙沉靜漆黑的雙眸撞上,用力雙手,差點以為是自己看錯了。
四目相對,沉默良久。
看不見衛池逾發紅的眼睛,曾經那個有些瘦弱的年好像已經了個的男人。
一陣雷聲過,下起了淅淅瀝瀝的小雨。
雨聲丁零,衛池逾啞著聲問:“他對你好嗎?”
明珠垂下眼睫的時候眼睛紅了一圈,沉默的點點頭。
過了很久,衛池逾又輕聲問:“珠珠,你現在喜歡他嗎?”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281 章

愛妃在上
愛妃,良宵苦短,還是就寢吧。某王妃嬌媚軟語,伸手輕輕地撫摸著某王爺的臉頰:王爺,咱們不是說好了,奴家幫王爺奪得江山,王爺保奴家一世安穩,互惠互利,互不干涉不是挺好嗎!愛妃,本王覺得江山要奪,美人也要抱,來,愛妃讓本王香一個…王爺您動一下手臂行嗎?王爺您要好好休息啊!某王妃吳儂軟語。該死的,你給本王下了軟骨香!呵呵,王爺很識貨嘛,這軟骨香有奴家香麼?
56.1萬字7.67 24331 -
完結272 章

邪王獨寵:傾城毒妃狠囂張
金牌殺手葉冷秋,一朝穿越,成了相府最不受寵的嫡出大小姐。懲刁奴,整惡妹,鬥姨娘,壓主母。曾經辱我、害我之人,我必連本帶息地討回來。武功、醫術、毒術,樣樣皆通!誰還敢說她是廢柴!……與他初次見麵,搶他巨蟒,為他療傷,本想兩不相欠,誰知他竟從此賴上了她。“你看了我的身子,就要對我負責!”再次相見,他是戰神王爺,卻指著已毀容的她說,“這個女人長得好看,我要她做我的王妃!”從此以後,他寵她如寶,陪她從家宅到朝堂,一路相隨,攜手戰天下!
48.8萬字8 25055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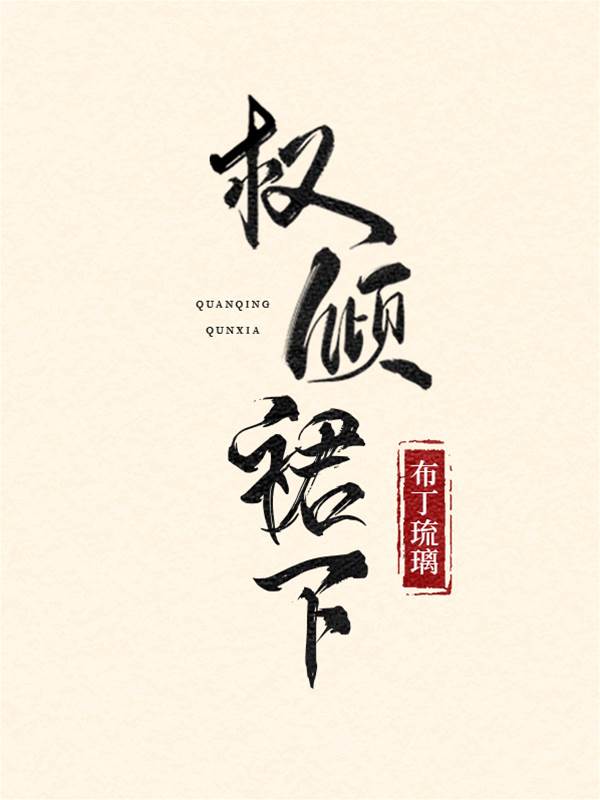
權傾裙下
太子死了,大玄朝絕了後。叛軍兵臨城下。為了穩住局勢,查清孿生兄長的死因,長風公主趙嫣不得不換上男裝,扮起了迎風咯血的東宮太子。入東宮的那夜,皇后萬般叮囑:“肅王身為本朝唯一一位異姓王,把控朝野多年、擁兵自重,其狼子野心,不可不防!”聽得趙嫣將馬甲捂了又捂,日日如履薄冰。直到某日,趙嫣遭人暗算。醒來後一片荒唐,而那位權傾天下的肅王殿下,正披髮散衣在側,俊美微挑的眼睛慵懶而又危險。完了!趙嫣腦子一片空白,轉身就跑。下一刻,衣帶被勾住。肅王嗤了聲,嗓音染上不悅:“這就跑,不好吧?”“小太子”墨髮披散,白著臉磕巴道:“我……我去閱奏摺。”“好啊。”男人不急不緩地勾著她的髮絲,低啞道,“殿下閱奏摺,臣閱殿下。” 世人皆道天生反骨、桀驁不馴的肅王殿下轉了性,不搞事不造反,卻迷上了輔佐太子。日日留宿東宮不說,還與太子同榻抵足而眠。誰料一朝事發,東宮太子竟然是女兒身,女扮男裝為禍朝綱。滿朝嘩然,眾人皆猜想肅王會抓住這個機會,推翻帝權取而代之。卻不料朝堂問審,一身玄黑大氅的肅王當著文武百官的面俯身垂首,伸臂搭住少女纖細的指尖。“別怕,朝前走。”他嗓音肅殺而又可靠,淡淡道,“人若妄議,臣便殺了那人;天若阻攔,臣便反了這天。”
52.5萬字8 22512 -
完結1779 章

快穿:病嬌大佬他好黏人南卿二二
南卿死亡的那一刻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自己能有一具健康的身體。死后,她綁定了一個自稱是系統的東西,它可以給她健康身體,作為報答她要完成它指定的任務。拯救男配?二二:“拯救世界故事里面的男配,改變他們愛而不得,孤獨終老,舔狗一世的悲劇結局。”“嗯。”不就是拯救男配嘛,阻止他接觸世界女主就好了,從源頭掐死!掐死了源頭,南卿以為自己可以功成身退了,可是男配們卻一個個不粘世界女主粘
247.7萬字8.18 20931 -
完結63 章

長燁無月
【和親公主vs偏執太子】【小短文】將軍戰死沙場,公主遠嫁和親。——青梅竹馬的少年郎永遠留在了大漠的戰場,她身為一國公主遠嫁大晉和親。大漠的戰場留下了年輕的周小將軍,明豔張揚的嫡公主凋零於大晉。“周燁,你食言了”“抱歉公主,臣食言了”——“景澤辰,願你我生生世世不複相見”“月月,哪怕是死,你也要跟朕葬在一起”【男主愛的瘋狂又卑微,女主從未愛過男主,一心隻有男二】(男主有後宮但並無宮鬥)(深宮裏一群女孩子的互相救贖)(朝代均為架空)
20.9萬字8.18 170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