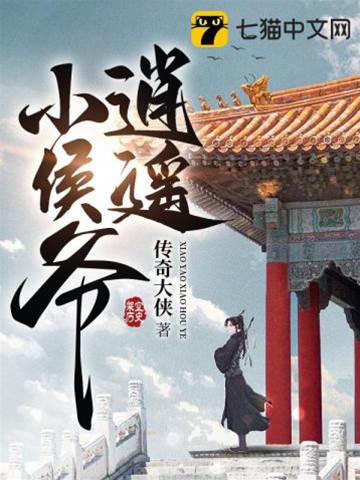《太子妃升職記》 第 73 章
想不到齊晟登基不過兩年,竟要準備著對北漠手,而且,還爲了這次手多方謀劃,不惜挑雲西叛。
張家、楊家、茅廁君與我等不過都是棋子,齊晟他下得好大的一盤棋!
據說他爺爺祖復辟時也是利用雲西之,現在看來,這爺孫倆還真是像,連手段都大同小異,真不愧那個“酷肖祖”的評價。
楊豫此刻眼中已全是敬佩之,危襟正坐,與我拱手道:“娘娘心思敏銳,真乃中豪傑。”
茅廁君看著我,脣角上卻是掛了一苦笑,說道:“皇上還是太子時,便對江北苦心經營,經常在江北大營一待數月,現在看來,他早已是有心對北漠手了。更別說兵指北漠還是祖的志。”
我腦子裡有些,這些到底是誰的志啊願的我不關心,我只知道我得重新認識一下齊晟此人了。
這樣一個能在數年前就慢慢謀劃一個天大的棋局的人,別得且先不說,只心志之堅韌就人到恐怖。
我沉默良久,忽地記起一件事來,忍不住問楊豫道:“我曾聽楊嚴說過,你們楊家有家訓,外敵當前必要先護國守民,他既然有用你平雲西的懷,爲何不讓你去領兵打北漠?”
畢竟楊豫是麥帥的傳人,軍中聲在那擺著呢,對北漠也可說是一種震懾。
楊豫聽我問到這個似是有些意外,稍一遲疑,平靜地說道:“因爲臣有一半北漠統,在此事上皇上是不放心臣的,這也是皇上爲何非要把臣調到雲西架空的原因,而不是明面上看到的那般爲了對付殿下。”
我微微張了,已是被這個消息給震傻了。
麥帥與徐氏都是正苗紅的南夏人,長子楊豫竟然有一半北漠統,這是怎麼說的?到底是麥帥了人還是徐氏爬了牆?再一聯想麥帥對徐氏母子的態度,難不這楊豫還真不是麥帥的骨?
Advertisement
茅廁君輕輕地咳了一聲,接過話去,“既然看了皇上的打算,那麼,我們要怎樣做?”
他說著,向我看了過來。
我覺得他這話問得有玄機,這個“我們”,可是又把“我”給圈進去了?我擡眼看茅廁君片刻,說道:“既然猜到皇上的用意,殿下可以不娶三姑娘。”
茅廁君聞言卻是搖了搖頭,道:“他既有除我之心,有些事便是避免不了的。我若是順著他的意娶了張三姑娘,礙著張尚書這一層的關係,到時候皇上對我可能還會擡一擡手,否則……”
他沒說下去,臉上掛著淺淡的笑意,只靜靜地看著我。
我覺得一個狐貍窩裡不可能養出綿羊來,哪怕他現在從始至終都披著羊皮,他也是吃的。所以,我不相信茅廁君是爲了守信纔要堅持與我聯盟,若不是我這個皇后還有可用之,他大可以拋開了我直接去找張家去談。
既然找我,那就說明在他們的計劃裡,我是必不可的。
我承認自己考慮事總是比他們慢半拍,當下最好就是以不變應萬變。
我瞥了眼一旁端坐的楊豫,問茅廁君道:“我腦子愚笨,猜不人心,殿下有什麼打算直說便是?”
茅廁君笑了笑,答道:“我與楊將軍商量過了,還是覺得你的法子最爲穩妥。”
我的法子?我的法子就裝烏,簡單易學,包教包會。
我氣樂了,說道:“既然如此,那大家就各自蹲各自的甕,都小心著點,人養小了沒事,只別被養死了就!”
說完起便往外走。
楊豫一下子急了,忙喚住了我,“皇后娘娘……”
我轉回來,看著他兩人,冷笑道:“既然你們都覺得我法子好,還這麼費勁地見我做什麼?”
Advertisement
楊豫微微皺了皺眉頭,卻不知說什麼好,看看我,又轉頭看茅廁君。
茅廁君坐在那裡默默看我片刻,忽地開口說道:“楊將軍,請您先回避一下,我有幾句話想與皇后娘娘說。”
楊豫點了點頭,又看了我一眼,從桌邊站起來大步地出去了。
屋中只剩下了我與茅廁君倆個,他低頭給自己的茶杯裡添著茶水,輕聲問我道:“你可還記得宛江上我與你說得那句話?”
我怔了一怔,宛江上他可是曾說了不話的,還曾許過我“平安康泰,食無憂”,這會子突然問起來,我卻有些不準他這是問的那一句了。
茅廁君擡眼看我,緩緩說道:“我既許諾,便會重諾。”
我心頭微微一震,忽地想起了我落水時的那一幕,他用手拉著我,盯著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說了這八個字後,便鬆開了著船舷的那隻手,護著我落了江中。
宛江九曲峽,江彎九曲,灘多水急,暗礁,時時兇險。
那一夜,我與他抱在一起,彼此用去爲對方擋著迎面撞來的礁石,半夜沉浮終換來逃出生天。
我點了點頭,答道:“我記得。”
茅廁君看著我,又繼續問道:“那我現在問你,你在興聖宮中說得那些話可還算數?”
我沉默下來,好半晌才答道:“算數。”
“那就好,”茅廁君似鬆了口氣,臉上出淡淡笑意,說道:“這陣子他待你這樣好,我真怕你就此昏了頭。”
我下意識地抹了抹鼻尖,有些訕訕地,“也是,人都說溫鄉乃英雄冢,其實溫鄉不對英雄管用的。”
茅廁君眉眼輕鬆,只笑了笑。
我轉回來重新在桌邊坐下,打算開門見山地和他談一談,便直接問道:“你們到底是個什麼打算?需要我做什麼?”
Advertisement
茅廁君面容平靜,默默看了兩眼,說道:“我手中力量不足,與他又有君臣之名,直接爭是爭不過的,唯有兵行險招。他早晚要打北漠,以他的脾氣屆時怕是要親征的,我會提前安排死士,藉此將他永遠留在江北,到時候你手握旨,扶帝登基。”
他的語速稍有些慢,口氣卻是極爲輕鬆,明明是在說弒君謀反的天大謀,卻似在說今兒大夥爬山都累了,晚上多加兩個菜吧,又或是明兒怕是要下雨,你別忘了多添件服。
我聽得認真,每字每句都放裡咂了一下,然後本著“懷疑”的神向他提出了四個問題,簡單概括一下就是四個“哪裡”:
第一,齊晟親征北漠的時候你在哪裡?還能活著嗎?手中還會有權嗎?第二,你所說的死士在哪裡?能保證一刀斃命嗎?第三,我到時候手握的旨在哪裡?形式合法嗎?第四,也是這個計劃中最關鍵的一點,帝在哪裡?
茅廁君一一解答道:“只要我現在肯委曲求全,都順著他的心意,他就要不了我的命。而只要我還活著,手中總是會有些人可以用的。死士不需你擔心,我既然這樣說,便已是做了安排。至於旨,不管他生前會不會留下,我總會你手中有人挑不出什麼來的聖旨便是。最後這一點,能否有帝可以登基,就要看皇后你了。”
繞了千百圈,轉了無數個彎,最後還是繞到了齊晟能不能生個兒子的問題上去。我!我的力還真大!
我思量一下,試探地笑道:“能不能有帝還是個未知數,既然能做掉齊晟,不如你自己來做皇帝?”
茅廁君緩緩搖了搖頭,目清明,“名不正言不順,天下必。而且,屆時楊豫定還會被困在雲西,我還需你張家來穩定江北局勢,就算我娶了張三姑娘,一個皇后也已是無法滿足張家的胃口,唯有扶你登上太后之位。”
Advertisement
恩,這倒都是大實話。
我點了點頭,垂目沉默片刻,將手掌按在桌面上站起來,說道:“好,就這樣定了!”
許是我答應的太簡單了些,茅廁君不出些詫異,看著我問道:“他現在待你這般,我還以爲你得猶豫許久纔會給我答覆。”
我嘲道:“你自己也是男人,難道還不知道男人是個什麼的東西?哪如自己兒子可靠!”
說完便起出去了。
朝小還眼地在外面等著,見我出來二話不說就拉著我往花園子裡走,待兩人剛繞進一個水亭裡坐好,朝的侍已是帶著寫意從遠過來了。
侍走到朝面前稟報道:“咱們隨都沒帶著可換的,只得給這位姐姐從山下新買了一,所以才耽誤了不功夫,郡主莫怪。”
朝隨意地點了點頭。
我擡眼細細打量寫意,見上果然是一簇新的,雖然料款式不算最好,倒也算是整齊。
寫意眼圈還有些發紅,眼地看著我,像是有無數的委屈。
我衝眨了眨眼睛,回頭又與朝閒扯了幾句,這才帶著寫意去找齊晟。
回去的路上,寫意湊在我邊低聲說道:“娘娘,是有人故意了奴婢一下,奴婢才落了水。後來帶著奴婢去換的時候,奴婢本來想只胡尋一件外衫穿上便是了,們卻將奴婢上的溼服俱都拿走了,奴婢在屋裡等了許久,這纔給奴婢送來了這服。”
我腳下慢了一慢,轉頭瞥了一眼,笑道:“自然是得這樣,不然怎麼能騰出空兒來拉我去與人見面。哎?你說這事咱們要不要與皇上說?”
寫意想了想,答我道:“奴婢覺得還是說的好。”
我點了點頭,“我也覺得這事得說,反正怎麼也是瞞不過去,與其被人審,還不如主代。”
寫意扶著我的手明顯地僵了一僵。
對這種明擺著做賊心虛的表現,我只笑了笑,手輕輕地拍了拍的手臂。沒關係,丫頭,咱們倆就繼續勾心鬥角下去吧,看最後誰能收了誰。
那邊齊晟早已是打發了楊嚴,正坐一大樹下與福緣寺的主持談經論道,見我過去了只淡淡地掃了一眼,又轉過頭去繼續與那老和尚閒扯。
雖然只那麼隨意的一眼,雖然齊晟那廝面上仍是一副平淡和之態,可我他媽心底偏就是莫名地發虛厲害,總覺得有些時候,他這種看似漫不經心的眼神卻比以往都要冷銳利。
我!爲什麼啊?剛剛分明是奉旨幽會的啊!
從翠山回盛都的道上,我端坐在一輛全新的豪華馬車,將我與茅廁君及楊豫的三方會談容簡要複述給齊晟聽,自然,由於會議記錄員寫意同志因故缺席,在容上難免會有一些缺斤短兩,只說楊豫已識穿了齊晟有意將他困在雲西的險惡用心,茅廁君更是向我指出了現在帝后和諧不過是個假象,是齊晟爲了與他爭奪張家而有意爲之,建議我不要被齊晟的甜言語欺騙,齊晟若是真心對我,就不會把江氏繼續留在大明宮,也不會我這個皇后至今無子。
齊晟一直垂著眼皮漫不經心地把玩新得的一串佛珠,直到我把話全部說完了也沒什麼反應。
我估著他是不好意思打斷我的話,想了想正想給自己添句“回答完畢”呢,齊晟起眼皮向我瞥了過來,不不慢地問:“楊豫竟然也在?”
我思量了一下,決定還是把話說的保守一些比較穩妥,便答道:“老九是這麼介紹的,不過,我只在泰興的時候遠遠看過楊豫一個影,至於這個是不是真的,我還真不能確定。”
齊晟聽了便似笑非笑地勾了勾脣角,說道:“老九若是隻想說那些,今日倒是用不到楊豫面。”
我心中暗暗一驚,齊晟這廝剛纔看著像是在走神,卻想不到出口便是這樣一針見。的確,若茅廁君見我只是爲了挑撥我與齊晟之間的關係,實在犯不著楊豫大老遠地從雲西跑回來。
我不有些後悔,不該爲了取信齊晟而把楊豫回盛都的事都說了出來,可此刻若是不說,這事以後萬一要是齊晟知道了,那我以前說的話不論真假,他怕是都要不信了。
我擡眼看向齊晟,說道:“我猜著,他是爲了向我顯示誠意吧,也我信他後確有楊豫的全力支持,只要再聯合了張家便可以扭轉乾坤。”
齊晟倚靠在車廂壁上,微揚下靜靜地看著我。
我深了吸口氣,壯著膽子繼續說道:“他還說,他要的不只是這天下,還有……我,他也可給我皇后之位,凡是你能給的,他都能加倍給我。”
齊晟的眼睛就微微地瞇了瞇,其中殺機一閃而過。
我心中暗念阿彌陀佛,茅廁君,對不起了,這下子你要蹲的水甕怕是要更小了,且記著一定要把脖子好,千萬別給了齊晟揮刀的機會。
齊晟問我道:“你怎樣答的?”
我眨了眨眼睛,答道:“我說此事太過重大,我一個人做不了主,得回來與你商量商量。”
齊晟微微一怔,隨即便放聲大笑起來。
我依舊跪坐在他的側,抿著看他。
齊晟笑了許久,忽地臂攬住了我的腰,一把將我扯倒在他的上,將他手上的那串佛珠攏在了我的腕上,然後用下輕輕地挲著我的頭頂,呢喃道:“明知道你說的都是假話,可我就是喜歡聽……就是喜歡聽。”
我一個沒繃住,子就下意識地僵了一僵。
正想著撐起來與他解釋幾句,可他手上卻用了力,只將我在他的前,停了片刻,忽地低聲說道:“芃芃,我們再生個孩子吧。”
尚在愣怔間,他已是用手擡起了我的下,低頭吻了下來。
頭腦暈沉間,我不由嘆,齊晟果然是個雷厲風行的主兒……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連載262 章
快穿係統之女主是boss
(1v1甜寵,男神略微病嬌~)梵輕死了,然後莫名的繫結了一個係統。係統:你要去不同的世界扮演女主,然後………梵輕點頭:懂了係統:等等我還沒有說完!等等宿主你幹什麼!你是身嬌體軟的女主,不是反派!等等宿主那是男主,宿主快把刀放下!不,宿主那是反派,你們不能成為朋友!宿主那是惡毒女配,你們不能做交易!然後,係統就眼睜睜的看著它的宿主,一次又一次的走上人生巔峰。本書又名《我的宿主總在黑化》
27.7萬字8.18 9605 -
完結1455 章

神醫王妃超難寵
她是古醫世家嫡系傳人,穿越成了他的沖喜王妃,盡心盡力救了他的命后,他心中的白蓮花出現,直接遞給她一封和離書。古代的棄婦不好當,但她從此腰桿挺直了,也不抱狗男人大腿了,直接走上了人生巔峰。皇帝跑來獻殷勤,世子爺十六抬大轎娶她進門,富商抱金山銀山送給她……某日,他出現在她面前,冷著臉:“知道錯了嗎?知道錯了,就……”回來吧。她笑著道:“下個月初八,我成親,王爺來喝杯喜酒吧,我給孩子找了位有錢的后爹。”
270萬字8.33 353404 -
完結83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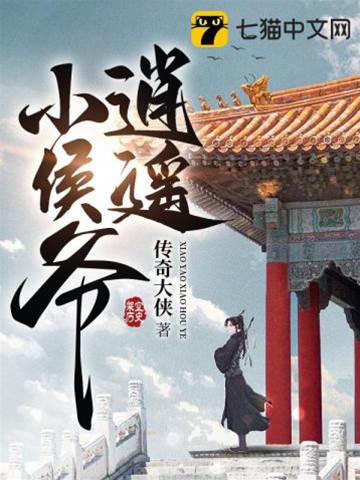
逍遙小侯爺
穿越古代,成了敗家大少。手握現代知識,背靠五千年文明的他。意外帶著王朝走上崛起之路!于是,他敗出了家財萬貫!敗出了盛世昌隆!敗了個青史留名,萬民傳頌!
148.9萬字8 98890 -
完結588 章

定居唐朝
公元622年,大唐武德五年,唐高祖李淵在位,未來威震四方的大唐剛剛建立,風雨飄雨。薛朗,一個現代青年穿越到此時的唐朝,生存是個大問題。 從孤身一人到安居樂業,這是一個男人的勵志史。 PS:想看王霸之氣一發,古人五體投地拜服的基本可以止步,生活從來都不容易,不管在哪里,能做的只是努力。本文主生活流。再P個S:略有存稿,放心跳坑!
111.1萬字8 1639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