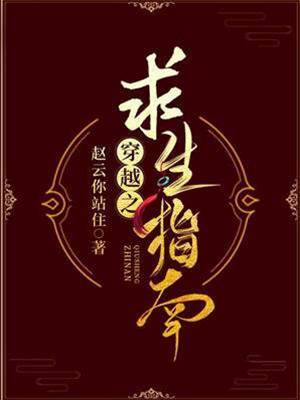《太子妃升職記》 第 70 章
綠籬這裡盼著我能夠椒房獨寵,齊晟那裡卻又開始了宮留宿,而且還比以前積極了些,三天裡頭有兩天會宿在後宮。後宮嬪妃本就不多,齊晟又像是有意突出我皇后的地位,於是,隔上幾天就能到興聖宮一次。
我本著“牀上要積極肯幹,牀下要任勞任怨”的工作態度,認真地做著“皇后”這份工作。
可沒想到齊晟竟然比我還要敬業,在牀上從來都是積極主,勤勤懇懇,絕不耍懶,能做兩次的時候從來不做一次。
這樣的工作態度著實人臉紅。
我越發覺得齊晟也不容易的,白天披上龍袍做皇帝疲力盡,夜裡了龍袍做牛郎力疲盡。爲了後宮和諧,不管每天有雨沒雨都得被人擰出一些水來。這樣下去,怕是早晚有一天步了先帝的後塵。
這樣一想,我就有點心,一天夜裡趁著中場休息的空,勸他道:“要是覺得累,就歇歇吧,這世上只有累死的牛,沒有耕壞的地,更別說這宮裡還這麼多塊地,哪能就都耕了,也別太難爲自己了,我想們也能理解的。”
齊晟被我說得愣了一愣,不知爲何忽地就惱怒了起來,把我過來過去好一番折騰,最後將我死死地在牀邊,雙手扣了我的手,啞聲問道:“張芃芃,你就這麼想氣死我?”
說完就低下頭來暴地吻了下來,連我脣都給磕破了。
事後我著自己破皮腫脹的脣,真心覺得自己是好心沒好報。
時間進四月,天氣開始熱了起來,宮們的衫越換越薄,宮中空氣中荷爾蒙的味道也越來越濃。我原想著齊晟這陣子巡宮巡得這樣勤快,黃氏等人的閨怨差不多也該沒了,可沒想著們幾個見我的時候仍都是斂眉垂眼,委屈地跟小媳婦似的。
Advertisement
憑良心說,我真是覺得齊晟在牀上已經夠努力了,這幫子人有些得隴蜀了。
待到五月間,雲西的平叛之戰打得越發激烈起來,朝廷裡戰報一日裡就能收到十好幾份,還都是六百里加急的,齊晟政務纏,再沒那麼多時間來後宮了,除了隔幾天會往我宮裡來睡一宿外,大多時候是把黃氏等嬪妃召到大明宮去侍寢。而且做派也越來越朝著傳統帝王去了,忙的時候三五天不近,興頭上來的時候,一夜裡召倆,前半夜一個,後半夜一個,跟趕任務一般。
此等形,我前世只在電視劇裡看過。
對於他這等行徑,我十分地不齒,作爲曾過二十年現代教育的原新青年,我唾棄他這種侮辱的行爲!
黃氏等人想必也應是不願的,誰願意睡一半被人從被窩裡拎出來送走啊,就算現在天氣不冷了,可這覺也睡不好啊。折騰半宿,也難怪第二天的臉會含三分委屈。
不過,總得來說宮中還算平靜。
綠籬隔上幾天就會藉著進宮給太皇太后請安的機會來我宮裡轉一圈,順便給我送些小兒來。
我肚子卻是一直沒有靜,我也說不清是喜是憂,綠籬便給我出主意道:“娘娘請尊送子觀音來吧,奴婢聽說翠山福緣寺那邊是極靈的,要不奴婢替娘娘去拜一拜?”
我不忍心拂了綠籬姑娘的一片好意,便點了點頭。
綠籬神抖擻地出了宮門,五月底的時候,就被診出懷有孕來了。
我得到這信時都有些愣,第一個念頭就是翠山福緣寺的菩薩果然靈驗,第二個想法是菩薩也不容易,工作太忙了,偶爾失誤一次也是有可原的。
Advertisement
聽說宋太后聽了這消息眼睛都紅了,當天就把茅廁君拎宮裡好一頓訓,連“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都說出來了。
其實茅廁君也無奈的,他與張三姑娘那裡才進行到議婚階段,離房都還遠著呢,更別說抱孩子了。再者說張三姑娘今年才十三歲,如果茅廁君不想做禽的話,怎麼也得等到小姑娘及笄才能圓房。
而且他與張家結親又屬於政治聯姻,都得彼此敬重著點,怎麼也不好做出這邊小王妃進門拜堂,那邊小妾請產婆生孩子的熱鬧事。
如此一來,生孩子更得是好幾年後的事了,也怨不得宋太后要紅眼了。
不過綠籬有孕,太皇太后倒是很高興。
綠籬往太皇太后那跑得勤,上也討喜,老太太本來就對印象不錯,這回一看肚子又爭氣,心裡更是喜歡上了,特意派了人去趙王府傳話給綠籬:頭幾個月那都不許去,也不用進宮給我請安,先把子養壯了再說!
如此一來,綠籬再沒借口進宮來看我了,聽說當天夜裡就抹了眼淚。
說這話的時候,趙王依舊是蹲在我興聖宮後殿的廊下,一臉的無可奈何。
我用雙手架著葳兒站在地上,看著寫意在一邊用去了頭尾的小魚喂貓。
葳兒裡依依呀呀地著,掙扎著出短的小去踢那貓兒。人雖小,勁頭倒是很大,一會功夫就把我累了一的汗。
我正有些煩躁,就聽著旁邊的趙王又幽幽嘆道:“我是真服了綠籬那丫頭了,你說那眼淚怎麼來得就那麼快呢?只要手帕子往外這麼一掏,眼圈立刻就紅,接著眼淚就下來了!”
其實這事我一開始的時候也很驚歎,不過見得多了,也就習慣了。
Advertisement
我安趙王道:“沒事,小姑娘都那樣。”
趙王奇道:“都那樣?”
我點點頭,轉過臉去吩咐寫意,“寫意,哭一個趙王看看。”
寫意先是一愣,眼圈立刻就紅了,淚汪汪地控訴我道:“娘娘盡欺負人,奴婢又不像綠籬姐姐那般不就哭。”
我面如常,轉回頭去看趙王,“哪,見到了吧?都這樣。”
趙王佩服地點了點頭。
寫意抹乾了眼淚,繼續淡定地喂貓去了。
葳兒又開始在我懷裡掙扎,還想著去踢那貓一腳。
我一邊用手堅定地把抱在懷裡,一邊問趙王道:“就瞧你表現的那樣,我原以爲你會爲江氏守的。”
趙王苦著臉說道:“皇嫂,那不都過去的事了嗎?咱別哪壺不開提哪壺,麼?”
我點點頭,停了停,又繼續說道:“你既然把綠籬拆了封,可就不能給我退貨了啊。”
趙王微微張著,滿臉的驚愕,半天沒能說出話來,過了好一會兒,這才又與我說道:“皇嫂也去趟福緣寺吧。”
我實在是被葳兒折騰煩了,就把轉手給了孃,孃帶著回屋裡去玩,又吩咐了寫意把貓抱走,然後才轉頭看趙王,問道:“你說我現在去福緣寺,合適嗎?”
趙王認真地想了想,回答我道:“合適的。”
我遲疑了一下,又問他道:“皇上那裡……會不會多想?”
趙王笑道:“臣弟覺得應該不會,若是會,他也就不會隔三差五地就來皇嫂宮裡了。”
我思量了一下,認同地點了點頭,這話說得也有道理,齊晟既然常來睡我,就應該想到我有可能會懷孕這事。俗話說得好,總在河邊走,哪有不溼鞋的,更別說這整天趟水的。
Advertisement
第二天,正好是齊晟來我宮裡的日子,我琢磨著男人在牀上最好糊弄了,於是很是積極主地勾引他滾了牀單,然後趁著他筋疲力盡閉著眼昏昏睡的當頭,委婉地向他表達了我想去福緣寺上香的願。
我本想著讓齊晟糊里糊塗地點了頭,沒想到他聽了反而是神了起來,睜開了眼稍稍有些意外地看向我,問道:“你想去福緣寺?”
我一面嘆著齊晟這迴流速度可真夠快的,一面老實答道:“趙王那裡說福緣寺許願靈的,臣妾就想著去一趟。”
齊晟的手指在我腰間輕輕地著,就是不說話。
我也覺得這事是有些不靠譜,自己也覺得有點心虛,咬了咬牙,手搭上了齊晟的腰,故意半擡起子,似非地著他的膛,低聲說道:“我在這宮裡悶得久了,想出去氣,翠山離得又近,早上出去,天不黑就能回來的,就我去吧。”
就這麼蹭蹭地,眼角餘便瞥到薄被的一慢慢地高了出來。
這一往下流,齊晟大腦供明顯就不足了,待我再撒一般地晃了晃他,他便答了一個字:“好。”
尼瑪真是一如既往的惜字如金啊!
齊晟說完這個字,手上就加了勁道,把我往他上扣了過去。
我故作正經地笑了一笑,將他的手從我腰上拉了下去,正道:“明兒皇上還要早朝呢,快些睡吧!”
說完自己便率先翻躺了下去,用被子將自己裹了個嚴嚴實實。
後傳來齊晟磨牙的聲音。
我正得意間,他忽地一把扯開被子將我扽了過去,二話不說就開始,剛把我的致挑起來的時候,他卻又突然停了下來,翻回去說道:“明兒還要早朝,睡吧。”
這種報復是多麼的稚啊!
偏我還被他勾得連氣都了,深呼吸了半天,還是沒法把心頭那團火了下去,索從牀上坐起來,轉頭惱恨地看了齊晟背影片刻,發狠地撲了上去。
不管了,先瀉了火再說吧!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2126 章

邪王強寵:廢材毒醫大小姐
章節錯誤,請大家搜素《邪王強寵:廢柴毒醫大小姐》觀看完整章節~ ——————————————————————————————————————————————————————————————————————————————————————————————— 她是21世紀的第一特工毒醫。 一朝穿越,卻淪為癡傻貌醜的廢材鳳府大小姐。 廢材如何?癡呆又如何?鳳傾歌冷笑。 且看她涅盤重生,容貌傾城。昔日欠她搶她欺她妒她,她通通一樣一樣拿回來,丹藥、法器、萌寵、美男通通盡收囊中。 隻是,背後那個陰魂不散的男人,是怎麼回事? 「喂喂,本小姐已經說過了,本小姐對你沒興趣。」鳳傾歌直直朝天翻了個白眼。 某男冷魅一笑:「這可由不得你。來人,把王妃捆了,扔進洞房。」
183.2萬字8 249167 -
完結521 章

帶著物資穿到年代搞事業
出生在富裕家庭從小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文舒念,從冇想過自己有天會得到傳說中的空間。 本以為是末世要來了,文舒念各種囤積物資,誰想到自己穿越了,還穿到了一個吃不飽穿不暖買啥都要票的年代當知青。 在大家都還在為每天的溫飽而努力的時候,文舒念默默地賣物資搞錢讀書參加工作,一路上也結識了許多好友,還有那個默默陪伴在自己身邊的男人。 本文冇有極品、冇有極品、冇有極品,重要的事說三遍,因為本人真的很討厭極品,所以這是一本走溫馨路線發家致富的文。 最後:本文純屬虛構。
86.7萬字8 33679 -
完結13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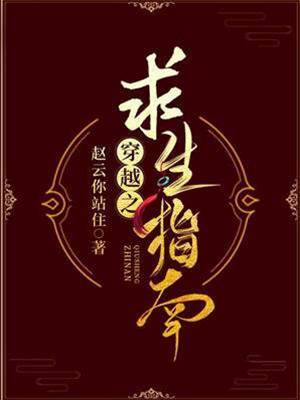
穿越之求生指南
同樣是穿越,女主沒有金手指,一路艱難求生,還要帶上恩人家拖油瓶的小娃娃。沿街乞討,被綁架,好不容易抱上男主大腿結果還要和各路人馬斗智斗勇,女主以為自己在打怪升級,卻不知其中的危險重重!好在苦心人天不負,她有男主一路偏寵。想要閑云野鶴,先同男主一起實現天下繁榮。
34.7萬字8 6919 -
完結1028 章

錦繡大明
錦者,錦衣衛;繡者,繡春刀;且看穿越五百年來到大明萬歷初年的楊震如何走上巔峰,重振河山!
281.1萬字8 11993 -
完結628 章

大秦鐵騎
國家衰落,從來不是外族之禍;朝堂之亂,才是國亂根本。一個華夏第一特種兵,從戰死他鄉到穿越異界,成為大武帝國的六皇子,但顯得極為光耀的身份,在整個大武皇朝上下,卻成為了被人嘲笑、諷刺的笑話。
108.5萬字8 5167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