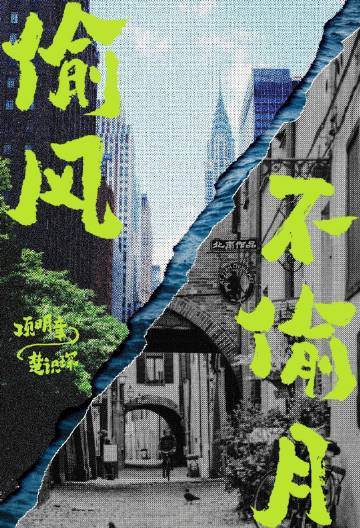《沉舟》 第85章 吃飯
幾秒鐘的沉默。
顧沉舟說:“賀海樓?”
“猜對有獎。”賀海樓索在窗戶旁靠著,跟顧沉舟說,“你想要什麼?”
“我想要你掛電話。”顧沉舟在電話那頭說。
賀海樓齒一笑,盡管對方這個時候看不見:“不真心的許愿不算,換一個吧。”這還真沒說錯,如果顧沉舟真不想聽見他的聲音,早就直接掛斷電話了,難道還會告訴他等他先掛斷?不合邏輯啊!
天瑞園里,顧沉舟推開桌子,從電腦面前站起來:“打電話過來什麼事?”
……唔,當然,目前來說,顧沉舟不掛他的電話,主要還是因為他會時不時送去一些有用的消息。賀海樓暗自想到。
顧沉舟沒有提最開頭那句話,賀海樓也沒有繼續延的意思,兩個人都有意無意地做出了忽略。
賀海樓回答顧沉舟的問題:“給你一個消息,聽不聽?”
“聽。”顧沉舟給了對方只有一個字的簡單回答。
賀海樓將自己的手掌按在玻璃上,過張開的指看玻璃窗外的漆黑:“不用在賀總理這里費工夫了,考慮考慮別人——我這麼說,顧大應該聽得懂吧?”
仿佛有一聲很輕的笑聲過信號,從并不算太遠的距離傳遞到賀海樓的耳朵里。
賀海樓的食指不覺了一下。
這一點似有若無的聲音勾起了他的,他開始在腦海里描繪顧沉舟的笑容:那個人笑起來會是怎麼樣的?當然,并不是那種冷淡的疏離的禮貌的微笑,而是——
熱絡的?會咧開,出牙齒,眼睛跟著瞇起來,臉頰上還有酒窩出現?
驚喜的?眼睛睜大,角不知不覺揚起來,笑容很淡但顯得很真實?
得意的?挑起眉梢,角也跟著一起向上飛揚,但幅度卻又克制在一個矜持的范圍里?
Advertisement
還有愉悅的、高興的、的……
“當然。”顧沉舟的聲音不太恰當地響起。
被打斷的賀海樓有些無趣地一撇:當然,就剛剛那件事來說,電話那頭的人現在最多也不過扯一下角,表示理應如此或者早已預料吧。
他又聽電話那頭的人往下:“賀這麼慷慨,我也送賀一個消息吧。”
“哦?”賀海樓表示洗耳恭聽。
“有些事本來就和賀總理沒有關系,倒是賀總理現在可以關注一下那些真正和這件事有關系的人。”顧沉舟點到即止,“如果沒有其他事,今天就到這里吧。”
這不是一句疑問句。
賀海樓本來還在琢磨顧沉舟前一句含義富的話,聽見這下一句話之后,眉梢微微一跳,用三分認真,三分玩笑的口吻說:“怎麼會沒有其他事呢?顧大別忽略我最開頭的話啊。”
電話那頭一陣沉默。
賀海樓興致地想象顧沉舟此刻的表,還代對方假設對方可能的回答。
一秒鐘,兩秒鐘,三秒鐘。
“嘟——”電話忙音。
電話直接被掐了……
賀海樓:“……”
算了。他有點郁悶又不乏愉悅地拿著手機走上最后半層樓梯,回到自己的房間里。
房間并沒有開燈。
淡淡的星輝提亮黑暗的房間,并在靠窗的木地板上照出數塊亮。
賀海樓走到飄窗邊,稍微收了收隨手放在那里的資料,又打開電燈坐回電腦桌前開電腦。
悉的開機畫面下,代表等待的滾條孜孜不倦地來回運。
賀海樓單手轉著手機,回想剛才的對話。
他告訴顧沉舟賀南山對這件事的態度,最主要的目的還是借著汪系的手斷了賀南山出手的想法……如果說現在的賀南山因為各方面的權衡,已經八可能不會出手,那汪系那邊一表態死咬彭松平,賀南山就一定不會出手,不止因為汪系的力量,更因為這位組織部副部長和賀南山雖然在同一個陣營里,卻一向面和心不合,現在有機會削弱甚至直接把對方拉下來,賀南山怎麼會放過,又為什麼要放過?
Advertisement
還有顧沉舟那句話。
顧沉舟之所以會說出來,意思……
賀海樓微一沉,首先排除了對方是在混淆視聽這個可能:并沒有什麼必要,就算賀南山不防備著董昌齊姜東的事,也防備著顧新軍的針對,一直是非常警惕的,顧沉舟想要用一句話瓦解賀南山的警惕心?他的腦袋一定被驢踢了。
當然,就算他自己的腦袋被驢踢了,顧沉舟那個家伙也不會,所以……
賀海樓的手指挲一下下,突然笑了:其實這也沒什麼不好理解的,副組織部長啊,雖然賀南山也是汪系和顧衛兩家的眼中釘,但這個鉗制著組織部長工作的副組織部長,不管對要借重組織部勢力的汪系還是想完全掌握組織部的顧新軍來說,跟中刺也沒有什麼差別了吧?
這麼一來,通知眼中釘對付中刺,也就是鶴蚌和漁翁的關系了。
不過這件事對賀南山來說,倒也算是漁翁得利了,只看這兩方誰的手段更高明,攥取到更多的利益……
這所空曠的房子里,賀南山和賀海樓的臥室僅僅只隔了一層天花板。
這間在二樓東邊盡頭的臥室里,老人坐在高背椅子上,紅的椅子正對著敞開的窗戶。
從高高吊頂上下來的燈照亮房間的每一個角落,涼風從窗戶吹。
坐在窗前的老人雙手疊地拄著拐杖。
他靠在椅子背上,形被高大的座椅襯得有些瘦弱,目眺向遠方,面容嚴肅、沉靜。
他的襯穿得板正,最后一顆扣子也穩穩當當地扣上,花白的頭發被染黑,梳得一不茍。
他的眼睛、鼻子、,每一都寫滿了堅毅和肅然。
但他額頭的壑,眼角的細紋,卻如歲月不覺的流逝,以最誠實的方式,昭顯出他的疲憊與衰老。
Advertisement
這邊顧沉舟剛剛掛掉了賀海樓的電話,起去跟顧新軍通了一下氣,又接到了一個電話,還照樣是不認識的號碼的。
他皺了一下眉,沒有直接掛斷,而是接起來打算看看是誰,如果是賀海樓——
“是顧大嗎?”電話那頭傳來俏皮的音,然后又很自覺地報上名字,“我是汪思涵。”
……還好沒掛電話。顧沉舟笑道:“我聽出來了。”
“說起來你看到那張照片了沒有?”汪思涵說,“照得還不錯嘛!”
這話的意思……沒等顧沉舟怎麼分析,汪思涵又接下去:“不過我爸爸看見了臉就有點微妙了,然后他說‘顧家那個小子?哼!’”接著就是對方忍不住的笑聲。
顧沉舟剛在這里出一個微笑,就聽見汪思涵輕快的聲音再次響起來:“對了,你什麼時候有空?我論文的資料收集得差不多了,最近都有時間,剛好請你吃飯……唔,我們才兩個人,就不要去國天香那種地方了吧,西餐吃來吃去也沒有什麼特別好吃的,我們是去長城路的魚莊吃魚,還是去林安路的川菜館,或者靠近灑水胡同的那家什麼名字來著的小飯店?”
還是個小饕啊。顧沉舟說:“我都可以,你想吃什麼?”
“吃魚怎麼樣?”汪思涵的愉快都明晃晃地通過信號流瀉過來了。
“明天晚上?”顧沉舟敲了時間。
“好,明天晚上七點,直接在魚莊見。”汪思涵說,“我就先掛啦。”
顧沉舟嗯了一聲,就聽見電話斷線的聲音,他將手機從耳邊拿開放在桌上,繼續之前未完的事。
長城路的魚莊并不是京城中吃魚的飯館里最有名氣最豪華的那一家,但就味道來說,確實不錯。
Advertisement
之前就約好了時間,顧沉舟特意提前十分鐘到達,卻沒有先進去,而是站在魚莊外頭,打算直接等對方到達再一起進去。
大概三五分鐘的時間,一輛黑的車子開到魚莊門前。
顧沉舟過車窗看見了坐在后車廂的汪思涵,但當先走下來的,是一直跟在汪博源旁、姓張的書。
張書今年剛剛過四十,就他現在的職位跟年齡來說,算是非常年富力強的。
“顧好。”這位書一下車就出雙手,角含笑著快步向顧沉舟走去,并用力握著對方的手有力地搖晃了一下。
顧沉舟瞥了一眼坐在車上還沒有下來的汪思涵,心道汪博源真是不一般地寶貝自己的兒,他跟汪思涵第三次見面,還沒怎麼樣呢,那位書記大人就打發自己旁的第一得力助手跟車過來,看樣子如果他現在的表現不能得到這位得力助手的滿意,跟著車來的妹子又要跟著車回去了。
“張書,晚上好,聽說前一段書記有些咳嗽,現在好些了沒有?”顧沉舟也跟著出笑容,他的笑容比平常了幾分矜持多了一些謙虛,不看僧面看佛面,他不在這位書面前拿大,看的是汪博源的臉。
“食補了幾天,現在已經好了。”張書笑瞇瞇地說,又意味深長地說,“顧啊,我們書記可是看見了那張照片——”
“大家混玩著的,居然驚了書記?”顧沉舟失笑,“那時候人多,思涵被不小心的人撞到了,我順手扶了一把。”
張書暗暗點了一下頭,不遠不近,態度很正常嘛——其實顧沉舟的名聲一向不錯,汪博源也沒有什麼特別不放心的,之所以還讓張書過來,一來是表示表示自己的態度,二來也是有備無患,這個心態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形容:父親看兒,越看越寶貝。
一兩句話之間,兩人的態度都表達到位了。
張書很有風度地跟顧沉舟道了別,轉往車子前走去。一直坐在后座的汪思涵這才得以下車。
下車以后,汪思涵先沖顧沉舟笑了笑,沒有立刻走上前,而是站在一旁跟張書和司機道了別,等到車子開走之后,才幾步走到顧沉舟旁:“久等了,有沒有被我爸爸嚇到?我爸爸從三年前就是這樣,越來越張我……”的聲音突然有點低落。
這并不是什麼:三年前汪博源的妻子葉秀英駕車外出時發生車禍,駕駛的轎車與裝載有毒的運輸車相撞,當場死亡。
這之后汪博源一直沒有再婚,現在看汪思涵這樣說,可能是對方已經將自己對妻子的疊加到對兒的上了,所以才非常關心兒的生活友況——不過這樣的關心在他們這個地位來說,也并不突兀。政治家庭里出生的男孩子,會被更多的培養他們對政治的興趣,而孩子,就主要從自素質開始,培養學識氣度、眼心。
這就是二代三代的圈子時不時會傳出哪家的兒子孫子在外頭搞男關系,卻很傳出哪家的兒孫在外頭鬧出糊涂事的緣故,不管是哪種家庭,對孩子這一方面要求,相較于男孩子,總是嚴得多的。
對比昨天的簡單方便,汪思涵今天的打扮顯得淑一些。
穿著一襲白子,脖子間掛著一條紫水晶項鏈,頭發還是簡單的扎一個馬尾,出兩只白的耳朵,背著手盈盈站立在夜里的時候,周像發了一樣,吸引來去路人的目。
顧沉舟一下子就理解了為什麼許一眼就看上了汪思涵——看上不奇怪,不看上才奇怪。
兩人目前連朋友都算不上,他并做出那些在西方看來是禮貌紳士、在東方卻有些突兀的作,只是微笑著說了兩句話,而后一起走進魚莊。
或許是待會就要吃好東西了,汪思涵的興致很高,從魚莊門口到大廳的短短幾步距離里,一直饒有興趣地和顧沉舟談閑聊,說到好笑的地方,也非常自然地笑出聲來。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221 章

電競團寵Omega
全息电竞联赛是Alpha们的秀场,凋零战队Polaris为了凑齐职业重返赛场,居然招了个第二性别是Omega的巫师。小巫师粉雕玉琢,站在一群人高马大的Alpha选手里都看不见脑袋,时不时还要拽着队长林明翡的衣角。全联盟都觉得昔日魔王林明翡掉下神坛,要笑死他们不偿命。 后来,他们在竞技场里被夏瞳用禁制术捆成一串,小巫师用法杖怼着他们的脑袋一个个敲过去,奶凶奶凶的放狠话:“给我们队长道歉!不道歉的话就把你们全部送回老家!道歉的话......我就唱歌给你们听!” 众俘虏顿感上头:“靠,他好可爱!” - 作为全息电竞行业里唯一的一只Omega,夏瞳不仅是P队的吉祥物,还是所有战队想挖墙脚的对象,迷弟迷妹遍地跑。 拿下联盟赛冠军的第二天,一个西装革履的Alpha敲开了P队俱乐部的大门。 “夏瞳是我走失的定制伴侣,请贵俱乐部即刻归还,让他跟我回去生孩子。” 林明翡赤着精悍的上半身,叼着烟堵着门,强大的信息素如山呼海啸:“你有胆再说一遍?” #让全联盟的团宠给你回去生孩子,你是不是没被人打过! #再说他现在是老子的Omega! 看着沉稳实则切开黑的大帅比X看着傻但打架超狠的小漂亮。 →1V1,苏爽甜,弃文勿告,感谢尊重。 →社会制度游戏规则全是鬼扯,千万别考据。 →求不养肥,养着养着可能就死了...
48.6萬字8 14032 -
完結12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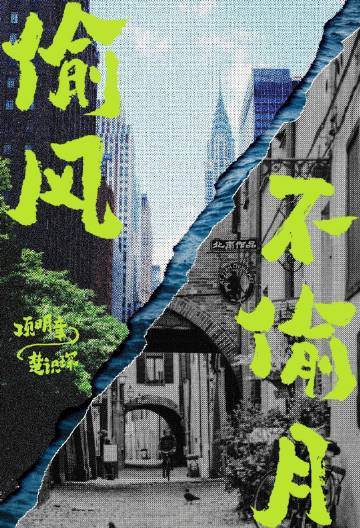
偷風不偷月
穿越(身穿),he,1v11945年春,沈若臻秘密送出最后一批抗幣,關閉復華銀行,卻在進行安全轉移時遭遇海難在徹底失去意識之前,他以為自己必死無疑……后來他聽見有人在身邊說話,貌似念了一對挽聯。沈若臻睜開眼躺在21世紀的高級病房,床邊立著一…
39.3萬字8 6359 -
連載136 章

我是卷王穿越者的廢物對照組
時書一頭悶黑從現代身穿到落後古代,爲了活命,他在一個村莊每天干農活掃雞屎餵豬喂牛,兢兢業業,花三個月終於完美融入古代生活。 他覺得自己實在太牛逼了!卻在河岸旁打豬草時不慎衝撞樑王儀仗隊,直接被拉去砍頭。 時書:“?” 時書:“操!” 時書:“這該死的封建社會啊啊啊!” 就在他滿腔悲鳴張嘴亂罵時,樑王世子身旁一位衣著華貴俊逸出塵的男子出列,沉靜打量了他會兒,緩聲道:“學習新思想?” 時書:“……爭做新青年?” 謝無熾面無表情:“6。” 這個朝代,居然、不止、一個、穿越者。 - 同穿古代卻不同命,謝無熾救時書一命。時書感激的找他閒聊:“我已經掌握了這個村子的命脈,你要不要來跟我混?吃飽到死。” 謝無熾看了看眼前衣著襤褸的俊俏少年,淡淡道:“謝了。我在樑王座旁當謀士,生活也挺好。” “……” 感受到智力差距,時書忍了忍:“那你以後要幹嘛?” “古代社會,來都來了,”謝無熾聲調平靜,“當然要搞個皇帝噹噹。” 一心一意打豬草的時書:“…………” - 謝無熾果然心思縝密,心狠手辣。 時書驚慌失措跟在他身旁當小弟,眼睜睜看著他從手無寸鐵的新手村黑戶,積攢勢力,拓展版圖,逐漸成爲能逐鹿天下的雄主。 連時書也沾光躺贏,順風順水。 但突然有一天,時書發現這是個羣穿系統,只有最後達到“天下共主”頭銜,並殺光其他穿越者,才能回到原來的世界。 “……” 一個字:絕。 時書看看身無長物只會抱大腿的自己,再看看身旁手染滔天殺孽、智謀無雙的天子預備役謝無熾。 ——他還不知道這個規則。 時書深吸了一口氣。 當天深夜。 時書拿著一把短刀,衣著清涼,白皙肩頭微露,誠惶誠恐爬了謝無熾的牀。
60.9萬字8 46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