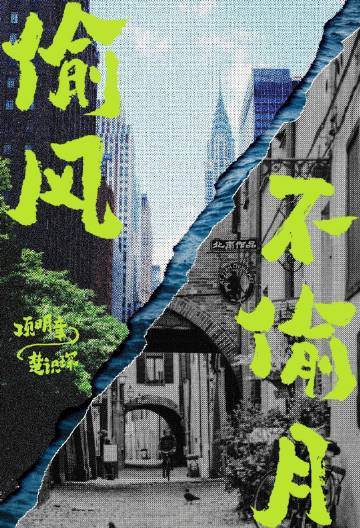《全世界都在等我們分手》 第59章 鈍刀03
韓荒時常來找林水程。
他很有分寸,不會太頻繁地來找他,就算是來也不會很尷尬,他一般都是和林水程一起照看流浪貓,或者問問林水程愿不愿意去看看他的辯論賽,又或者請林水程幫忙指導一下他的論文。
有時候林水程會拒絕,有時候林水程會同意幫忙。
韓荒看林水程一直待在家里,每天除了喂貓就是打連連看,問過他要不要加學校的救助組織。
大約幾十年前,星大旁邊曾有一個廢棄的園,因為資金條件不足而運轉不下去,里邊還有一批生病的沒有人管,星大學生就自發公演募捐,幫這些養老送終,后續也跟著接納一些流浪的小。如今,星城聯盟大學保護協會已經是全聯盟都比較有名的一個權益組織了,學生們會把流浪貓狗統一起來,運作貓咖狗咖和一系列小周邊產品、廣告等,支出收全部公開明,自給自足,剩下的錢還可以繼續用于保護和環境保護。
韓荒說:“我原來進這里邊是為了學習管理協調能力,星大保能從學生社團規模發展如今聯盟注冊權益公會和基金會,我爸指定我一定要進去學一學。師兄你也做了這麼多,要不要會和大家一起?事不多,也可以認識很多人……嗯,徐夢夢師姐也在里邊!”
林水程說:“謝謝你,不過我最近不太想出門,就不用了。”
韓荒看著他的短信回復,想說什麼又頓住了,轉而去找徐夢夢的聯系方式。
“啊?你問小林師弟啊,我和他也很久沒有聯系了,他出什麼事了嗎?”
“沒有沒有,師姐,我就是問一下。我以為你們是很好的朋友,你會知道一些他的近況。”
Advertisement
韓荒曾經在餐廳遇見林水程和徐夢夢,以為他們是關系很好的朋友。
徐夢夢回復說:“沒有的,我和小林師弟就是約個飯,但是平時沒有到特別好的朋友的關系,最近院系關閉,我也沒聯系上他,不知道他最近怎麼樣。我怕他太忙,也不好意思打擾他。”
韓荒皺眉道:“林水程在這邊也沒什麼朋友嗎?”
徐夢夢想了又想,努力思考:“好……好像沒有。他原來是江南分部的吧,我也沒見他有什麼同學找來玩……不過他有個男朋友!很帥的,應該當過兵,他來接過他幾次,我印象很深的。”
“我知道了,謝謝師姐。”
韓荒放下手機,眉頭深鎖。
旁邊的學生會干員湊過來問:“怎麼了啊會長,進展不順利嗎?我聽他們說前幾天遇到林神搬過來了,你還到他家去坐了坐?”
韓荒了腦袋:“不是這個事。”
他斟酌了一下,皺眉問道:“如果一個人……沒什麼朋友,假期的時候也不太愿意出門,他這樣一個人悶著會不會出什麼問題?”
干員猶豫了一下:“主席你說的是林神吧,我看不會有什麼問題吧?他們搞科研的不都這樣?宅男……不過當然了,林神肯定是咱們學校科研宅男里最好看的!”
韓荒還是皺眉。
干員笑嘻嘻地說:“哎呀行了行了,你這就是關心則,林神那麼強的人能出什麼問題?”
“算了,跟你們說也說不通,我先走了部門辦公室的水電記得關。”韓荒說,“下午有約了,我過去看看。”
“我呸!前腳在這里杞人憂天后腳就去約會!”干員唾棄他的背影,“談的人真是矯死了!”
韓荒和林水程約了下午去給幾只貓做驅蟲。
Advertisement
他敲開林水程的門時,見到林水程還穿著睡,看見他來時也有點意外:“你怎麼過來了?”
韓荒覺得有點奇怪,但還是告訴他:“學長,我們約了今天下午幫幾只貓驅蟲打疫苗。”
“我想起來了,不好意思我忘了。我是在想好像有什麼事沒做。”林水程了太,說了聲稍等,而后回房間換打點,穿鞋出門。
兩個人四抓貓,把幾只貓都塞進車后座,然后開著去了寵醫院。
鎖車時林水程鎖了好幾次都沒有鎖上,最后是韓荒發現他沒打開AI控制系統。他問道:“學長你……還好嗎?”
林水程深吸一口氣:“不好意思,這幾天睡迷糊了,有點發燒,反應力也不太好。”
韓荒沒說什麼,和他一起抱貓上去了。
小灰貓被檢查出有一點耳螨,需要另外開藥。醫生開單子前,問林水程想用哪個梯度價位的藥:“第一種價格貴點不過見效快,刺激也不大。”
林水程說:“就這種吧。”
醫生給他開了單子,要他去拿藥付款,剩下幾只貓的疫苗還沒打,林水程就頷首把這幾只貓拜托給韓荒,他自己去拿藥。
取藥在樓下,林水程拿著單子下樓,正準備進排隊隊伍的時候,被一個老人攔下了:“這個,小伙子,你們這里的機怎麼用的,能不能教教我?”
老人悠悠地拿著就診卡,在他眼前晃來晃去。他后背著一個小小的航空籠子,里邊是一只有氣無力的鸚鵡。
一樓很亮堂,玻璃窗很大,進來的是一種很奇怪的昏黃,像夕又像朝日,如同水過了濾鏡一樣,連著其他人說話的聲音都嗡嗡了起來。
那老人的不斷開合著,林水程發現自己本沒有聽懂他的話——老人里說的所有字他都清晰地聽懂了,但是組合起來就無法理解其中的意思,他只是下意識地理解了老人現在遇到的困難:他不知道怎麼用自助機取消他掛的號,并重新預約另一位專家號。
Advertisement
老人在他的指導下完了作,回來謝他。
這下林水程聽懂了他說的是什麼,他說:“謝謝你小伙子,我養的鳥它十五歲了,要不是它生病了,它說謝謝比我順溜。”
濾鏡被剝除,人中的聲音被放大了竄他耳中,幾乎一剎那轟然作響,接著是劇烈的耳鳴,帶起了劇烈的疼痛。
林水程捂住一側耳,用手指狠狠地住了疼痛的地方,指尖有些發抖。
他后有人往前走去,面前有人往后離開,他后有門面前也有門,這外邊的階梯和里邊的階梯一模一樣,他看不懂人們行走的方向。
他想不起來自己到這里來是干什麼的了。
——他到一樓來,是為了什麼事?
林水程重重地咬了一口自己的指尖,疼痛終于喚醒了他的一點神志。
他低頭看見了手里的病歷單,病歷單上寫著“傅落銀”三個字。
——我的生日是什麼時候,林水程?說錯了我也不怪你。
——你我什麼?你再一遍?
——林水程,小貓咪,你哪來這麼多傷心事?
“傅落銀”這三個字如同某種警鐘,如同電影中的圖騰,夢境與現實的參照,閃電一樣劃破他混沌的思緒。
他給一只小貓起了這個名字。
林水程猛然驚醒,抓了病歷單。
在他面前三五米的地方,“取藥”三個字清晰莊重地刻印在那里。
林水程回去的時候,韓荒正在配合醫生抓住鬼哭狼嚎的炊事班長,準備給它打疫苗。
首長見慣了大場面——它也是挨過幾針的貓了,今天過來純屬參觀游玩,已經窩在了凳子上開始打瞌睡。
小灰貓在首長邊繞來繞去,企圖把腦瓜挨在首長上尋找安全,只可惜屢屢被首長一爪子拍走。
Advertisement
林水程過去抱了小灰貓過來,擰開耳螨藥水給它滴。
“傅落銀”這只貓算是比較乖的,林水程一只手控制著它,另一只手迅速滴藥進去,貓咪耳朵抖了抖,他跟著用手了使藥水擴散,兩只耳朵滴完后,小灰貓跌跌撞撞地跳了下去,瘋狂甩腦袋,一不小心踩到首長上,又被首長著揍了幾爪子。
接近晚上時,林水程照常給貓咪們喂糧。
該到了各回各家各找各窩的時候了,首長施施然地竄進了房,外面的貓徘徊了一會兒,也都一只一只準備散去了。
林水程看了一會兒墻底下的小灰貓,猶豫了一會兒,蹲下來輕輕出手。
小灰貓走過來,嗅了嗅他的手心,又抬頭來看他,小小的眼睛里寫滿了大大的疑。
林水程順勢就把它抱了起來,進門關好房門:“你先在我這里住一段時間好不好?你的耳朵生病了,你在這里我好給你藥。”
小灰貓不習慣被人抱,它蹬了一下兒,從他懷里彈開了,繼而心懷謹慎地開始到嗅嗅走走,不過也沒有要出去的意思。
首長站在高,喵喵著,不無警惕。
林水程剪開一個枕頭套,套在大號瓦楞紙碗上,給“傅落銀”也做了一個窩。
“抑郁癥的部分表現,注意力無法集中,可能產生一定程度上的睡眠障礙,比如失眠、睡困難或者早醒,也有人相反,嗜睡,總覺得很累,很難清醒;一部分人會失去食,不想吃東西,也有一部分人表現為胃口大增,類似暴食癥狀;行力下降甚至喪失,甚至連起床的意志都會喪失,進而影響到一些其他的社會功能,嚴重一點的會伴隨幻聽、幻視和記憶障礙,比如會突發忘正在做的事,時間有長又短,可能在病人眼里,他們是突然到了某個地方的,就跟喝酒斷片一樣,經常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要做什麼。”
醫生對傅落銀說,“夫人之前是有幻視和幻聽,現在在藥治療下,只是嗜睡,現要換藥了,需要定期觀察反映況,一旦發現病人狀態不對,一定要及時通知我。做藝行業的人可能更加敏、富,夫人這段時間接的書籍、影視報刊等等也都需要控制一下,盡量不要去接那些帶負面彩的文學作品。”
“我知道,我和我爸都不常在家,我會讓他們看好我媽的。”傅落銀說,“辛苦醫生您了。”
他站起來送人,往外送到門口。
楚靜姝的況時好時壞,傅落銀今天回來看了看,讓家里所有人都沒想到。
和前幾次的歇斯底里不同,和上一次的尷尬也不同,今天楚靜姝看見他之后,只是默默流淚,哭得停不下來。
盡管什麼都沒說,傅落銀依然能從看他的眼神中領悟到一些莫名的緒,比如不甘,比如憾與怨恨。
管家和保姆趕把楚靜姝送回房了。
管家過來給他倒茶:“爺也休息一下吧,夫人休息了,您想吃點什麼東西嗎?”
傅落銀卻答非所問,他抬頭看了看樓上楚靜姝房間的方向,輕聲說:“我忘了是看書還是看電影,有過一個故事,一個家里,一堆雙胞胎,媽媽比較大的那個,結果大的死了。小兒子有一天回家和媽媽吵架,他媽媽問他,為什麼死的偏偏是他,要是死的是你該多好。”
管家臉驟變:“爺……”
“我媽不會說出這句話。”傅落銀笑了笑,“可能會這麼想,但是不會說出來。不說,我就當不知道,你們也得這樣。”
他今天回家,純屬是因為和林水程的家呆不了。
周衡安排了人上門大掃除,他又不喜歡吵鬧,干脆就回來看看楚靜姝。
至于他要看的林水程的資料,今天下午就送到了他手上。
傅落銀給自己泡了杯茶,回到他自己的房間里慢慢看。
他以前是查過林水程的資料的,不過沒仔細看。他是傅氏軍工科技的新任董事長,也是未來七的核心領導人之一,所有和他接的人都會查過一遍底細,確保不是商業間諜或者其他可以份的人。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