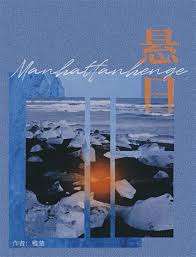《全世界都在等我們分手》 第26章 (2)
銀安靜沒說話,看他接下來要看什麼。
他其實約想到了,但是真正看這只小貓咪做出以前沒有做過的事的時候,他還是有些意外。
似乎是從上次他吻過他之后,林水程就變得主了起來。
林水程扣著他的手指,把自己進他的氣息中時,傅落銀到了他眼神中殘存的淡漠與執拗。
他其實一直以來都有個覺,林水程是個重的人,以前那些配合不是遷就而是共謀。
他配合他,縱容他,林水程第一次越界,第一次違背了人乖順的原則——他把他醒,只為滿足自己的私,紓解自己的愿。
可是傅落銀生不起氣來,他看著林水程眼底的星,只覺得這仿佛一個夢境——它不存在于現實,不是因為這樣的林水程多難得,而是林水程的魂不在這里。
“在目前已知信息的尺度上,兩座完全一樣的房子,會有什麼讓人區分出它們的標志差異?”林水程喃喃著,聲音沙啞好聽,汗水濡他的額發,也沾他的睫。
Advertisement
傅落銀輕輕拂開他的額發,他的指尖:“建造的人。”
“一個已經死了,一個不知道在哪里。建造者在幕后。”林水程低聲說,“我想不出來。”
聲音越來越輕,接近迷離。
傅落銀安靜聽著,隨后他說:“我小時候,和我哥一起玩過積木游戲。”
林水程打斷他:“你別說話。”
“相同的一組積木,相同的房子,我喜歡從左到右逐個搭建。我哥則喜歡從下到上,先做地基,再蓋上層。”
傅落銀好整以暇地看著他,對他的抗議不以為意。
林水程怔了一下。
“差異是會有的,好學生,只要你問,我就會把我的搭建方式告訴你。”傅落銀拭去林水程眼角的生理眼淚,傾吻他,“只要你問。”
“那我得問一個十五世紀的逝者。”林水程喃喃說,迷蒙中,他忽略了一切,忽略了傅落銀提起了從未提起過的家人,忽略了月正將他自己的照得瑩白發亮,無比人。“我得問……我必須問。”
Advertisement
因為那是他一開始就想要做的事。
似夢似幻的黑夜中,一切思緒都漂浮在虛無的熱浪之上,淹沒在親吻中。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