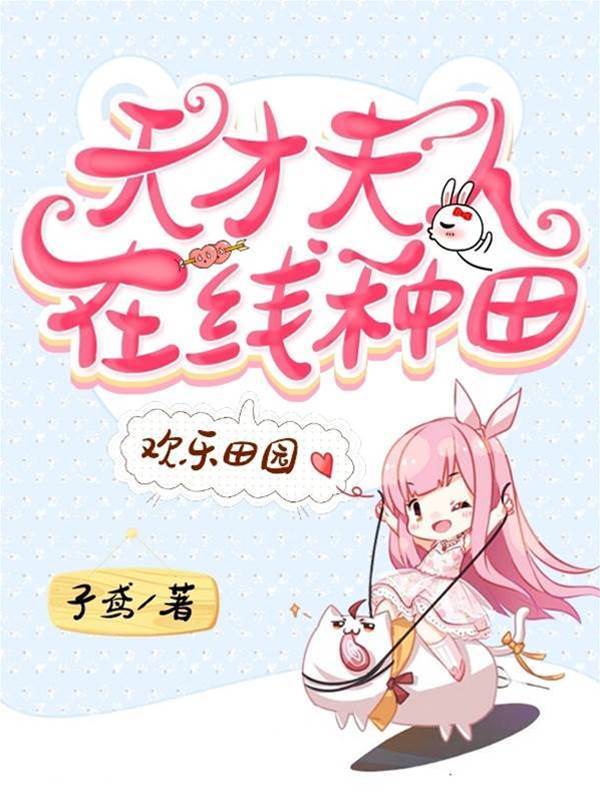《大唐風華路》 第746章 韓躍和武則天的第一次見面
韓躍不曾注意到武曌,或者說即使注意到了也只是一瞥而過,畢竟在場有幾百個學子,年齡從小到中年都有,穿著從貧寒到富貴皆存。
雖然武曌渾衫破爛,但是也有同樣衫破爛的學子,唯一有些區別的也許就是臉上涂抹了東西,但是韓躍不可能在幾百人中看的這麼細。
此時已經是午后未時,按照規矩必須要開啟鄉試第三題。
韓躍負手站在考棚正中,忽然悠悠吐氣開聲道:“今有一詩,名為憫農,此詩原是兩首詩詞分作,卻被我的孩子胡拼湊一起,但是為師覺得拼湊的不錯,陛下也認為帶著真,故而便用此詩為題,讓大家聽了寫一點心中的想法……”
他沒有自稱本王,反而用了一個為師的字眼,僅僅這一個為師的字眼,就讓在場學子們脈噴張。
為師這個稱呼,一般是不發出的。一旦這麼自稱,基本就認同了某件事。
那就是在場這一眾學子,從此都是趙王的學生……
武曌同樣心口跳了一下,不知為何忽然想到韓躍有兩個弟子,似乎那兩個弟子最初也只是研究院學生,后來才機緣巧合從學生晉升為弟子。
學生,弟子,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為弟子,才是師尊之徒,可以算半個家里人,可以是門下的生。
韓躍忽然改負手為舉手,然后緩緩一指在場所有學子,也不知是不是巧合或者其它,最后指尖恰好就指在了武曌的上,鄭重道:“我知道你們不人出寒門,家里都是勒了腰帶拱你們讀書,比如這位年書生,前來科舉都沒有一件像樣的服穿……”
眾人下意識順著韓躍指尖看去,武曌十分的低下了小腦袋,只覺得自己心口怦怦跳,臉蛋兒也跟著紅通了。
Advertisement
韓躍哈哈一笑,接著道:“不好意思啊,拿你做了個典型,為師之所以要說這番話,就是要引出鄉試第三題,所謂憫農,憐憫的正是農人。”
眾人顧不得再去看武曌,連忙屏氣凝息聆聽韓躍的話。
韓躍目再次一掃,語氣緩緩開聲道:“憫農,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誰不腐,從無傳千古。但因百姓淚,寒猛如虎……”
這原本是兩首詩,第一首詩是韓躍抄的,第二首則是韓躍自己作的,兩首詩被小石頭拼湊了一起,雖然屬于胡拼湊,但是詩詞的韻味竟然更上了一層。
在場不學子都是出農家,對于這兩首詩所刻畫描寫的意境一聽便懂,有人不由自主想起自己在農田里勞的爹娘,瞬間眼眶就變得潤起來。
韓躍念完詩后微微一嘆,輕聲道:“天下興亡,百姓皆苦,這一首憫農就當做鄉試第三題吧,為師希爾等不管落第還是進科,將來無論種田還是當,你畢生行事先不要忘了今日參加科舉之時,曾在這鄉試之中聽到了這憫農一詩……”
說到這里頓了一頓,忽然面轉為嚴肅,緩緩開口道:“鄉試第三場,現在開始,所有學子,請寫憫農觀后。”
這一首詩的觀后,好寫,也不好寫。
對于貧寒之家出的學子來講,這首詩寫的就是自家邊事,父母日夜在田地勞,甚至他們自己也常做農事。
那種辛勞和疲累,完全是刻進骨子里的東西。
但是對于富家子弟來言,這首詩的境界就有些遠離了。種田他們聽說過,但是不曾親自去試過,朱門酒臭,路有凍死骨,大唐時代兩級分化還是很嚴重的,富家子弟絕對不會去接貧寒百姓的農事。
Advertisement
偏偏這一次科舉舉國都可應考,寒門子弟固然占據了多數,但是富家子弟同樣也允許參加,而且富家子弟的學識一般都比寒門子弟要高。
可惜這第三題,他們無法發自心去寫觀后。
就連武曌都是如此,畢竟只了兩年的罪,兩年之前的那些時日,是國公之家的兒。
科場之中,漸漸有落筆沙沙的聲音。無論是寒門子弟還是富家子弟,都開始飽蘸濃墨筆疾書。
只要答完這一題,鄉試便算考完了,至于能不能晉升過關,那就要看各自的學識和發揮。
韓躍邁步在考棚緩行,不時低頭查看一下學子們的答題,遇見寒門學子寫的必然會點一點頭,遇見富家子弟寫的必然會皺一皺眉。
有些東西需要發自心,并非學識淵博就能代替,顯然富家子弟們對于憫農的悟并不深刻,幾乎所有人都是在強拼湊答題。
韓躍對此也不阻攔,反正鄉試只是第一道遴選,他繼續邁步考棚,不知不覺就走到了武曌的邊。
這一次,韓躍是真的大皺眉頭了。
因為他發現武曌寫的不行,明顯帶著一種強拼湊的味道。但是這個年衫破爛,按說應該是出自貧寒之家啊?
“難道是豪門之子,后來家世破落……”韓躍心中一,忍不住喃喃出聲。
他聲音很小,但是武曌軀明顯還是晃了一下。韓躍如今的目何等凌厲,瞬間就察覺了眼前年軀微晃的跡象。
也是從這微微晃一下,立馬坐實了他心中的猜測。
“原來還真是家世破敗的孩子!”
他口中微微一嘆,忽然俯低頭下去,溫聲道:“昨日種種,已往事,人之敗,在于未來。我見你筆法之間工整有度,字里行間既有秀氣又有霸氣,顯然你的格里面有種不服輸的神,勿要被眼前的困苦所嚇倒,所謂生活,無非是生下來就得活罪,但是為師卻不這麼理解,我認為今日罪是為了將來福……”
Advertisement
說著自覺自己是學子們的師父,有資格給學生們帶去一些溫和鼓勵,于是手輕輕一拍武曌肩膀,呵呵溫笑道:“努力吧,年,日出東方,其道大,大唐的未來,在于你們。”
……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57 章

棄婦當家:帶著福寶去種田
【穿書+悍妻+萌寶+種田+甜寵】 醫學大佬沈螢兒穿書了,兒子是未來的滅世大魔王, 剛生下孩子她男人就死了,婆家人說她兒子是剋星轉世,娘倆被攆出家門。 沈螢兒不靠天不靠地,就靠自己那雙手。 她醫術高超,敢跟閻王爺搶人,成了一方‘小華佗’。 她種的地,畝產千斤,家裡糧滿倉。 她養的豬,膘肥體壯,村里人人都羨慕。 經商,打鐵,寫作,十八般武藝她都會。 想娶她的男人擠破了頭。 沈螢兒:“哼,男人?那玩意兒咱不稀罕!” 反派小寶寶捏緊小拳頭:“我長大了保護娘!” 娘倆小日子過得紅紅火火,不料半路殺出英俊高大的男子,對她糾纏不清 那男人還帶著個娃,小豆丁仰著和她有七分像的包子臉喊,“娘親,抱!” 沈螢兒摸著自己肚子,一臉懵逼。 某人圈她入懷,咬著她的耳垂得意的笑:“為夫力氣大,一箭雙雕!”
28.5萬字8.09 121985 -
完結33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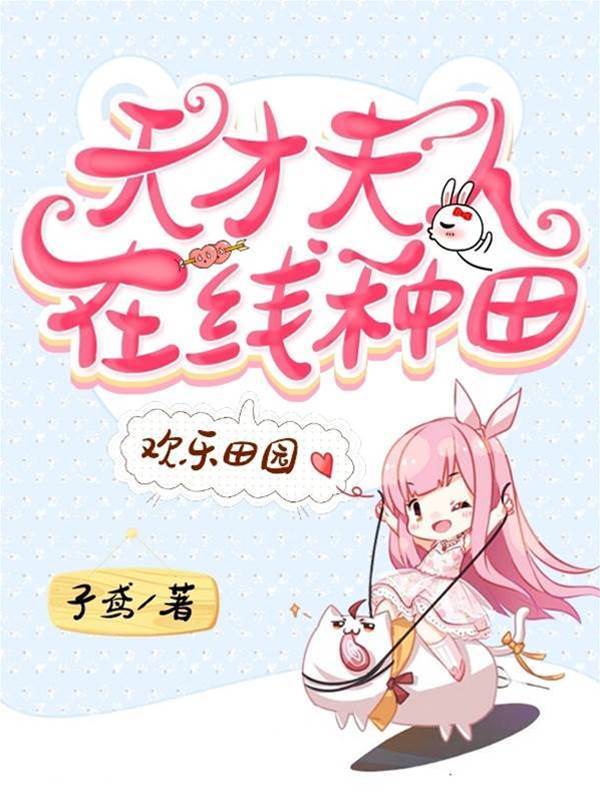
歡樂田園:天才夫人在線種田
研究出無數高科技產品的云若終于熬到退休了,只想從此在農村種田養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淡云流水了此一生。 可偏偏有人不長眼,要打擾她閑云野鶴的悠閑生活,逼她開啟打臉模式。 文盲?賠錢貨?網絡白癡?粗俗鄙陋的鄉巴佬?還想逼她嫁殘廢? 所謂家人對她的嫌棄猶如滔滔江水,綿延不絕,直到…… 世界頂級財團在線求合作,只要專利肯出手,價錢隨便開。 世界著名教授彈幕叫老師,只要肯回歸,他給當助手。 全球超級黑客直播哭訴求放過,以后再也不敢挑釁女王大人的威嚴。 十五歲全球最高學府圣威諾大學畢業,二十歲幾十項頂尖科技專利在手,二十一歲第十次蟬聯黑客大賽冠軍寶座,二十二歲成為最神秘股神,二十三歲自創公司全球市值第一…… 二十四歲,她只想退休……
62.5萬字8 15604 -
完結260 章

流放路上炮灰寡婦喜當娘
許柔兒萬萬沒想到,自己竟然穿成炮灰寡婦,開局差點死在流放路上!不僅如此,還拖著個柔弱到不能自理的嬌婆婆,和兩個刺頭崽崽。饑寒交迫,天災人禍,不是在送死就是在送死的路上。但許柔兒表示不慌。她手握空間富養全家,別人有的我們也有,別人沒有的我們更要有!“那為什麼我們沒有爹。”“爹?”許柔兒看著半路搶來的帥氣漢子,見色起意,一把薅來。“他就是你們的爹了!”帥男疑惑:“這可不興喜當爹。”“我都喜當娘了,你怕什麼喜當爹!”
47.3萬字8 29692 -
完結673 章

逃荒:我靠千億物資嬌養戰神殘王
末世戰甲軍部少將蘇縈穿越了。穿越到勾結渣男謀害丈夫的渣女身上。一來就流放,還附贈兩個娃和一個分分鐘要她命的殘廢丈夫。小的傷,大的殘,蘇縈大手一揮,這都不是事。流放路上沒吃沒喝還被追殺,灑灑水啦。物資空間在手,她左手肉,右手酒,刺殺的人來一個打一個,來兩個殺一雙。治得好殘廢丈夫,養得胖萌娃,在荒地之上開山建房,圍地種田,建立出屬于自己的文明和王國,做自己的女王。治好殘疾丈夫的病,讓他殺回上京,洗清冤屈,奪回屬于自己的一切后,蘇縈和離書往桌上一灘,一別兩寬,各生歡喜。某王咬牙攔人:蘇縈,你敢離了試...
119.9萬字8 141893 -
連載1569 章

首輔大人夜夜翻牆:餓餓! 飯飯!
一朝穿成農家女,娘親是喪夫新寡,幼弟是瘸腿癱兒。前有村賊吃絕戶,后有奸人縱災火,一夜之間,覃家滿目瘡痍。覃宛揉著含淚擤涕的妹寶頭發揪:“哭啥,有阿姐在呢。”一個月后,寧遠縣縣北支起一家食攤。月上柳梢的西街夜市,酸辣螺螄粉,香酥臭豆腐,鴨血粉絲湯……飄香十里。縣北食肆老板揮手趕客:“快!今兒早些閉門歇業,覃娘子要收攤了!”人前只吃魚翅燕窩的李府夫人托自家丫鬟:“覃家食攤的螺螄粉,多買些來,悄悄的。”云州知府設宴款待京城來的陸宰執:“大人請用,這便是遠近聞名的覃家香酥臭豆腐。”矜貴清冷,食性挑剔的陸修淡淡瞥了案桌一眼,拂衣離去。月末傍晚,人聲鼎沸的西街夜市,刺啦一聲,覃家食肆新雇的幫廚將黑色豆腐下了油鍋。覃宛順手遞上套袖:“係上,別濺了油。”“嗯。”碎玉擊石般清明冷冽。知府大人遠遠望見這一幕,冷汗津津。那頭戴冠帽,頂著一張人神共憤的清貴容顏,站在油鍋前行雲流水炸起臭豆腐的,不是陸宰執是誰!
142.6萬字8.18 3568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