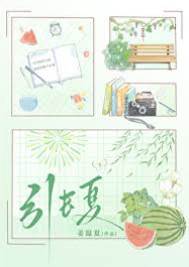《撒野》 第17章
顧飛聽到了幾乎同時響起的兩聲響。
當。
噗。
他同時打了兩顆石子兒出去,中了一顆,另一顆偏了,打在了地上。
“哎呀,可惜了,”蔣丞一邊往兜裡掏石子兒一邊說,“叉指導,你覺得他這次是失誤還是技達不到呢?”
叉指導?
顧飛半天才反應過來,x指導是什麼玩意兒。
“我覺得他的技還是有提高的空間,”蔣丞再次拉開彈弓,“他好像要換一種挑戰方式……這次是降低難度還是繼續……”
他的手一鬆,一顆石子兒飛了出去,沒等顧飛看清,他接著又一拉,第二顆石子兒也飛了出去,再接著是第三顆。
當當當。
三顆全中。
顧飛看著他的背影,如果不是現在這樣的場景,他還真是想給蔣丞鼓個掌的。
不是有準頭,作還瀟灑的。
李炎要在,看完消音版的這一幕,估計就不會再說看不順眼了。
不過這麼牛的表演結束之後蔣丞居然沒有給自己鼓掌,也沒有揮手鞠躬,一句話也沒說地就那麼站在了原地。
過了一會兒他低頭慢慢蹲了下去,雙手抱住了頭。
顧飛愣了愣。
表演得這麼投……嗎?
Advertisement
不過很快他就看到了蔣丞的肩膀輕輕了幾下。
這是哭了。
顧飛把最後兩口煙完,在腳邊掐掉,起繼續往裡走了。
他對看這種場麵沒什麼興趣,看個樂子可以,窺視彆人的傷,看著一個總跟個摔炮似的人哭,沒什麼意思。
這湖是有儘頭的,順著走也繞不了一圈,前麵有座長得跟爛地瓜一樣的山,過不去了。
顧飛找了一小片沒草的地,用了十分鐘才把火給點著了。
然後把袋子裡一捆捆的紙錢拿出來,扔進火裡。
有金的,有黃的,還有花的,麵值從無到幾百上千億,應有儘有。
顧飛看著騰起的火焰,把手過去烤著。
這種時候大概需要說點兒什麼,彆人大概會說收好錢啊我們都好的彆掛念啊錢不夠了說啊管夠啊,他要如果要說,還真不知道能說什麼。
沉默地看著火焰變換著,在濃煙裡騰起,在風裡招手似地晃,然後一點點變小,最後隻剩了青黑的煙。
顧飛拿了樹枝,拉了一下,黑的紙屑帶著火星飄起來,然後一切就都恢複了平靜。
他站起來,從旁邊把鬆散的雪踢過來,把一片黑灰燼蓋掉,轉離開了。
Advertisement
每年過了這一天,顧飛就覺得自己一下鬆快了,日子回到無聊裡,守著店,守著兔子一樣滿街竄的顧淼,去學校上著無聊的課,玩著弱智遊戲消除,看著老徐徒勞地想要拯救他於所謂的黑暗中。
那天蔣丞在湖邊沒哭多久,他燒完紙再回頭的時候,蔣丞已經沒在那兒了。
不過在學校上他的時候也看不出什麼異常,還是那麼渾是刺兒地拽著,上課照樣是趴著聽,或者閉著眼聽,偶爾半瞇著眼記個筆記。
他倆上課倒是互不乾擾,話都沒得什麼可說的。
隻是顧飛每次想起他在湖邊那一通演,就總擔心自己會笑出聲來。
“大飛,”周敬靠到他們桌子上,“大飛?大……”
蔣丞一臉不耐煩地拿起手裡的書在了他腦袋上,著聲音:“有話直他媽說!你真沒因為這個被人揍過麼!”
“!”周敬捂著腦袋瞪了他一眼,又看著顧飛,“大飛,我今天去徐總辦公室的時候聽他說了一,好像下月學校要搞春季籃球賽。”
“不知道。”顧飛說。
“你參加吧?我們班就指你了,你要不參加,肯定輸。”周敬說。
Advertisement
“彆煩我。”顧飛指了指他。
周敬轉趴回了自己桌子上。
蔣丞突然有點兒走神,下月?春季籃球賽?
三月算春天麼?
想到籃球賽,他就猛地有些慨。
以前在學校打籃球的日子一但回想起來,就會扯起些彆的不痛快,但偏偏又停不下來,那種痛快地在場上奔跑的回憶。
跟現在相比,那些回憶都是明亮的。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2722 章

惡魔校草欺上身:甜寵999次
簡介: 【寵文!甜文!寵到沒節操!甜到無下限!歡迎入坑。】 壁咚——他把她抵在牆邊,邪肆一笑,“做我女朋友。”蘇傾傾無辜眨眼,“帥哥,我不認識你。”“不認識?那這樣,是不是就認識了?”話音落下,洛夜軒就俯首噙住了蘇傾傾的唇……蘇傾傾沒想到一夜“借宿”就此惹上聖德學院頭號風雲人物,成了他同居女友!從此想逃逃不掉,想躲躲不了,天天被霸上!終於有一天,她被逼上床角跳起,“混蛋,你別再亂來了!”洛夜
248.1萬字8.18 177 -
完結9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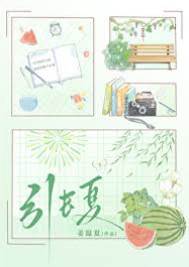
引長夏
桑渝和溫斯擇一起出生,一起長大。 一個乖巧討喜,除了一張臉,拿得出手的只有社牛的技能,和隨時躺平與世無爭的氣質。 一個恃帥行兇,除了一張臉,拿得出手的還有滿分成績單、各色光榮榜、競賽國獎…… 初二暑假。 桑渝耳朵裏滑過媽媽嘴上唸的溫斯擇千般好,反問一句“溫斯擇是不是應該本姓桑”,在抱枕飛過來的前一秒躍上陽臺。 溫斯擇正等在那兒,午後的陽光穿過樹蔭落了幾點在他身上。 男生一臉惺忪懶怠,指腹捏着包着“語文”書皮的漫畫書脊,擡起眼皮看向她,“桑渝,和我一起考到附中。” 桑渝:…… 她瞟一眼對方手裏的“人質”,遲疑點頭。 - 勤奮沒有回頭路。 桑渝頂着黑眼圈,在閨蜜暢想某人簡直校園文男主,雙眼直冒粉紅泡泡時無情戳破,“他數學語文分數沒我高——” 眼看泡沫要破碎,閨蜜一隻手掌捂過來,壓着嗓音低嚎。 想到自己和溫斯擇秀成績時那人眼皮都沒掀一下,桑渝示意閨蜜把手挪走。 “等着吧,看我考到第一把你的校園文男主按在地上摩擦!” 第二天,主席臺上溫斯擇演講結束,擡眼向下瞥來,目光躍過人羣落在桑渝身上。 “最後,祝賀桑渝同學在本市聯考中榮膺第二名,我等你——” 少年略一停頓,脣角微勾,低沉的嗓音傳遍校園每個角落。 “把我按在地上摩擦。” - 夏日暑熱,朋友去買冰棍兒。 剛出店門便看到不遠處的樹蔭下,平時裏一口冰都不沾的溫斯擇,站在桑渝面前,微低着頭。 “給我吃一口。” 桑渝把沒咬的那一面遞過去。 溫斯擇偏頭,在她咬過的地方,咬下一口。
32.6萬字8 8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