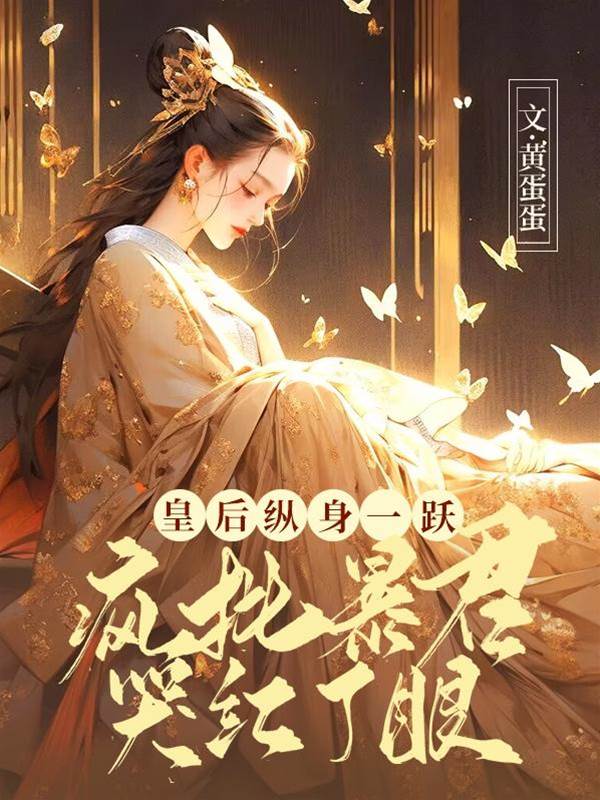《重生之女将星》 第81章 打劫
“打劫”江蛟結了一下,“什、什麼打劫”
“我們已經先到此地,天時地利人和,這都不打劫豈不是辜負了天意”王霸“王兄,這回可乾你的老本行了,還記不記得規矩”
王霸有些惱怒,又有些自得,隻道“我當然知道”
“那就先去踩盤子吧。”
“踩盤子是什麼意思”江蛟一頭霧水。
“這個我知道,”黃雄替他解釋“綠林黑話,事先探風勘察旁周。”
王霸哼了一聲,對禾晏道“你還知道行話啊。”
“我就知道這一句。”禾晏道“諸位沒有異議的話,就由我來安排一下如何”
眾人都瞧著。
“此地勢高,我們來的早,想來等別的組來此地時,定然已經乏累,神鬆懈。我們隻需埋伏在這裡,搶走他們的旗幟就行。我們一共五人,需一人上樹勘察況,其餘人埋伏周圍。這個人就是我,”禾晏指了指自己,“我在樹上。”
“待人前來時,王兄在前,將他們的人引咱們圈中。江蛟兄弟和石頭,你們一人持長,一人持長槍,分佈左右。黃叔在陣後陣,如此可將他們圍在中間。此時我再從樹上下來,我的九節鞭可趁機將他們的旗幟捲走。”
眾人恍然大悟,難怪禾晏要選九節鞭。真打起來一片混,未必有的機會近,可鞭子隻要隔著遠遠地一捲,便能將旗幟給卷過來。
“為什麼我要當餌”王霸不滿“我能陣。”
“因為你最厲害,”禾晏麵不改的瞎謅,“若是換我們其他人拿著旗幟去引人過來,旁人定會懷疑,你就不一樣了,你在新兵中本就厲害,搶到旗幟合合理,由你拿著,最好不過。”
江蛟有點想笑,最後忍住了。石頭和黃雄默默地低下頭去,唯有王霸一人深以為然,對禾晏安排的那點不滿,頓時也就煙消雲散。
Advertisement
“但這樣安排果真能行”江蛟有些懷疑,“若是他們手在我們之上怎麼辦”
“放心,我們已先到此地,比他們歇息時間長,力足。況且這樣左右包抄,攻守兼備,他們隻會自陣腳。再者我們的目的也並非同他們打架,而是爭旗。”
“兵書雲凡先戰地而待敵者佚,後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這裡頭五人,唯有江蛟和禾晏是念過書的。其他幾人還沒反應,江蛟卻是看向禾晏,神復雜的問道“你讀過兵書”
“略懂。”禾晏答道。
黃雄看了看江蛟,又看了看禾晏,嘆了口氣,“我記得你曾說自己讀過什麼手臂錄,眼下又說讀過兵書,你如此能耐,總有一日能馳名萬裡,同我們不在一。”
“不敢當。”禾晏笑道。
“反正富貴了別忘了我們就。”王霸小聲道了一句,大概覺得丟臉,又補充道“不過看你也不太像能富貴的樣子。”
禾晏聳了聳肩,道“那現在大家就先各自找個位置藏起來吧,我先上樹,你們吃點東西休息一下,江兄把旗子拿一麵給王兄,等會兒聽我哨音。我以鷓鴣哨聲為信,哨聲一至,王兄便拿旗幟去引人過來。”
眾人沒有異議,都四散開,各自找了地方藏好。禾晏則找了一棵高大的樟樹,仰頭爬了上去。
這爬樹的作倒是靈活,王霸見狀,小聲嘀咕了一句“跟四腳蛇似的”
禾晏一口氣爬到樹頂,找了最枝繁葉茂的一坐了下來,此刻風來,吹得人滿麵清涼,倒是說不出的舒適。這位置又高,能將附近一覽無餘,見暫時還沒別的新兵上來,便從懷中掏出一小塊乾餅,啃了兩口,又喝了點水。
等把這一小塊餅吃完,又靠著樹枝躺了幾分鐘,便見附近往下一點的小路上,傳來窸窸窣窣的靜。有一組新兵上來了。
Advertisement
禾晏登時坐直子,藏在樹葉中也沒彈,裡輕輕地發出鷓鴣哨聲,連吹三下。的哨聲同鷓鴣聲一般無二,若非提前打過招呼,江蛟一行人也分辨不出來。
藏在暗的黃雄對王霸使了個眼,王霸將水壺掛好,手裡拿著那麵旗幟站起來,往外走。
也不知是不是他慣來做這種打劫的營生做習慣了,裝模作樣起來,竟也人看不出一點端倪。王霸每走兩步還要左右看看,彷彿一個剛到此正在探路的人。
他這走著走著,便同那上山來的這組新兵撞了個正著。
“你”那新兵還沒來的及說話,王霸便捂著腰往回跑。他不捂還好,一捂,便教人看到他腰間那麵紅的旗幟。
新兵一愣,接著激起來,對後人道“他落單了,他有紅旗,弟兄們,搶啊”
那一群人聞言,立刻窮追不捨,王霸似是一人落單,並不戰,隻邊跑邊罵“呸,別跟著你爺爺再跟小心剁了你”
這群人視王霸手中的紅旗為囊中,便大笑追來,道“那你來剁啊這位兄弟,繳旗不殺”
“我繳你再追我就不客氣了”王霸警告道。
“到底是誰對誰不客氣啊”那群人一麵笑著,一麵追來,待跑到一林時,王霸突然停下來。
“怎麼,是跑不了”為首的新兵笑了,學著匪首的模樣,“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要從此地過,留下買路財”
王霸本來還想逞逞威風,聞言直接被氣笑了,他出腰間兩把巨斧,轉喝道“野悶頭鉆,哪能上天王山。搶到你爺爺我頭上,我看你是豬油蒙了心,招子不昏”
他這一連串山匪中語,誰也聽不明白。對方也不與他在此多纏,舉劍刺來,直向著他腰間的旗幟。
Advertisement
正在這時,後突然傳來響,左右兩側的草叢中,突然現出兩名年輕男子,一人持長槍,一人持鐵,正是江蛟和石頭。又聽得一聲巨響,手持金背大刀的頭壯漢已然躍至前。
方纔還是五對一,王霸被追的屁滾尿流,如今勢急轉而下,活像甕中捉鱉。四麵八方皆是伏兵,不過是四個人,卻弄出了十麵埋伏的盛況。
那幾人愣了片刻,笑意漸消,道“是埋伏他們使詐”
這一路上來,要麼是真刀真槍直接開搶的,要麼是埋伏在暗直接沖出來一場惡戰的。如這般跟唱大戲一樣,還有個餌在前邊做戲,實在是頭一回。為首的新兵一咬牙“怕什麼人數相當,怕了他們不,跟他們拚了”
一扭頭,幾人便一起沖了混戰之中。
說實話,這幾人雖然各有所長,倒也不至於說是萬裡挑一的地步,畢竟今日上山的所有新兵,都是涼州衛出類拔萃的人才。可怪就怪在,江蛟幾人,一手便占了上風。
一來是他們上來的時間長,早就在此休息吃過東西,養蓄銳了許久,而另一支新兵剛剛經過跋涉,都沒來得及坐下喝口水就陷混戰,自然於被。二來麼,就是他們這佈置的位置,很有些門道。
江蛟和石頭分在左右兩側,使得從頭到尾這幾人都被圍在中間。黃雄的大刀虎虎生威,倒和王霸的巨斧配合的天無,兩長兩短,攻守兼備,竟然讓這隻新兵找不出對方的一點錯,反而被頻頻於下風。
江蛟一槍挑開對方的劍,將對方的兵都給打落,有一個新兵就道“不行,搶不到旗,咱們還是快撤吧”
“怎麼撤”為首的新兵沒好氣的道“你給我找個空隙出來試試”
Advertisement
他好幾次都想突圍了,愣是找不到一個缺口。倒是如此消耗下去,他們自己人先撐不住了。
“不對啊,”一名新兵避開黃雄的大刀,轉頭問“他們怎麼隻有四個人,還有一個人呢”
對啊,打了半天,不過是五對四,還一人,但因他們被製的太狠,竟也沒注意到,這會兒經人提醒,立刻明白過來。新兵頭領就道“有詐注意保護旗幟”
話音剛落,就聽得王霸大吼一聲“禾晏,你看戲呢還不出來”
但見那枝繁葉茂的樟樹裡響起一個年輕快的聲音“來了”
林裡陡然現出一個赤影,年言笑晏晏,如燕子掠過,姿態輕盈,看在對方眼中卻如臨大敵,最邊上的一個男子還沒來得及將包袱藏起來,猛然間一條長影朝自己麵門撲來,他下了一跳,下意識的鬆開手,長影如蛇,蜿蜒靈活,卷著包袱遠去,年收回九節鞭,坐於樹上,笑盈盈的將手一抖,包袱皮飄落,手裡拿著一隻旗幟,笑道“多謝”一扭頭便消失在叢林裡,留下一聲“東西到手,撤嘍”
剩下的江蛟幾人如收到命令一般,方纔還激戰正酣,如今全然不戰,收起長槍就跑,這幾人本就被爬山累得半死,一番激戰後又疲力竭,哪裡趕得上,不過追了幾百步便不得力,眼睜睜的看著那群人跑遠了,再也沒了影。
“這是什麼土匪”有人累癱在地,咬牙切齒的大罵“真是無法無天”
“沒辦法,賊不走空嘛。”另一頭,禾晏正讓江蛟把手中的紅旗收起來,打了個響指道“走。”
“去哪兒”王霸問。
“打劫下一家。”
鴿子在窗戶上來回踱著步,有人掌心裡灑了些米粒,鴿子便落到他掌心,乖乖任由人從上取下銅管來。
肖玨看完紙條,遞給沈瀚,搖頭一笑。
紙條上字倒是很簡單,就隻說了一件事,禾晏在山上四設下埋伏,乾起打劫的營生,搶了好幾支新兵隊伍的旗幟。
爭旗爭旗,重在一個“爭”字,但爭得這樣,又明正大的,實在是絕無僅有。他們從頭開始就隻想著旗子,全然不想和別的新兵發生爭執,便是後來設下埋伏,也是以旗幟為重。沒有旗幟的,搶都不搶,任由旁人走過。有旗幟的,就趁火打劫,劫完就跑。
到頭來,損耗最小,得旗最多。
“他還會討巧的。”半晌,沈瀚才憋出這句話。
“不僅會討巧,也會用兵。”肖玨道。
“用兵”
“以近侍遠,以逸待勞,以飽待。”他彎了彎角,慢悠悠道“涼州衛的新兵,都被他耍了傻子。”
沈瀚無言,這年,真教人不知道說什麼好。他突然又想起一事“說起來這五人,竟都以他為首,且沒有異議。”
其實爭旗一事,除了同別的新兵爭,每一隻隊伍裡亦有爭執。每個人的習慣和戰法不同,未必就會和諧,有的小隊甚至會爭奪指揮權,以至於到最後一無所獲。懂得配合和懂得安排,也能看出新兵的能力。從這一點上說,禾晏已然備了調兵遣將的能力。
這五人裡,除了石頭外,其他人都和禾晏曾有過矛盾爭執,眼下卻沒有一個人因此同禾晏糾扯。
這也是這年的過人之。
“這幾人都不錯,”沈瀚想了想“江蛟他們同其他新兵手,都略勝一籌。到現在為止,尚無敗績。都督看,這幾人可否夠格進前鋒營”
肖玨輕笑一聲,不置可否,“不是他們能力強,是因為禾晏布陣。一個布了陣的小隊,一群散兵,本就不可同日而語。”
“都督是說”沈瀚似有所悟。
“左右張開如鶴翼,大將陣中後,你沒看出來麼,”肖玨道“他用五個人,布了鶴翼陣。”
大約是這訊息來得太過悚然,沈瀚一時沒有出聲。一個新兵若是會布陣,那幾乎就可以說明,這個人有問題了。沈瀚遲疑了一下“或許是巧合”
“是不是巧合,接下來就知道了。”肖玨道“飛奴。”
黑侍衛悄無聲息的出現他後“公子。”
“傳信給白月山上其他校尉,”他捧起桌上茶盞,淺淺啜飲一口,“下山路上,布陣。”
“都督”沈瀚急了“這樣會讓其他新兵下不了山的”
“放心,”年輕男子放下手中的茶盞,轉而撿起棋盒裡的黑子落下,剎那間峯迴路轉,他道“會有人破陣的。”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907 章

權寵悍妻
國公府的嫡女,嫁與將軍為妻,助他成為一代名將,卻被夫君婆婆厭棄,懷孕之時,他寵愛小妾,以剋星為由剖腹奪子,更拿她頂罪屠之。殺身之仇,涅槃重生,她殺心機姐妹,誅惡毒繼母,奪回母親嫁妝,渣男和小妾都一一死在她的劍下。重活一世,她不再癡戀,可偏遇那不講道理的霸道元帥。「我這個所謂國公府嫡女說白了隻是個鄉野丫頭,配不起元帥,不嫁!」「嫡女也好,鄉野丫頭也好,本帥娶定了!」「我心腸歹毒,容不得你三妻四妾,元帥若不想後院血流成河,最好別招惹我。」「本帥不納妾,隻養狼,專養你這頭女惡狼,事不宜遲,春宵苦短我們來吃肉,為本帥生一窩小狼崽子!」
147.6萬字8.18 390550 -
完結487 章

退婚后,修仙女配靠彈幕翻盤了
宋錦抒胎穿到了古代,卻沒想到有一日未婚夫上門退婚,看見他頭頂上竟然有滾動彈幕! 【氣死我了,這一段就是逼婚的場景了吧!】 【惡心的女人,長得都像個狐貍精!就知道天天貼著男人跑!】 宋錦抒:!?? 她怎麼就是狐貍精,啥時候倒貼了,還有這些彈幕憑什麼罵她!? 宋錦抒這才知道原以為的普通穿越,結果竟是穿進一本修仙文里,成了里面的惡毒女炮灰! 不僅全家死光。 哥哥還成了大反派! 宋錦抒氣的吐血,因為一個破男人,竟然會有這樣的結局,真當她傻? 退婚,果斷退婚! 【叮!恭喜宿主激活彈幕系統】 【扭轉較大劇情節點,難度:一般,獎勵極品健體丹×1,黃級雁翎匕(首次獎勵),屬性點:力量+1,防御+1】 擁有了彈幕系統,只要她改變自己和家人的原定命運,系統就會給出獎勵,憑借這個金手指強大自己,追求大道長生它不香嗎? 宋錦抒立志決定,認真修煉成仙,什麼男人都全部靠邊! 然而她卻沒想到,自家性子冷漠的哥哥宋錦穆,卻對她退婚的事耿耿于懷,竟然成天想收刮美男塞給她。 宋錦抒:“……” 球球了,現在她一心向道,真的無心戀愛啊! ps:女主低調,但不怕事,非圣母,慎入
98萬字8.18 18155 -
完結153 章

浮生沐煙雨
"她是丞相的掌上明珠,卻一朝跌入泥潭,藏身青樓為奴為婢。他是皇城司總指揮使之子,武藝超群,十歲便立下救駕奇功,得圣上賞識。卻以心狠手辣聞名于世。兩個本是云泥之別的人,rn卻因為一具被泡的面目全非的女尸,牽扯在一起。撲朔迷離的死因,莫名其妙的遭遇,將他們推入一張無形的大網。是人心叵測,還是命運捉弄?待到浮生夢醒,誰錯將春心暗付?他說,留下來,我定一心待你……她說,要麼殺了我,要麼放我走……"rn
55.1萬字8 7169 -
完結3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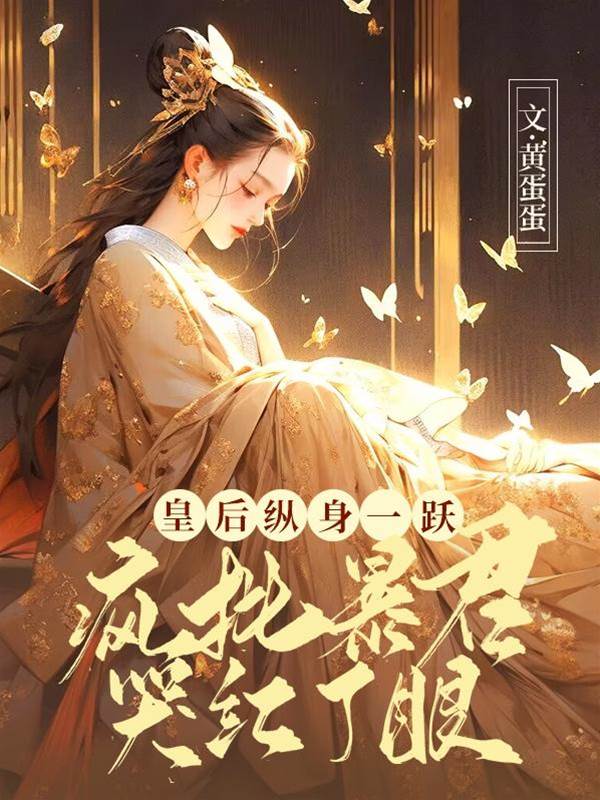
皇後縱身一躍,瘋批暴君哭紅了眼
【1v1,雙潔 宮鬥 爽文 追妻火葬場,女主人間清醒,所有人的白月光】孟棠是個溫婉大方的皇後,不爭不搶,一朵屹立在後宮的真白蓮,所有人都這麼覺得,暴君也這麼覺得。他納妃,她笑著恭喜並安排新妃侍寢。他送來補藥,她明知是避子藥卻乖順服下。他舊疾發作頭痛難忍,她用自己心頭血為引為他止痛。他問她:“你怎麼這麼好。”她麵上溫婉:“能為陛下分憂是臣妾榮幸。”直到叛軍攻城,她在城樓縱身一躍,以身殉城,平定叛亂。*刷滿暴君好感,孟棠死遁成功,功成身退。暴君抱著她的屍體,跪在地上哭紅了眼:“梓童,我錯了,你回來好不好?”孟棠看見這一幕,內心毫無波動,“虐嗎?我演的,真當世界上有那種無私奉獻不求回報的真白蓮啊。”
53.4萬字8.18 4176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