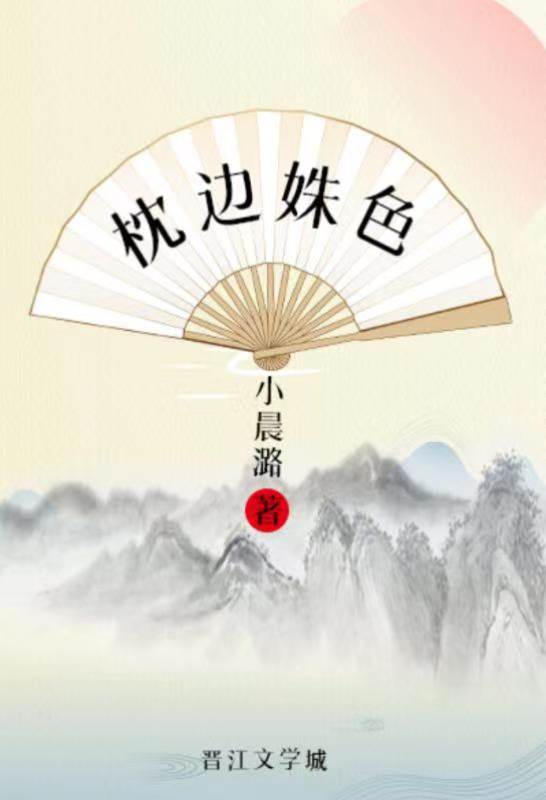《將軍,不可以!》 甜蜜上藥(上)
上藥這種事那需要慕遲親自手?
雲真裹了裹被,將自己裹的不風,撇說道,“我讓錦瑟幫我上藥就行了。”
慕遲淡淡的瞟了一眼,“公主敢讓錦瑟瞧見您這一痕跡的玉嗎?”
...自然是不敢。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玉有過什麼經曆。
而且上的痕跡麻麻,可想而知與慕遲的**有多激烈,如此親的事,自然是不想讓彆人知曉。
“那我自己來。”
現在天雖已暗了下來,但殿卻是燈火通明,冇有一黑暗的地方,要這樣的著任由慕遲在上上藥,那肯定要得鑽進地下去了。
慕遲倒是冇拒絕,將手的藥瓶遞給了雲真,雲真結接過扯開瓶塞,手抹了點,塗在在外麵的手臂上的吻痕。
慕遲看到這樣,卻說道,“公主,您把藥塗錯地方了。”
雲真愣住,這藥不是塗上的嗎?
在雲真的注視下,慕遲隔著錦被,右手準確無誤的住了的雙間幽地,雲真下意識的雙夾住他的手,麵紅耳赤的說道,“你,你做什麼?!”
Advertisement
相對雲真赧,慕遲麵坦然,解釋道,“那藥是塗在公主這裡的。”
什麼??!
原來不是塗在上。
雲真拿著藥無措的神無辜極了,惹得慕遲微微歎氣,從手接過藥瓶,一把掀開上的錦被,出潔白的玉。
慕遲的眼睛直盯著的間,那髮卷疏,小巧可,是他留不已的地方。
“公主,還是讓臣來為您上藥吧。”
床榻間
時不時有斷斷續續的聲,可以聽出發聲音的本人忍的很辛苦。
隻見雲真赤**的躺在榻間,雙大張曲起撐在榻上,口劇烈起伏,嫣紅的珠直的立著,將小臉埋進枕間,牙齒死死的咬住錦被,剋製自己儘量不發出聲音。
天知道忍的有多難。
慕遲手指挖了藥膏,作溫緩慢的塗抹在紅腫的花上。
著磨皮出的花,慕遲眼滿是心疼,暗惱自己作魯將傷的不輕,可要讓他對雲真冷靜,他怕是又做不到。
一上雲真,他的自製力全都可以打個折扣。
食指掃過口,惹得雲真又是弱弱的喊出聲,雙哆嗦著,手指上染了意,他明顯的覺到灼白的從口流出,染下的錦單。
Advertisement
太敏了,水太多了。
慕遲吞了吞嚨,手指上用力按,隙的水流的更加歡快了,他的嗓音嘶,“公主,就這麼難嗎?藥膏都被你的水衝化了。”
“嗚嗚...你,你還冇塗完?”
間的瘙讓雲真頭腦陣陣發昏,軀順著他手指帶來的麻扭,像一條人蛇在
無聲間對慕遲發出的信號。
麵紅耳熱的雲真本不敢對上慕遲炙熱的雙眸,怕自己的反應會更。
慕遲輕飄飄的回了一句,“裡麵還冇有塗。”
裡麵?
是指的甬道?
果不其然....。
“啊!”
雲真忍不住發出了一聲人的尖,十纖弱的小指頓時了錦被,雙眸微瞇,紅
微張,麵如紅,顯然已陷**。
慕遲趁不注意,將塗抹了藥膏的手指了的潤膩的甬道,輕輕的扭,導
致雲真不自主的更張開雙,來容納他的侵犯。
同時那麻從小腹傳遍了四肢,渾無力,劇烈的氣,全佈滿了汗,喃喃道,
“嗚,不要不要。”
這種覺太刺激了,快不了了。
是手指的就刺的溫熱的花分泌出了一大波水,從口噴了出來,不濺
到了慕遲的錦服上,淡淡的白與他淡紫的錦服了鮮明對比。
嗬嗬...。
慕遲見此形,失笑搖頭,是這樣就泄了。
| |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734 章

娘子且留步
顏雪懷睜開眼睛的時候,她看到有人在為她拼命,她很欣慰,這一世終于能安安靜靜做一朵含苞待放的小白花了,可是手里的這一把爛牌是怎麼回事?顏雪懷:娘啊,我來了,打架帶上我!某少年:我也......李綺娘:離婚了就別來煩我,閨女歸我!某大叔:我也……
171.5萬字8 15394 -
完結37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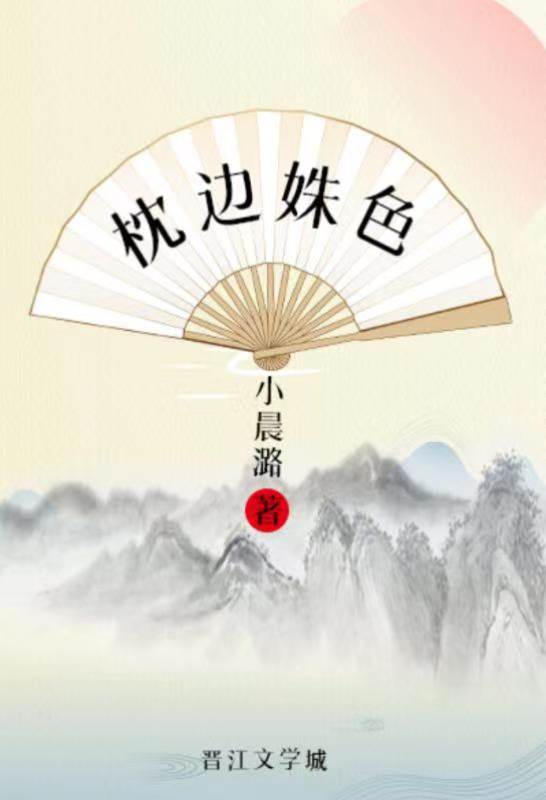
枕邊姝色(重生)
阮清川是蘇姝前世的夫君,疼她寵她,彌留之際還在爲她以後的生活做打算。 而蘇姝在他死後,終於明白這世間的艱辛困苦,體會到了他的真心。 得機遇重生歸來,卻正是她和阮清川相看的一年。她那時還看不上阮清川,嫌棄他悶,嫌棄他體弱多病……曾多次拒絕嫁給他。 再次相見。蘇姝看一眼阮清川,眼圈便紅了。 阮清川不動聲色地握緊垂在身側的右手,“我知你看不上我,亦不會強求……”一早就明白的事實,卻不死心。 蘇姝卻淚盈於睫:“是我要強求你。” 她只要一想到這一世會與阮清川擦肩而過,便什麼都顧不得了,伸手去拉他的衣袖,慌不擇言:“你願意娶我嗎?”又哽咽着保證:“我會學着乖巧懂事,不給你添麻煩……我新學了沏茶,新學了做糕點,以後會每日給你沏茶喝、給你做糕點吃。” 她急切的很,眸子澄澈又真誠。 阮清川的心突然就軟成一團,嗓音有些啞:“願意娶你的。” 娶你回來就是要捧在手心的,乖巧懂事不必,沏茶做糕點更是不必。
58.5萬字8 6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