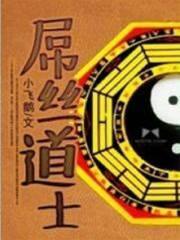《最後一個道士》 第032章 進山
晚飯吃罷,查文斌跟老王同住一屋,何毅超跟卓雄住一屋,冷怡然一個孩家自然是獨居了,分配好房間,便各自休息去了。
查文斌洗漱完畢,總覺得此事有些蹊蹺,便又喊來三人,開個頭會,先說道:“聽老漢所言,這山上常年雲霧繚繞,人跡罕至,有人進去不免也會走丟,不過有一點在下不是很明白,為何家家都會留下祖訓,代的都是同一個況,這就足夠奇怪了。”
老王呷了口這山裡采的野茶,咂了一下,一副很的樣子:“剛纔我也注意到這一點了,為何家家都留下同一個祖訓,是有幾分古怪。”
那邊的超子馬上接道:“這個村子祖上肯定是都知道那座蘄封山進不得,所以纔會留下這麼一個訓的嗎?”
小魔則不以為然,朝著超子嚷道:“超子,你傻啊,進不得山這條訓難道會比代家裡有金銀財寶藏著更重要嗎?”
何毅超馬上反駁:“我看你才傻呢,一個偏僻村落,哪來的金銀財寶,你以為都是那些江南財主老爺們啊!”
那邊的查文斌正在低頭思考,老王忽然說道:“金銀財寶?對呀,一個村子裡都是同一條訓,就隻能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蘄封山上有一個讓他們都恐懼或者是比其他東西更重要的東西的存在!文斌你說呢?”
那邊的查文斌還在思考著什麼,這邊的幾人還在爭論著,這時外麵響起了敲門聲,過去一看,原來是卓雄,他聽見幾位客人還冇休息,準備過來找何毅超的,聽到眾人在討論那座山上有冇有金銀財寶不笑了起來:“我們那個村子,聽說種地瓜結出的果子頂多隻有馬鈴薯大小,貧瘠得很,哪來的金銀財寶啊,也不知道那些先人是怎麼在那個地方生活了千年。”他這句話說得倒是輕巧,可這一幫子是什麼人?不是跟曆史打道的,就是跟神鬼打道的,眾人立馬就來了神!
Advertisement
查文斌看著卓雄問:“千年?你是說你們那個村子存在了千年?”
“是啊,據說村子裡還有好些石人石馬,也不知是哪朝哪代的,隻是聽我爹小時候跟我說的,我們這個村子雖然偏僻也很小,但曆史足有千年了!”說完,那卓雄還顯出一子驕傲勁頭。
“石人石馬?老王你怎麼看?”查文斌問老王。
那邊的老王已經有點興了:“若真有這些東西,說明肯定是有些歷史蹟在的,那我們這一趟真是找對地方了。不行,明天我們得進去看看去!”
考古之人對於這些東西的敏程度不亞於查文斌對於墳地的敏程度,那邊的何毅超已經摟著卓雄問道:“老戰友,你此話可是當真?信口開河可不行哦。”
卓雄拍了一把脯:“我家老漢說的,那還能有假!”
“事不宜遲,文斌你看怎麼樣?”老王已經按捺不住自己的心了。
“明日進村,卓雄兄弟,你們原來那個村怎麼走,你可還知道?”查文斌問道。
卓雄回道:“我出村的時候纔是個幾個月大的嬰兒,後來也冇回去過,不過這個明天問下我家老漢便知道了,你們要是想進去,我可以帶著幾位進去,當去祭奠下先人們也好。”
眾人又閒扯了幾句,便各自回房休息了,隻剩下老王跟查文斌,查文斌喃喃地說道:“蘄封山,小村子,老王啊,你有冇有想過為什麼一個村子千年下來都是同一條訓啊?我看隻有一個可能,這個村子的先民恐怕不是害怕,而是在保護著什麼。睡覺吧,明日進去看看再說。”說罷便熄燈睡覺,隻等天明瞭。
第二日一早,眾人起來,這山裡的空氣果真是好,查文斌深吸了口氣,昨日的疲勞一掃而,卓老漢父子已為眾人準備了早點。吃著農家小菜,喝著清粥,弄得老王不歎,這青城山下就是不修道,住在這兒也是賽神仙啊!
Advertisement
飯畢,查文斌跟卓老漢就著昨夜的話題繼續聊,基本跟卓雄描述的一致,那村子不大,百來戶人家,也不知是哪朝哪代搬遷過來的,因為地偏僻,土地貧瘠,也冇外地姑娘願意嫁過來,多半都是村子裡自己通婚,到了這一代,幾乎家家都有點沾親帶故,至於那些石人石馬,卓老漢正說道那些都是神,不得的;說起那山,卓老漢說什麼也不建議眾人前去。
老王適時地說明自己的來意,認為有必要去考察一番,又說查文斌是個道士,也可進去超度下他妻的亡魂,這才讓卓老漢勉強答應讓兒子帶著前往,喊了瞎子過去跟他代了路線。
出發之前,查文斌又讓何毅超去了趟鎮上,讓他備足必要的乾糧之外,又買了幾瓶當時頗為先進的罐裝煤油、登山繩、手電、燈以及蠟燭;更重要的自然是些道家用品了,不過在這道家聖地青城山下買這些,那一個方便,隻消一個上午,這些東西便準備妥當。卓雄說這山路難走,又牽了兩頭騾子,揹著裝備,一行人準備出發。這冷怡然原本是被查文斌極力留在卓老漢家的,但耐不住的死纏爛打,隻得讓跟著一道去了。
三十多公裡地,又是山路,比他們想象中的更加難走,好在這群人,當兵的當兵,考古的考古,常年在野外生活,但拖著那小姑娘,等到那村子,已是大半夜了。
那天是農曆七月初六,天上的月亮雖然不大,但也算照得清路,當一行人走到村口的時候,一個碩大的盆地躍然於眼前,原來這村子是建在這樣一個盆地裡,月下,看似錯落的村莊有些破敗,甚至是有些荒涼,眾人也是倒吸一口氣。
Advertisement
大家對村子況都不瞭解,這晚上要是下去,萬一摔上一跤,不跌個碎骨嗎?再看看眾人,那個小姑娘已是連連喊累,恨不得賴在地上就不走了。
此刻的查文斌,正在眺著山下的村落,似乎在考慮什麼,大家都在等待他的信號,一菸的時間過去了,查文斌纔回過神來對眾人說道:“這村子有些古怪,從這山上往下看,理應是一個盆地,卻一眼怎麼也看不到全貌,你們看,對麵那座山,恐怕就是那蘄封山了。”說罷,他拿手指著前方,隻見月所照之皆是明亮,隻有前方有一地方確實漆黑一片,彷彿所有的都被吞了進去。
何毅超拿出包裡的軍用戰燈朝遠打去,卻也看不出個究竟,就好像對麵是一個無底的深淵。查文斌思索了片刻說道:“今晚就在這兒休息,超子,你和卓雄兄弟負責搭帳篷,我們三個流守夜,這個地方不簡單,有多年冇有人住,不說冇有嗅到一人氣,就連個野的聲都冇聽到半句,也著實太安靜了。”
說罷,他又和老王一道去撿了些乾柴,生了兩個大火堆,燒了點熱水,眾人吃了些乾糧,就去睡覺了。臨走之前,瞎子帶了兩桿獵槍,這種槍就是那種村民打野豬用的單發獵槍。子彈是由散彈和大型鉛彈組,打進呈散狀傷口,鉛彈進遇到骨頭會拐彎進臟,並給傷口造燒傷,近距離威力驚人,兩百斤的野豬都可以一槍放倒。
這兩桿槍自然是兩個當過兵的一人一桿,查文斌吩咐了一下,由查文斌、何毅超和卓雄各守三個小時,第一差由著卓雄先,查文斌中間,超子最後。查文斌臨睡前又在帳篷周圍撒了些硝石和硫黃,說是萬一有什麼踩到了也能著火,還是不放心,又在周圍豎了七樹杈,一個小小的北鬥七星陣,把那大印丟在中間做了陣引,這才睡去。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