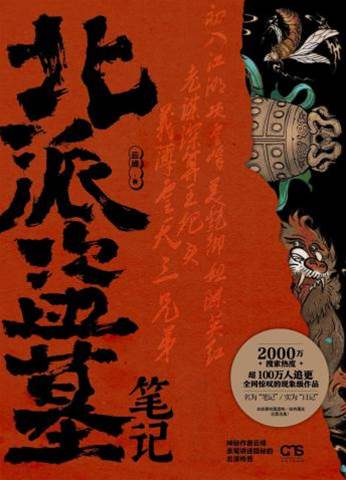《黑水屍棺》 五百二十七章 回家
大概是見我神出現了變化,粱厚載說到一半就停了下來,問我怎麼了。
我朝他揚了揚下「你接著說。」
粱厚載這才繼續說道「還記得東北老黃家的事吧,當初羅有方的字條出現道哥的課本裡,誰也想不通羅有方要幹什麼,可是現在想一想,他可能就是想告訴咱們,葬教的幕後主事要麼就是羅中行,要麼就是和羅中行有莫大的關聯。後來他隨著咱們一起進地宮,似乎也不是為了盜走玉啊。」
我依舊皺著眉頭「那是為了什麼?」
粱厚載「為了麻痹葬教的人。你還記得嗎,咱們離開地宮以後,莊大哥他們曾在老黃家一帶進行過一次大清掃,抓捕了大量葬教員。進地宮的那些傭兵隻是其中的一小撮人而已,這麼多葬教員守在老黃家附近,不隻是為了接應他們吧,我想,如果傭兵進地宮以後長時間沒有訊息,應該會有更多的葬教員進地宮。而羅有方隻要咬咱們,在葬教看來,就不需要派更多的人進去了。」
我說「可是,在那樣一個地宮裡,進去的人應該沒辦法和外界保持聯絡吧。那些進地宮的傭兵怎麼向外部傳達訊息呢?」
粱厚載想了想,說「他們應該有自己的手段吧。」
我還是不太相信羅有方是我們人,當即搖了搖頭「這種說法有點牽強啊。」
粱厚載接著說道「咱們再說這次的事吧,如果不是羅有方讓蘆屋正信散佈邪,你就不會中韓晉的詛咒,咱們也不可能來到這裡,當然也不會見到那個長得很像羅有方的古人。在看到那個老人歷經數年時間卻越變越年輕,我就想起了羅有方給咱們的提示,他曾經問你,相不相信這個世界有人能長生不老。」
Advertisement
的確,在看到那個老人的時候,我也曾回想過羅有方這番話。
粱厚載的話還沒說完「現在還有一件事讓我耿耿於懷。如果說當初羅有方真的造了張小攀的死,那就算羅有方是咱們的人,他也是罪孽深重。」
說完這番話,粱厚載就一直盯著我,似乎期待我給出一個答案。
我沉思了很久才對他說「雖說,羅有方做的這些事,都給了咱們很多提示,支的兩件法也回來了。但也沒有直接證據表明,他就是咱們的人吧?」
粱厚載「確實沒有直接的證據,可我覺得,羅有方是個聰明人,而且心思縝,不然的話,正道中人不可能這麼多年都抓不到他。他如果真想對付咱們,不可能每做一件事都給咱們留下這麼多線索吧?除非他是故意給咱們線索的。目前來說,這也是唯一合理的解釋了。」
劉尚昂忍不住問道「幻象裡頭的那個漢人究竟是幹嘛的呀,為什麼他和羅有方這麼像呢?」
粱厚載搖了搖頭「不知道,羅有方隻給了咱們線索,但沒給咱們答案。」
說完,他又轉向了我「道哥,你怎麼想?」
我了自己的太,問粱厚載「我還有幾副葯沒吃完?」
「六幅,三天的量。」粱厚載回應道。
我點了點頭,說「三天以後,咱們回趟老家吧,正好我也很久沒回去了。回去看看我的老爹老孃,順便再查一查張小攀。」
粱厚載問我「要不要先給馮大哥打個電話,讓他先查?」
我搖頭道「如果羅有方真是咱們的線,這件事也絕對不能讓馮師兄知道。」
粱厚載顯得有些不理解「為什麼?」
我無奈地嘆了口氣「不為什麼,總之知道這件事的人越越好。咱們回去以後,還是瘦猴著手調查吧。」
Advertisement
劉尚昂應了聲「沒問題。」
在之後的三天裡,我們三個不管幹什麼都提不起興緻來了,所有人的心思都在羅有方上。
三天過後,我們在火車站買了票,可在過安檢的時候,我卻被攔住了,因為青鋼劍和番天印。劉尚昂一看況不對趕給莊師兄打電話,要不是莊師兄派了當地的人趕來理,我搞不好要被弄到局子裡去了。
青鋼劍雖然斷了,還是把木劍,可它畢竟非常鋒利,屬於管製類的武。而番天印,則可以算得上文了。
這還是我第一次過安檢被擋住,以前走安檢的時候遠沒有這麼嚴格。
順帶一提,車組列車也是在那兩三年的時間裡出現的。
後來也是沒辦法了,我們就跑到二手車市場買了一輛四座的微型卡車,這輛車車主隻開了一年,車後還帶著卡箱,正好方便以後運棺材用。
當天下午我們就辦了相關手續,掛了個臨時車牌就上路了。
在以後的幾年裡,這輛車也了我們的專用座駕,不過我和梁厚載還是火車坐得更多一些,車一直是劉尚昂自己開著。
當我們一路風塵僕僕地回到老家時,已經是第二天的晚上了,我回來之前也沒跟我爸媽說,看看手錶,已經是十點多了,如果這個點回去,我媽肯定又要起床給我們做飯。思來想去,我還是決定今晚在旅館湊合一晚上,明天上午再回家。
沒想到剛在一家旅店裡安頓下來,我媽就給我打來了電話,問我什麼時候放假。
我說我已經回來了,見時間有點晚,本來打算在外頭住一晚上來著,結果被我媽好一頓數落,說我回到家門口了都不進家,在外麵住個什麼勁。
於是我又上了劉尚昂和粱厚載,退房、回家。
Advertisement
在我上大學以後,我爸媽就搬回老家了,但我對老家的路不算太,指揮著劉尚昂繞了好大一個圈子纔算是來到的村口。
劉尚昂一邊將車開進村子,一邊問我「道哥,你咋連自己老家在那都不知道呢?」
我說「沒回來過幾次,去年回家還是大舅和王強接的我,我一路上老走神,也沒記路。」
回想一下,我長那麼大,好像就回過四五次老家,頭兩次年紀很小不記路,後來師父帶來我過一次,可那次之後沒多久,村子外麵的公路就改道了,那是我唯一一次用心記路,結果記了也白記。
再後來,就是從寄魂莊回來以後的事了,可每次坐在馮師兄的車上,我基本上不是睡覺就是看手機,本沒特意去記路。
這次即便是進了村口,我還要不斷回想自己家在哪,還好我爸走到村路上來接我們,不然的話,我估計我都找不到家門。
我們一下車,我爸就問我「這是哪來的車,怎麼車牌不大一樣呢?」
我就向我爸解釋「我們在貴州二手車市場淘的,隻有個臨時牌。」
我爸盯著我看了一會,突然笑了「你這氣比以前好多了。」
聽到我爸的話,我也隻是笑了笑,沒說什麼。
師父過世的這兩年裡,說實話,我一直都沒有振作起來,頭一年為師父守喪就不用說了,剛上大學的時候,我解開了心結,可生活的狀態卻沒有改變,依舊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裡出不來。
直到渤海灣那邊出事,莊師兄的一通電話讓我心思重新回到行當這邊,不然的話,我都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能恢復過來。
我爸見我不言語,也笑了笑,跑去給劉尚昂找停車的地方了。
一進家門,屋子裡就飄來了麵湯的味道,我知道是我媽煮了麵條。
Advertisement
在我的老家有一種說法,「滾蛋的餃子,迎客的麵」,就是說有人從外麵回到家了,就給他弄碗麪吃,有人要離開家了,就給他包餃子。
我也不知道在老家還有多人奉行著這樣的老傳統,隻知道每次我回家的時候,我媽會給我們下麵條,每次我要走的時候,嗬嗬,臨行前的那一頓肯定還是麵條。
大概是希我能早點回來吧。
在我小的時候,我媽算是一個很溫婉的人,話不算太多,什麼事都現在行上,所以每次我犯了錯,通常不會說教,而是直接上掌。可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媽變得羅嗦了,每次我到了家就喜歡在我耳邊叨叨個不停。
這次也是,我一進門,我媽就湊在我跟前問我怎麼到了家門口卻不進家,問我在學校裡怎麼樣,問我怎麼和粱厚載、劉尚昂一起回來了……
我坐在餐桌前,一一回應著。
對於我媽的嘮叨,早年我也是很煩的,尤其是上高中那會,隻要一嘮叨,我覺頭都快炸了。
可後來我師父對我說,我媽之所以嘮叨,是因為見我的機會太了,總是有很多話想對我說,好不容易抓住了機會,恨不能將很長時間攢下來的話全都傾倒出來,才變了這樣的嘮叨。
從那以後,我再聽我媽的嘮叨,就不覺得煩了。有時候回到家,忙著餐廳裡的事,沒時間搭理我,我反倒覺得了點什麼似的。
跟我媽說話的時候,我爸帶著劉尚昂他們進來了。
見我一直坐在餐桌前聊天,卻遲遲沒筷子,我爸就對我媽說「媽,你先讓孩子吃飯,麵條都糗了。」
於是我媽又開始催我吃飯。
我爸媽住的地方,還是他們當年離開的那座老房子,隻不過在住之前收拾了一下,重新壘了牆、做了地麵,可不管怎麼說,這裡的條件都比家屬院那邊差一些。
房子再好,也是一堆混凝土、鋼筋搭起來的建築而已,可隻要有家裡在人,能吃上一口可能算不上特別味的熱飯,我就覺得心裡頭暖暖的。
家之所以是家,大概就是因為它有著這樣的暖意吧。
吃過飯,我和我爸坐在院子裡聊起了天,聊了什麼肯定記不得了,隻記得我媽從廚房裡拿來了鎮好的西瓜。
家裡已經沒有井了,西瓜也是放在冰箱裡,不知道為什麼,我總覺得冰箱鎮出來的西瓜遠沒有井鎮西瓜那麼清涼。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