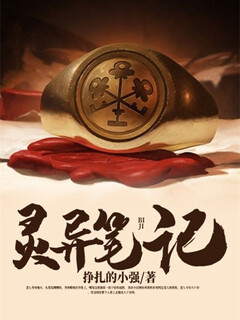《黑水屍棺》 第七十三章 迷陣
他這邊剛說完話,在牆壁塌陷出的那個口裡突然出現了一個人,那個口原本就是黑漆漆的一片,裡麵什麼都看不清,這個人就是「刷」的一下,突然站在了口,連一丁點腳步聲都沒有,就是這麼憑空出現的。
雖然梁厚載之前已經提醒過我,可我還是被嚇了一跳。
直到我回過神來,纔看清楚口外站著的,是一個年紀比我大些的,長得很好看,有一頭很長的頭髮,上不時散發著一種很清淡的香味。
呂壬霜,17歲,是屯蒙一脈的師侄,因為師族輩分的關係,見到我的時候要恭敬地一聲「師叔」,而我隻喚作「壬霜」就可以了。
其實壬霜這兩年變化比較大,我已經很難記清第一次見的時候是什麼樣子了,隻記得似乎和現在一樣,是個頗有姿的姑娘,頭髮的長度一直沒變過,香是天生的。除此之外,讓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腳脖上的那串銀鈴。
那就是一串用很細小的銀鈴鐺串起來的腳鏈,當壬霜邁著步子朝我們走過來的時候,銀鈴就會發出非常微弱但又十分清脆的「叮鈴」聲,那聲音傳到人的耳朵裡,會讓人在一瞬間放鬆下來,那種覺,就好像在那一瞬間,頭頂上的每一頭髮都突然變得了一樣。
來到莊師兄和馮師兄麵前,很恭敬地行禮:「師父、師叔。」
對了,剛才說了一件事,呂壬霜是莊師兄的弟子。
之後呂壬霜又看了看我和梁厚載,問我莊師兄:「這兩位師弟怎麼從來沒見過呢?」
莊師兄看了看我,有點無奈地笑了笑,他先是拍著呂壬霜的肩膀,對我說:「呂壬霜,我徒弟。」之後才對壬霜說道:「這是你左師叔!他拜師門的時候,你不是也見過了嗎?另一個是梁厚載,是你左師叔的朋友,趕人一脈的傳人。」
Advertisement
呂壬霜很驚奇地看了我一會,才朝我抱了抱拳:「左師叔。」
突然被人作了師叔,我還真有點不習慣,當時也不知道說點什麼好,就朝著呂壬霜乾乾地笑了兩聲。
我笑的時候,呂壬霜一直盯著我看,好像對我很好奇的樣子,可當著莊師兄的麵,大概又不敢失了禮數,才趕把眼神收回去,轉而對我莊師兄說:「師父,師叔祖他們已經到了鎮門堂了。」
莊師兄點了點頭,就讓呂壬霜在前麵帶路,他和馮師兄則一前一後地走進了那個口,臨進的時候,馮師兄朝我和梁厚載招了招手,示意我們跟上。
在口深,卻是是漆黑的一片,途中,我也能很清晰地聽到每一個人腳步聲。
這也就讓我更加疑,剛才呂壬霜是怎麼無聲無息地突然出現在口的?
走了沒多遠,我就看到地麵上出現了一些鮮綠的小點,點的數量一共有九個,在道路的中央排一列。馮師兄就對我說:「這些夜石裡摻著我們那一脈特製的土,放在這裡,是做陣眼用的。這幾個陣眼,破不了,要想從這地方出去,隻能按照特定的次序踩它們。」
馮師兄平時說話很像現在這樣,說出每一個字的時候都著一驕傲,我覺,地上的那些夜石,或許就是馮師兄佈置下的。
之後,馮師兄就走到了那些夜石前,用左腳掌在第一顆石頭上踩了四下,又在第二顆石頭上踩了十一次,每顆石頭被踩的次數都不一樣。
馮師兄一邊踩著,一邊慢慢朝著最末端的一顆夜石移,從石頭上散發出來的有種很朦朧的覺,馮師兄的影被這種輝映襯著,似乎也變得朦朧起來,直到他的腳掌在最後一顆夜石上踩了七下之後,馮師兄整個人都被那種輝籠罩起來。
Advertisement
那樣的景,真的是有些真假難辨,從石頭上散發出的芒明明很微弱,馮師兄又被覆蓋其中,可在一剎那之後,我就看不見馮師兄的影了。
他竟然就這樣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莊師兄上來拍了拍我,我才從驚愕中清醒過來。
莊師兄沖我笑了笑,問我:「你記住每顆石頭都要踩幾次了嗎?」
我仔細回想一下,又沖著莊師兄點了點頭。
之後莊師兄就讓我先去踩那些石頭,說是讓我一下豫鹹一脈的絕學。
我學著馮師兄的樣子,用腳踩在月石上,當我的腳掌到第一顆石頭的時候,就覺一陣涼意順著我的腳掌,一下竄上了的口。好在這樣的涼意並不會讓人覺難,它僅僅是出現了一瞬間,就消失得無影無蹤。
而在它消失的那一瞬間,我有種覺,覺夜石上的芒突然變得亮了起來,每踩完一顆石頭,這樣的覺就會強烈一分,但我心裡也知道,這隻是一種飄渺的錯覺而已,夜石上的芒沒有變亮,口中還是一片漆黑,不知道為什麼,莊師兄、梁厚載還有呂壬霜的影,卻似乎變得越來越模糊了。
當我最後一次踩在第九顆夜石上的時候,周圍突然間變得無比明亮。
我抬起頭來看,卻發現自己來到了一個寬闊明亮的隧道裡,隧道兩旁是用石板砌起來的高大石牆,上麵每隔一米多就有一點著的火把,火映襯著牆麵上的龍紋浮雕。
我心裡正驚奇,就覺肩膀被人拍了一下,回頭一看,就看見馮師兄就沖著我笑,可除了馮師兄,其他人卻不見了。
我張著,又朝四周觀了一會,確定這不是錯覺,才問我馮師兄:「我怎麼……怎麼就到這來了?」
Advertisement
馮師兄笑著說:「其實你從剛才開始,就一直在這。」
我沒明白馮師兄的意思,就問:「不是,怎麼回事,我咋聽不明白呢?」
馮師兄朝我擺了擺手,說:「這個我不能解釋得太細,咱們三脈的傳承不能互通。」
就在我和馮師兄說話的這一會功夫,梁厚載也來到了我邊,我不知道他是怎麼出現在這的,也不知道他是在什麼時候出現的,隻是當我覺到邊有人在息,回去看的時候,梁厚載就已經站在我邊了。
在梁厚載之後,呂壬霜、莊師兄也依次出現在了隧道裡,每個人都像是憑空出現的一樣,每個人出現的位置,都在我視覺的死角上。
不隻是我,在他們出現的那一個瞬間,包括梁厚載和我莊師兄,都沒有看到他們。
雖然我也知道,寄魂莊三脈的傳承不能互通,可心裡實在是好奇,最後還是忍不住去問馮師兄:「這地方,到底咋回事啊?」
馮師兄嗬嗬笑著,說:「這種事,說不得,說不得啊。嗬嗬,不過有件事可以告訴你,在這個隧道裡的確做過一些特殊的佈置,你在這裡麵行走的時候,會有一種時空錯的覺。其實時空是不會的,錯的僅僅是你對空間的覺。」
馮師兄說完,莊師兄又在我旁邊補充了一句:「其實就是一個**陣,豫鹹一脈通36種大陣、72種小陣,這種**陣,隻能算是72小陣裡最簡單的一種。」
莊師兄一邊說著,一邊從牆上拔下一火把,朝著隧道盡頭的暗走去。
馮師兄跟在莊師兄後麵,問莊師兄:「你們屯蒙那一脈,不也有108種陣法?」
莊師兄點頭:「對啊,要說起來,你們那一脈的陣法,還是屯蒙延出來的,不過年代久了,兩脈的差別就越來越大了。你們豫鹹的陣大多都涉及風水,屯蒙這邊的陣法都是用來筮卜的。」
Advertisement
聽著兩個師兄你一言我一語地討論陣法的事,我心裡就覺得酸酸的。
人家那兩脈都有這麼多陣法,可我們守正呢,所有的陣法相加起來也不過六七個,我師父對我說過很多次,在我們這一脈的所有陣法裡,最厲害的就是封門陣,可就算是這門陣法,和豫鹹一脈的那些陣法比起來,也是相差甚遠的。
儘管馮師兄、莊師兄和我一樣,都是寄魂莊的門人,可畢竟是不同的脈係,在我心裡,也總是希我們守正一脈的傳承不管在那個方麵,都能比另外兩脈強上一點。
來到隧道的盡頭又是一個漆黑的口,中似乎沒有一點點亮,整個口就像是一塊巨大的黑幕,和隧道連在一起。
可當莊師兄舉著火把走進口的時候,我才發現這個其實很淺,沒走幾步就到頭了,隻是壁全部被塗了黑,才給人一種深不見底的覺。
我走到口邊緣的時候,莊師兄突然朝我壞笑了一下,然後我就看見他用什麼東西一下滅了火把。
火把一滅,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
當時我正站在口的邊緣上,裡麵黑乎乎的一片,竟然讓我產生了一種站在懸崖邊上的覺,黑暗中,我看不到莊師兄,隻是覺得眼前的很高、很深,我覺在我前麵幾厘米開外的地方就是萬丈的深淵,我明明知道眼前的是什麼樣子的,可就是耐不住會有這樣的覺。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1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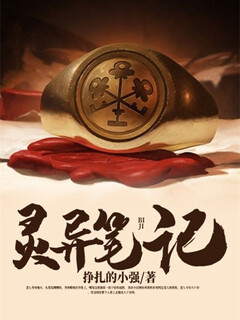
靈異筆記
為什麼自從做了眼角膜移植手術後的眼睛時常會變白?是患上了白內障還是看到了不幹淨的東西?心理諮詢中的離奇故事,多個恐怖詭異的夢,離奇古怪的日常瑣事…… 喂!你認為你現在所看到的、聽到的就是真的嗎?你發現沒有,你身後正有雙眼睛在看著你!
29.6萬字8 7634 -
完結1126 章

茅山後裔
我是一個"災星",剛出生就剋死了奶奶,爺爺以前是個道士,爲我逆天改命,卻在我二十歲生日那天離奇死亡.臨死前,他將一本名爲《登真隱訣》的小黃書交給了我,卻讓我四年後才能打開…
291.7萬字8.18 38465 -
完結1395 章

我的女友是喪屍
當災難真的爆發了,淩默才知道末日電影中所描繪的那種喪屍,其實和現實中的一點都不一樣…… 原本到了末世最該乾的事情就是求生,但從淩默將自己的女友從廢棄的公交車裡撿回來的那一刻起,他的人生軌跡就已經朝著完全不受控製的方向狂奔而去了。 造成這一切的原因很簡單,他的女友,變異了…… 等等,那隻夏娜,你鐮刀上挑著的好像是我的吧! 學姐!不要總是趁我不注意的時候打我啊! 還有丫頭,你這樣一直躲在旁邊偷笑真的好嗎? 最後……不要都想著咬我啊啊啊啊!!!
324.9萬字8 2366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