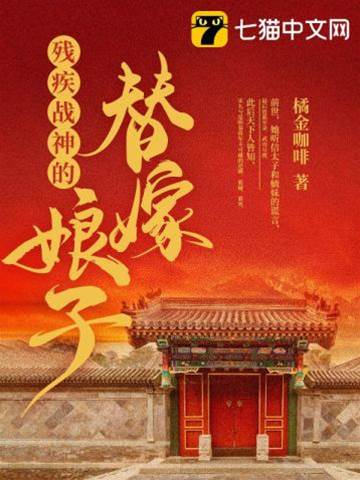《鹿門歌》 第121章
聽到陸子謙的呼救後,洪震霆即刻趕到鄰房,可惜那幾名“閹人”武功未見得多高,輕功卻俱是一流,足足追襲了二里地,他們始終未能追上那幾名刺客,最後只好無功而返。
平煜等人趕至陸子謙客房外時,洪震霆等人恰好從外頭返轉,眉間約可見疑之。
事出突然,他們不是沒懷疑過這幾名刺客的真實來歷,只他們沒料到平煜爲了引陸子謙吐真相,早在從萬梅山莊出來便開始做局,方方面面都考慮得極周詳,加之坦兒珠的確一貫是東廠垂涎之,故老練如洪震霆,一時也未能看出破綻。
見平煜和李攸“聞訊”而來,洪震霆目復雜地看一眼陸子謙,對平煜道:“平大人,那位王同知去了何?”
在此之前,他因不知陸子謙藏有一塊坦兒珠,雖然一路相伴,卻並未專門派人日夜保護陸子謙,是以今夜那幾名刺客能輕而易舉地闖陸子謙的客房。
可在知道東廠爲何找陸子謙的麻煩後,他震驚之餘,第一個懷疑的對象便是王世釗。
畢竟此人雖在錦衛任職,實則是王令的侄子。先前衆人在萬梅山莊一道對付金如歸時,王世釗又全程在場,既得知最後一塊坦兒珠的下落,焉能不有所行。
平煜本就打著給王世釗栽贓的主意,聽洪震霆這麼問,譏諷一笑,順水推舟道:“自從王公公跟皇上率軍離開京城,王同知因掛心王公公的安危,前日在金陵時,只給我留了一封信,便不告而別,這幾日人影全無。王同知跟王公公叔侄深,想是怕戰場上刀劍無眼,已自行前往宣府跟王公公匯合,也未可知。”
言下之意,王世釗如今不在錦衛,不再他管束,越發可以放開手腳替王令收集坦兒珠。
Advertisement
陸子謙驚魂未定,一旁聽見,擡頭狐疑地看向平煜。
平煜恰好朝他看來,眸意味不明。
對一陣,陸子謙敗下陣來,僵地收回目。
最初的慌張過後,他已經多恢復了鎮定,開始仔細回憶今夜的每一細節,照當時刺客出現時的形來看,有些地方很值得細細推敲。
可他明知如此,卻別無他法,因坦兒珠已然暴,無論東廠還是錦衛,都斷不會輕易放過他。
爲今之計,他只能將坦兒珠乖乖奉上 。
傅蘭芽他想救,可他也不想給京中家人惹來無窮無盡的麻煩。
唯一讓他到不甘心的是,相較於東廠,他竟寧肯將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訴平煜。
平煜想必也是吃定了這一點,所以纔會在他面前如此沉得住氣。
“陸公子,我十分好奇,你上怎會有一塊坦兒珠?”平煜了陸子謙一晌,似笑非笑地開口了。
陸子謙眼皮掀了掀,一哂,緩緩道:“此事說來話長。天快亮了,若平大人不想讓人半途相擾,煩幫我屏退不相干的人,容我細細道來。”
等平煜做好一應安排,房重歸寂靜,陸子謙便從懷中取出一本書,擱置於桌上那塊坦兒珠旁邊。
他先將當年如何無意中救了李伯雲一事代明白,這才道:“二十年前,李伯雲有位投意合的未婚妻,不幸的是,這位未婚妻還未過門便病亡了。”
洪震霆吃驚不小,“難道伯雲是因爲這個緣故纔去鎮教搶奪坦兒珠?怪不得當年那位未過門的杏娘病逝後,伯雲病了一段時日,忽有一日登門來找他姐姐,只說如今倭寇作,他堂堂七尺男兒,不能茍安一隅,要幫府剿倭,不等他姐姐細問,便匆匆而別。我和他姐姐只當他已對杏孃的事釋懷,沒想到他竟是去了夷疆。”
Advertisement
說到此,洪震霆悲從中來,長嘆一聲,緘默了下來。
陸子謙頓了頓,毫無波瀾道:“所謂剿倭不過是託詞,李伯雲實則是在聽得坦兒珠之名後,既生了一能復活未婚妻的僥倖,也生了貪念,唯恐這等稀世奇珍落旁人手中,這才連夜點了門下幾名明幹練的門徒,跟他一道趕往夷疆。
“也就是在那回鎮教戰時,他不慎被右護法放出的毒蛇咬傷,雖因力渾厚,僥倖活了下來,一武功卻因此盡喪,所帶的門下弟子也悉數命喪大岷山峰頂。
“好不容易傷愈,他想起因著自己的貪慾,不但武功全廢,連教中門徒也折損大半,自覺無回去面對洪幫主夫婦及逍遙門的幾位長老,便藏著奪走的那塊坦兒珠,滯留在夷疆,終日渾渾噩噩,借酒度日。數月後,他在一座荒廟中夜宿時,無意中發現了鎮教教徒的蹤影,跟隨一路,聽到這二人說話。
“這兩人說,當時來教中搶奪坦兒珠之人,因掩了臉面和招式,無從得知究竟是哪門哪派。
“多虧教中的左右護法細細打探,現已知大致知道其中一人便是東蛟幫的幫主。而另一塊不慎失的坦兒珠,因當時西平老侯爺率軍掃鎮教所在的大岷山山腳,十有八|九落在了西平老侯爺的手裡。教主如今病危,右護法打算讓左護法留守教中,自己則去京中想辦法從西平侯府將那塊坦兒珠出。”
此話一出,屋子裡肅穆得針落可聞。
不止平煜,連李攸和洪震霆都出錯愕表。
平煜臉沉沉的,冷聲道:“你是說我祖父奪了一塊坦兒珠,而右護法知曉此事?”
不對,在他的記憶中,祖父從未提起過坦兒珠三個字。若府中真有坦兒珠,此又曾在江湖上掀起腥風雨,祖父就算不相信關於坦兒珠的傳言,勢必也會對家人有所提及。
Advertisement
故,這一切不過是右護法一廂願的猜測罷了。
陸子謙搖頭道:“李伯雲當時不過略一提及,並未深究這話裡的真假。但他見鎮教對坦兒珠如此執著,本已經心灰意冷,卻因著一份不甘,在聽到那兩名教徒的談話後,也跟著離開了雲南,趕往京城。
“到了京城後,他易了容貌,用剩餘的積蓄在京中西平侯府附近開了一家酒肆,爲求恢復功力,每日契而不捨習練心法。
平煜聽得西平侯府四個字,不易察覺地握了手中的茶盅,好不容易纔按耐住自己打斷陸子謙的衝。
“一年過後,李伯雲力有了恢復的跡象,無事時,便時常拿著那塊坦兒珠揣,時日久了,他發現那上頭所雕刻的東西似是一幅地圖,於是便蒐羅來京城所能蒐羅到的地圖,攤開畫卷,整日裡對燈研讀。可惜的是,他直將手中地圖一一比對完畢,始終未有頭緒。
“無奈之下,他想起當年鎮教一戰時,曾聽左護法痛罵那位潛教中的叛徒,稱此人爲布日古德,罵此人是韃子。他心中一,索打算找些北元境的地圖來看。
“因當時朝中大開馬市,時有北元人率馬隊到我朝,販售馬匹的同時,換些布料和瓦回去。李伯雲便從一位北元商人手中高價買下一幅北元境的地圖,又藉著跟馬隊中隨從攀談,打探北元可有什麼起死復活的傳說。
“那人倒是說起了一座山名,說那山下有座廟,被當地人奉爲神祗,據說月圓時分,廟中神明或會顯靈,若帶著供品進廟,誠心許下願,沒準能神明,達所願。
“可惜的是,那山雖不難找,廟卻因有神明護佑,有人見過,傳說中,只有有緣之人才能有幸尋到廟的所在之。聽說百年前,有一位北元王爺無意中勘破了廟外的機關,費盡千辛萬苦求得了神明的垂憐,喚回了他本已嚥氣的母親。”
Advertisement
平煜自是不相信所謂起死回生的鬼話,然而聽了這番話,卻免不了想起當年流放時曾在北元境見過的異象,尤其是那座一夜之間消失的古廟,最爲古怪。
便問:“那座山是不是託託木兒山,就位於旋翰河附近?”
陸子謙啞然,看了看平煜,點頭:“正是。”
平煜眸中起了波瀾,難道此廟果真跟坦兒珠有關?
陸子謙卻又道:“知曉此事後,李伯雲索又贈了些銀兩給那名北元人,託他畫些託託木兒山的地貌給他,沒料到的是,此人極重諾,一年後,不但再次隨商隊前來我朝易,同時還將一幅託託木兒山的詳細地形圖予了李伯雲。
“李伯雲喜出外,比對了手中那塊坦兒珠上雕刻的痕跡,越發肯定上頭所畫的是座山,至於是不是就是託託木兒山,因他手中只有殘餘的坦兒珠,暫且無法下定論。
“只是,他越發覺得五塊坦兒珠若拼湊在一起,很有可能是一把開啓某大門的鑰匙,而那座時常神消失的古廟,沒準藏有北元什麼罕寶,只要找到託託木兒山,加上有坦兒珠做匙,不難找到那座古廟。
“他認爲,如果當年鎮教教主所言爲真,啓坦兒珠時需滴落藥引的心頭到坦兒珠之上,方能讓五塊坦兒珠上頭的痕跡顯形,那麼在他看來,這所謂用心頭顯出來的東西,也許恰好便是進那座古廟的路線圖。
平煜怒極反笑,什麼東西非得用心頭方能顯形?無稽之談!
“如此一邊揣坦兒珠的,一邊暗中找尋右護法,不知不覺間,李伯雲在京中蹉跎了三年,原本僵凍的力逐漸有了化開奔涌之勢,在此期間,西平侯府始終未有不妥。他心知鎮教之人均擅長易容,右護法更是個中翹楚,既到了京中,說不定早已改易容貌、扮作他人,可惜茫茫人海,他就算有心找出右護法,一時也難有頭緒。”
平煜聽了此話,心底那份含不詳的預再起涌起,死死盯著陸子謙,臉變得極爲難看。
他清楚地知道,右護法二十年前便已潛永安侯府,五年前,更害死真正的鄧安宜,取代鄧安宜爲了永安侯府的二公子。
倘若這位假扮鄧安宜的右護法認定祖父手中有塊坦兒珠,在找尋藥引的同時,難保不會將主意打到西平侯府頭上。
巧的是,恰是在五年前,平家突遭大難……
他心底突然變得一片冰涼。
……五年前那一場覆頂之災,始作俑者難道另有他人?
“
作者有話要說:這是5月2日的更新~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904 章

田園錦色:空間娘子種田忙
她空間在手,醫術也有,種田養娃,教夫有方。他抬手能打,拿筆能寫,文武全才,寵妻無度!他們雙胎萌娃,一文一武,天賦異稟,最會與父爭寵!“孃親,爹爹在外邊闖禍了!”大寶大聲的喊道。“闖了什麼禍?”“孃親,爹爹在外邊招惹的美女找回家了……”二寶喊道。“什麼?該死的……”……“娘子,我不認識她……啊……”誰家兒子在外麵幫爹找小三,還回來告狀坑爹。他家就兩個!
266.7萬字8.18 93047 -
完結52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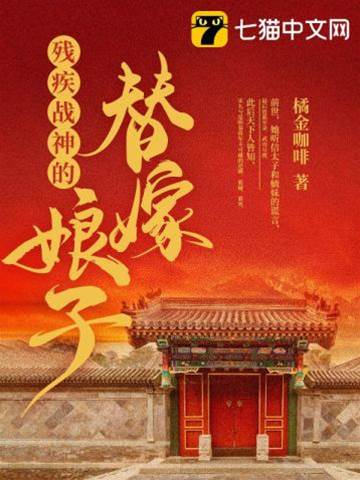
殘疾戰神的替嫁娘子
【重生+男強女強+瘋批+打臉】前世,她聽信太子和嫡妹的謊言,連累至親慘死,最后自己武功盡廢,被一杯毒酒送走。重生后她答應替嫁給命不久矣的戰神,對所謂的侯府沒有絲毫親情。嘲笑她、欺辱她的人,她照打不誤,絕不手軟。傳言戰神將軍殺孽太重,活不過一…
97.6萬字8.18 35390 -
完結530 章

撿了五個哥哥後,京城無人敢惹
流浪十五年,薑笙給自己撿了五個哥哥。 為了他們,小薑笙上刀山下火海,拚了命賺錢。 哥哥們也沒辜負她,為妹妹付出一切。 直到,將軍府發現嫡女被掉包,匆匆忙忙找來。 可也沒好好待她。 所有人譏她粗野,笑她無知,鄙她粗獷。 卻無人知道,新科狀元郎是她哥哥,新貴皇商是她哥哥,獲勝歸來的小將軍是她哥哥,聖手神醫是她哥哥,那一位……也是她哥哥。 假千金再厲害,有五個哥哥撐腰嗎? 不虐,男主未定,無固定cp,任憑大家想象 ???
101.3萬字8 193896 -
完結302 章
悍妃從商記
當再次醒來,看到兒子,她心情激動,卻不想卻深陷在一個帝王陰謀當中,且看花想容如何用自己的商業頭腦,打造一片,古代的驚天商業帝國……
77萬字8 1105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