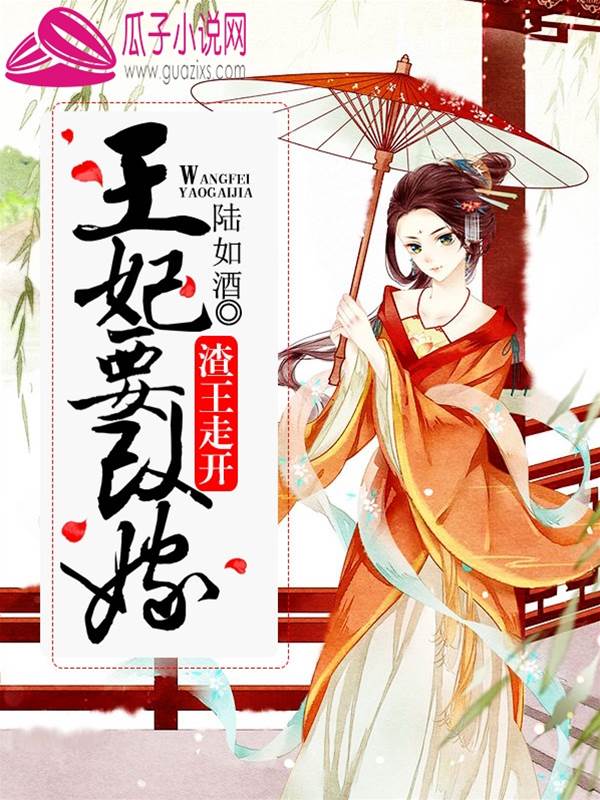《嬌娘醫經》 第27章 不說
秀王爲親王,其子嗣只能承襲國公。
晉安郡王乃皇帝特封,雖然同爲兄弟姐妹,其份高於等人。
晉安郡王疾行幾步,在正中跪坐,先向其上王妃施禮,再向兄弟姐妹還禮。
“好了,一家人,不要外見了。”秀王妃這才說道,手。
屋子們這才紛紛坐好。
“琮郎,聽聞你昨夜又在你父王靈堂枯坐一夜。”秀王妃說道,看著年郎,眼中含淚,“你莫要再如此,你長途奔襲而來,又哭靈三日,熬壞了子,如何向皇上代。”
“父母生養恩,兒不能盡孝與前,心著實難。”晉安郡王俯說道,聲音沙啞。
秀王妃擡手拭淚。
“你快起來吧,這些話就不要再說了。”說道。
那邊一個兄弟讓開一座,晉安郡王施禮後歸坐。
室安靜肅然。
“你父王不在了,大家的功課也不能丟。”秀王妃說道。
子們齊聲應聲是。
秀王妃又說些話,無非是日常瑣事代。
正說話,門外又傳來聲音。
“母親。”
伴著聲音,一陣風一般捲進一個年郎,亦是孝裝扮,年齡十三四歲,面容與晉安郡王肖像。
看到他進來,座上的秀王妃頓時含笑,出手。
那年郎並未施禮,而是徑直走到王妃前坐下。
“璜郎,又去哪裡了?這麼晚纔回來?”秀王妃手著他的肩,毫不掩飾慈問道。
“母親,我去庫房,找出父王贈與我的那副字畫。”年郎說道,面帶黯然,“此前我懶,父王以書畫警示與我,我故意藏起來了,此時父王不在了,我…”
他說到此,眼發紅,哽咽不語。
Advertisement
秀王妃眼淚早就下來了。
“好孩子,你父王知道你這個心思,你莫要難過了。”忙說道。
年郎點點頭,這纔看向屋中,對著晉安郡王出笑容。
“哥哥。”他說道,起施禮。
晉安郡王含笑還禮。
又說笑一時,晉安郡王起告退。
“你去吧,早些歇息。”秀王妃說道,說罷又補充一句,“在家不要拘謹。”
晉安郡王低頭道謝,又與兄弟姐妹們辭別,這才起出去了。
屋門拉上,隔絕室的視線,但卻更熱鬧的說笑傳出來。
“..母親,你也要多休息…”
“…哥哥,你可見昨日誰人拿走了我的玉杖…”
兄弟姐妹之間談切切,一掃適才沉悶拘謹。
晉安郡王形背對正室,腳步停了一刻未。
“郡王?”廊下僕婦低聲問道。
晉王郡王轉過頭,出含笑面容,再次衝室低頭施禮,轉大步而去。
他一路大步而行,昂首闊步,等在王妃院外的侍從疾步才能跟上。
一直走一直走,似乎不知道走到哪裡去,卻又毫沒有畏懼的走下去。
後的侍從並不敢出聲,噤聲相隨,直到晉安郡王自己先停下來。
“呃。”他著四周一刻,“我住的地方,在哪裡?”
說罷自己又是展一笑,出細白牙,與路旁白燈相映襯。
“我走的時候太小了,家裡雖然都沒變,可是我都不記得了。”他笑道。
侍從忙也含笑應是,一面忙引路。
一衆人調轉頭向一個方向而去。
夜深深,秀王府變得安靜,白刺刺的燈籠如同星辰點點,莫明的帶上了幾分森寒。
一聲詭異的聲從秀王府一角傳來,似乎夜梟鳴,又似人聲哭號,但一轉耳便逝,並沒有引起人的注意。
Advertisement
一個侍從擡腳踹了一下,地上的人翻個滾。
室燈如豆,影影綽綽。
“真夠的,郡王,還是不說。”他轉低聲說道。
晉安郡王從牆邊的黑影走出來,依舊穿著那白孝,只是手中多了一塊白錦帕,此時正掩在邊。
“倒是條忠烈漢子。”他慢慢說道,拿開手帕,面上帶著慣有的燦爛笑意,看著地上不知死活的人。
那侍從擡腳踢了一下地上的人,人滾一下,並沒醒來。
晉安郡王看著地上的人,昏昏的燈讓他的臉變得忽明忽暗。
“其實,你說與不說,又有什麼分別,我不需要知道誰要害我,我只需要知道,有人要害死我便是了。”他慢慢說道,說罷擺擺手,“不用問他了,你們隨便玩吧,怎麼也得全他的忠義纔是。”
侍從笑著應聲是。
立刻又有兩三走出來,兩腳踢起那人又翻個轉,如豆燈下,照到那人的雙,其上白骨森森,掛著些許皮,看樣子竟是生生被刮下來的。
這一翻踢打,人竟然醒過來,張口嘶喊,早有一個侍從手掐住,同時亮出手中寒。
“廖爺,你放心吧,郡王說,不用你答了。”侍從低笑道。
那人似乎知道什麼,力掙扎,看著面前白年郎,眼中滿是恐懼。
但還是晚了一步,那侍從一刀割下了他的舌頭。
鮮濺了一地,晉安郡王后退一步,用手帕輕輕揮了揮,似乎要驅散這腥氣。
廖管事暈死在地上。
晉安郡王看了一眼,轉出去了。
冬夜的風呼嘯而過,吹得廊下燈籠刷刷。
年郎看了眼夜空,一彎月斜掛,燈晃晃中,照著如玉般的臉上並無半點笑容,他就那樣默然看了一刻,轉沿著廊下慢行而去,白刺刺的燈下,白亮亮的影顯得格外的修長以及寂寥。
Advertisement
天大亮的時候,陳紹已經出了宮門到了皇城腳下。
一路上散朝的浩浩的文武員紛紛避讓。
這是休沐近兩個月的吏部相公重新朝的第一天,前後左右,無數目相隨,這其中有高興的自然也有嫉恨的。
就在方纔,月朝會散後,代政的大皇子親自住陳紹,說皇帝要見他。
這說明什麼,說明陳紹在皇帝眼中還是最可以倚重的人,本來想要取代他的機會只有其父喪丁憂,但如今,這個機會也沒了。
明明連太醫都束手無策的病,竟然真的治好了。
這個陳紹實在是太好運氣了。
對於這些目,陳紹沒有在意,他心裡還想著方纔面聖的事。
屏退了大皇子,皇帝與他單獨談論朝政,君臣二人相談甚歡,一來可見皇帝雖然說病了但神很好,二來也說明皇帝對他的倚重。
他年名,所幸沒有沉淪,進士及第,在皇帝有意的栽培下歷練,就在終於要委以重任的死後,趕上了母親病故,雖然可以奪,但爲了他的名聲,皇帝並沒有如此做,而是讓他丁憂三年,沒想到再次委以重任的時候,他的父親又….
萬幸,萬幸。
看得出皇帝也鬆了口氣,要不然也不會開那樣的玩笑。
“聽聞全城趕盡雀兒,只求陳家方。”皇帝笑道,“記得送來讓朕也嚐嚐你這陳家好黃雀。”
陳紹不由笑了笑。
自己靠著文名在朝野中聞名,沒想到又靠著吃食在京中百姓中聞名。
想來用不了多久,他陳紹會在百姓中有個陳黃雀的渾名了吧?
陳神,變陳黃雀,一下子春白雪到下里人,度也太大了。
怎麼突然就這樣了?
Advertisement
自從那個子進門,老父的病好了,而且,這個黃雀最初還是要吃的,要不然廚子也不會做出這個來。
這村俗上不得檯面的小東西,竟然也能吃的如此味。
果然大俗便是大雅。
這個子,真是古怪又有趣。
陳紹進了家門,換了常服,立刻就往父親院子走來,一進院門就看到大開的屋門裡對坐的老。
雖然瘦弱但神矍鑠斜倚盤膝而坐的白髮老者,素袍大袖黑髮端正跽坐的,隔著棋盤相對,以及棋盤旁鮮紅袍手拄頭晃來晃去的。
陳紹一瞬間停下腳步,似乎不遠打破這初冬對弈圖。
“娘子,不會下棋?”陳老太爺問道。
程娘已經看著棋盤好一刻了。
“想不起來。”說道。
想不起來?是會?還是不會?
陳老太爺一時有些不解。
“我會玩雙陸,爺爺,姐姐我們一起玩雙陸。”丹娘說道,打斷了二人之間的談話。
老者執黑子落,片刻之後,又執白子,原來是一個人自娛自樂。
“父親。”對著門口的的丹娘一眼看到父親,高興的喊起來。
陳紹進門跪坐施禮,問候了父親,又對程娘表示謝。
程娘還禮。
“雖然好了很多,但目前,還是不要太多走路。”對陳太老爺說道,“速則不達,如果此時再犯病,再多的錢,我也沒辦法了。”
陳太老爺哈哈笑了,手拍著,實在是能走路的太大了。
“再施針五日,就可以,單靠吃藥恢復了。”程娘說道。
父子二人大喜,一是終於不用再那種痛楚了,二也是說明,痊癒的日子越來越近了。
“真是太謝謝娘子了。”陳紹肅容再次道謝。
由他們父子說話,程娘便起告辭了,丹娘自然也跟上。
“丹娘,莫要吵到娘子。”陳紹忙囑咐道。
丹娘高高興興的牽著的袖走出來。
天已經冷了很多。
“三五日後,就會下雪了。”程娘說道,擡頭看看天。
“真的嗎?太好了,那就可以去山上賞雪了。”丹娘高興的說道。
走了沒多遠,迎面有子的說笑聲傳來,然後便看到四五個花團錦簇的子們走過來,見到程娘和陳丹娘,都停下腳。
明日恢復雙更,咳,其實也就多一千字而已。
另多謝臺灣站書友,金讃票已經破百了,謝謝謝謝。rs
猜你喜歡
-
完結336 章

狂妃來襲:丑顏王爺我要了
殺手之王穿越而來,怎可繼續受盡屈辱!皇帝賜婚又怎樣,生父算計姨娘庶妹心狠又怎樣?淪為丑顏王爺未婚妻,她嗤笑:“夫君如此美如天仙,不知世人是被豬油蒙了眼嗎?”“女人,嫁于我之后,你還以為有能力逃離我嗎?”…
89.5萬字8 120883 -
完結905 章

空間娘子要馭夫
二十一世紀神醫門后人穿越到一個架空的年代。剛來第一天被浸豬籠……沒關系,她裝神弄鬼嚇死他們……又被打暈喂狼?沒關系,她拉下一個倒霉蛋……只是,這個倒霉蛋貌似很有性格,白天奴役她,晚上壓榨她……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五年翻身得解釋。雙寶萌娃出世…
127.8萬字8 22655 -
連載52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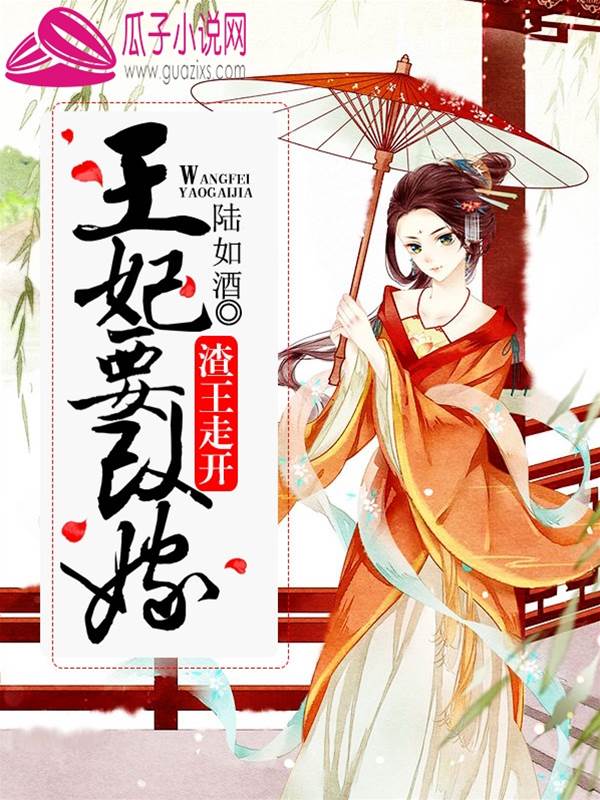
渣王走開:王妃要改嫁蘇妙妗季承翊
蘇妙,世界著名女總裁,好不容易擠出時間度個假,卻遭遇遊輪失事,一朝清醒成為了睿王府不受寵的傻王妃,頭破血流昏倒在地都沒有人管。世人皆知,相府嫡長女蘇妙妗,懦弱狹隘,除了一張臉,簡直是個毫無實處的廢物!蘇妙妗笑了:老娘天下最美!我有顏值我人性!“王妃,王爺今晚又宿在側妃那裏了!”“哦。”某人頭也不抬,清點著自己的小金庫。“王妃,您的庶妹聲稱懷了王爺的骨肉!”“知道了。”某人吹了吹新做的指甲,麵不改色。“王妃,王爺今晚宣您,已經往這邊過來啦!”“什麼!”某人大驚失色:“快,為我梳妝打扮,畫的越醜越好……”某王爺:……
99.7萬字8 12789 -
完結163 章

嫁三叔
顧長鈞發現,最近自家門口總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少年徘徊不去。一開始他以爲是政敵派來的細作。 後來,向來與他不對付的羅大將軍和昌平侯世子前後腳上門,給他作揖磕頭自稱“晚輩”,顧長鈞才恍然大悟。 原來後院住着的那個小姑娘,已經到了說親的年紀。 顧長鈞臉色黑沉,叫人喊了周鶯進來,想告誡她要安分守己別惹上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卻在見到周鶯那瞬結巴了一下。 怎麼沒人告訴他,那個小哭包什麼時候出落得這般沉魚落雁了? 周鶯自幼失怙,被顧家收養後,纔算有個避風港。她使勁學習女紅廚藝,想討得顧家上下歡心,可不知爲何,那個便宜三叔總對她不假辭色。 直到有一天,三叔突然通知她:“收拾收拾,該成親了。” 周鶯愕然。 同時,她又聽說,三叔要娶三嬸了?不知是哪個倒黴蛋,要嫁給三叔那樣凶神惡煞的人。 後來,周鶯哭着發現,那個倒黴蛋就是她自己。 單純膽小小白兔女主vs陰晴不定蛇精病男主
25.4萬字8.18 1652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