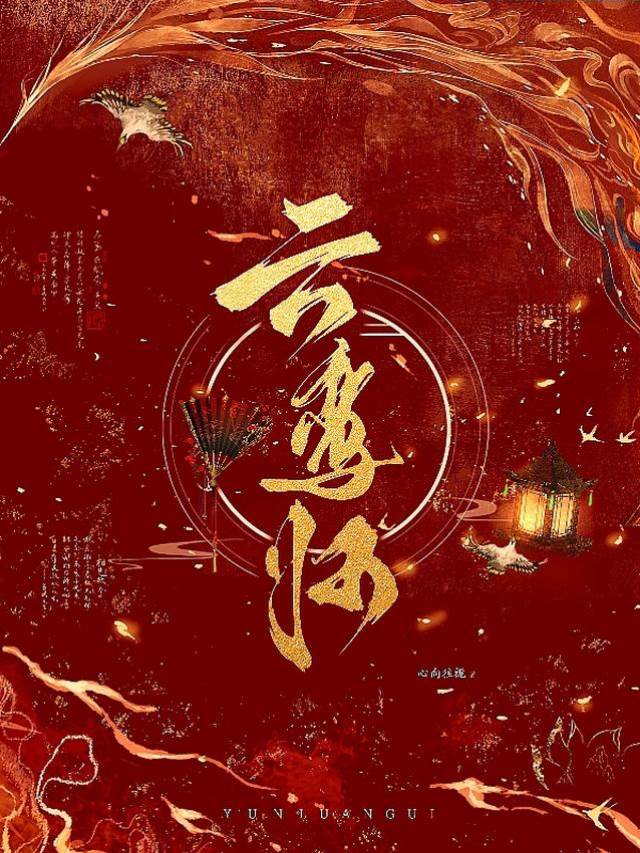《扶搖皇后》 風起太淵 第五章 人在月中
一彎鐵青的月,鑲嵌在臧藍的天幕上,月森冷,照得山林一片幽翠。
風從高高低低的樹梢掠過,樹葉的聲音呼嘯若,不知道從哪座遙遠的山頭傳來淒厲的狼號,帶著令山林震的肅殺隼利氣息,穿越浩瀚無窮星空,穿越茫茫大行山脈,穿山裡重鐐在的人耳中。
山暗溼,遍佈青苔,深且狹長,風從口過,便響起幽幽若鬼哭的嘶吼,深約有點白閃亮,仔細看去,卻是肢零落的白骨。
孟扶搖蜷在溼的地面上,衫襤褸,遍鱗傷。
被關在這個玄元劍派死牢裡已經快七天。
那日,力戰後,林玄元竟然不顧份散米藥迷暈,隨即驟下殺手,一掌將擊飛,並當衆怒斥“學本門珍藏武藝”,衆弟子頓時“恍然大悟”,對“學絕技”的孟扶搖好生一頓侮辱,隨即林玄元將關這死之中。
七天林玄元每天都來,問的來歷,並要出那天對戰黑年所使用的劍法。
當今天下,武力爲尊,一門絕技對於一個勢力的興盛有非同凡響的重要意義,林玄元眼高妙,早已看出那天這個擅長僞裝的弟子所使的劍法雖因功力不足未臻完,本卻是絕學,所以,他勢在必得。
Advertisement
孟扶搖卻只是咬牙沉默,知道這條老狗十分狡猾,幾句言語,自己的劍法便已經了他的“門絕技”,將來玄元劍派多了一種絕世劍法,也就了順理章之事,而自己這個出劍法的“藝者”,最後的下場,定然是被滅口。
孟扶搖不想死在這裡,還有很多重要的事要做。
可是當一個人重傷,又時時被嚴刑拷問,再加上沒有任何食,要如何生存下去?
孟扶搖息著,過口用來封鎖的石頭陣,看向遠的月,那月在泛起的眼底,看來越發模糊妖異,遙遠而不可。
那自由的月,灑遍五洲大地的月,照上那老狗安眠的枕前,卻照不上沉溺於黑暗中七天七夜的的。
角浮現一淺淡的苦笑,孟扶搖閉上眼睛,著自己消散大半的真氣,自己的“破九霄”功法,本已練到第三層頂峰,今日一劫,功力倒退大半,一年多來的苦修,全白費了。
“破九霄”據死老道士說是震古爍今驚世駭俗的絕頂功法,越往上越難練,練到第九層可謂獨步天下,孟扶搖對此嗤之以鼻,認爲八死老道士是在吹牛,只是這功法難練卻是真的,練了十年,纔到第三層,就這速度,死老道士已經大讚奇才,如今生生倒退一層,孟扶搖真真大恨。
Advertisement
夜更沉,一約的水聲,漸漸響在安靜的山。
掙扎著爬起,孟扶搖一點點蹭著地面挪過去,鐵的鐐銬撞擊著嶙峋的地面發出嗆啷的聲響,好半天才挪到山壁邊。
重重的對壁上一靠,用盡力氣的孟扶搖不顧山壁髒溼,將臉頰的上正在緩慢滲水的山壁,一滴滴的等那救命的水源。
這七天,就靠這每天半夜會準時出現的水源,活了下來。
喝了幾口水,了口氣,孟扶搖了臉,發現自己臉上的假傷疤都已經被水衝去,不過也沒關係,反正這中一時也沒人來。
喝了水,神好了些,孟扶搖倚在山壁上,無意中向外一看,突然眼神一凝。
前方,一座突出的孤崖,如一刃被天神劈裂的劍鋒,斜斜曳出在山之外,那淡銀的月,正正掛在那絕崖之上,圓而亮,看上去像是被陡峭的絕崖之尖勾住一般。
月森涼而潤,山巔明月裡有人正在作飛天劍舞。
那人袍寬大,被山風吹得獵獵飛舞,於峰巔之高飄的薄雲淡霧間若若現若在九天,舉手投足飄然舉瀟灑靈;長劍點裁雲鏤月風華迤邐;明明只是一個遙遠的影子,起伏轉折之間,卻生出林下之士的散逸風度,和靈玉骨的神仙之姿。
Advertisement
瑤臺之上墜落明珠,蓬萊之境盪舟欸乃,那諸般種種景緻,都是極好的,卻不及此刻那月中舞劍之影,迅捷與優雅同在,剛勁與曼妙共存。
星河浩淼無極,皓月煙籠寒沙,淺黑的劍舞之影鍍上玉白的月,鮮明如畫,而斯人一劍在手,不謝風流。
不知不覺間,孟扶搖已經看癡了去。
以至於口突然覆上一層斜長的黑影,暗傳來有人悄然走近的細微聲響,一時竟也沒發覺。
==========
嗯……親滴們……男主出來鳥……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192 章

六宮鳳華
狠辣無情的謝貴妃,熬死所有仇人,在八十歲時壽終正寢含笑九泉。不料一睜眼,竟回到了純真善良的十歲稚齡。仇人再一次出現在眼前……算了,還是讓他們再死一回吧!
206.8萬字8 131377 -
完結824 章

凰權弈:戰神王妃有點毒
星際時代的女武神鳳緋然,一朝被人暗算身亡,無意間綁定鹹魚翻身系統竟然魂穿到古代,原主還是被人欺辱的嫡出大小姐,看她鳳緋然如何逆天改命、獨步天下。
141.3萬字8 15203 -
完結935 章

禁欲皇叔心尖寵
【打臉暴爽】【雙強雙潔】天戰醫局的總司,穿越成大燕王朝的孤女落錦書,一來就背負謀殺蜀王妃的嫌疑,被滿城追捕。要證明清白還不簡單?那就把只剩一口氣的受害人蜀王妃救回來,殊不知殺人嫌疑是洗 清了,卻遭蜀王與白蓮花玩命謀害。好吧,那就放馬過來吧,她殺瘋了。手撕悔婚渣男,再毀絕世大白蓮,還順勢救了重傷的皇叔蕭王殿下。皇叔權傾朝野,驚才風逸,頂著大燕第一美男子的稱號,竟還是單身的鑽王五?那正好了,她有才,他有貌,他們女才郎貌,天作之合。權貴們:京城裏愛慕蕭王殿下的高門貴女不知凡幾,怎會選了那刁橫兇惡的孤女?百姓:蕭王妃多好的人啊,能文能武能醫能罵,蕭王殿下得此悍妻,乃是前生修來的福氣。蕭王殿下眉目溫潤:少淵何幸,娶得錦書這般良善專一的女子為妻。錦書眼珠微轉:弱水三千,我只取一二三四五瓢看看,我發誓只看看。
173.7萬字8.18 18574 -
完結28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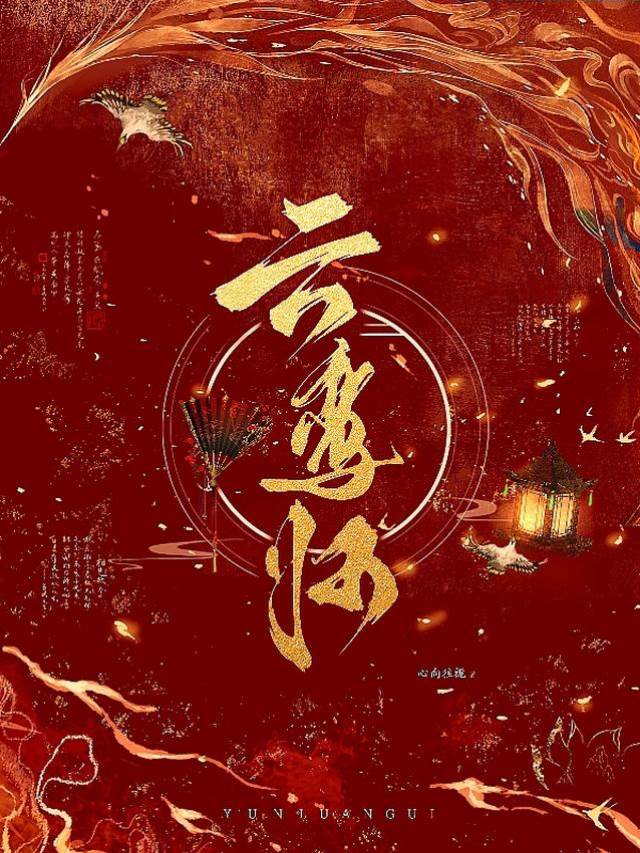
雲鸞歸
【黑蓮花美人郡主&陰鷙狠厲攝政王】[雙強+甜撩+雙潔+虐渣]知弦是南詔國三皇子身邊最鋒利的刀刃,為他除盡奪嫡路上的絆腳石,卻在他被立太子的那日,命喪黃泉。“知弦,要怪就怪你知道的太多了。”軒轅珩擦了擦匕首上的鮮血,漫不經心地冷笑著。——天公作美,她竟重生為北堯國清儀郡主薑雲曦,身份尊貴,才貌雙絕,更有父母兄長無微不至的關愛。隻是,她雖武功還在,但是外人看來卻隻是一個病弱美人,要想複仇,必須找一個位高權重的幫手。中秋盛宴,薑雲曦美眸輕抬,那位手段狠厲的攝政王殿下手握虎符,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倒是不錯的人選。不近女色,陰鷙暴戾又如何?美人計一用,他照樣上鉤了。——某夜,傳言中清心寡欲的攝政王殿下悄然闖入薑雲曦閨閣,扣著她的腰肢將人抵在床間,溫熱的呼吸鋪灑開來。“你很怕我?”“是殿下太兇了。”薑雲曦醞釀好淚水,聲音嬌得緊。“哪兒兇了,嗯?”蕭瑾熠咬牙切齒地開口。他明明對她溫柔得要死!
42.5萬字8 2182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