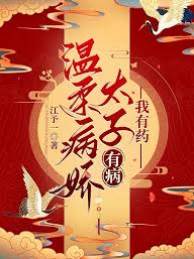《花開錦繡》 第18章 離開
日頭漸漸偏西,趙九爺走了進來。
他穿了件洗褪了的靚藍短褐,袖子挽到了肘上,腰間扎了布帶,利落中著幾分幹練:“你收拾好了沒有?我們要走了!”
傅庭筠一下午都在糾結這件事,聞言臉上出幾分躊躇。
趙九爺抿著,半晌才道:“這兩件事並不衝突――你先到渭南住下,令尊、令堂知道你還活著,必定會來找你,到時候有什麼事大可當面問令尊令堂,以後怎麼辦,也能有個商量的人。再者你還虛,不宜餐風宿,有你舅舅、舅母照顧,也可快些好起來。”
最要的是,趙九爺和萍水相逢,他不僅救了的命,而且在他自己的環境都很窘迫的時候還給了這麼多的幫助,已經是仁至義盡,不能再拖累他了。
傅庭筠想著,打起神來點了點頭,拿起枕邊的包袱:“那我們走吧!”
趙九爺站著沒,表有些怪異地瞥了一眼:“你還是換打扮吧!”
傅庭筠很是意外,低頭打量自己的衫。
月白的細布棉衫,靚藍素面十六幅馬面,扎著了條靚藍的汗巾,通沒有一件首飾,乾乾淨淨,整整齊齊,沒什麼不妥啊!
不解地著他。
如玉,青如墨,的紅豔滴如夏盛的石榴花,嫵妍麗得如同那五月明的好風,偏生一雙杏目清澈如一泓山澗泉水般澄淨,毫沒有覺到自己的麗般,豔中就帶了三分清雅,更是人心魄。
趙九爺在心裡歎了口氣,道:“你先找塊帕子把頭包了,再換深點的裳。”又看見提包袱的手,白皙細膩如羊脂玉,“用汗巾把手也包了!”
Advertisement
傅庭筠走親訪友的時候曾隔著馬車的碧紗窗見過那些墮民,他們都穿著深的裳,包著頭,穿著草鞋或赤著腳,頭髮、臉上都是灰,髒兮兮的。
“你是讓我扮做墮民嗎?”猶豫道,“府對他們一向不客氣……”
這樣一來,他們被搜查的機會就增加了很多。
“現在外面到是流民,安化、合水、隴西、安定都引起了嘩變,那些衙役哪還敢搜查!”趙九爺耐心地道,“越是穿得鮮,就越有可能被搶。一旦誰被搶,那些慌了的人就會聞風而,群起而攻之。雙手難敵四拳,我到時候未必能護得住你。你這樣子,太打眼了!”
傅庭筠面頰微紅。
真是百無一用,連趕個路都會連累他。
忙點頭。
趙九爺避了出去。
傅庭筠照著吩咐重新換了裳,又仔細地打量了一番,覺得沒有什麼破綻,喊了聲“九爺”。
趙九爺走了進來,後還跟著和他一樣打扮的阿森。
看見傅庭筠,阿森的眼睛有些發直。
深靚的布裳越發映襯著的臉瑩瑩如玉了。
趙九爺頗有些無奈,輕輕地咳了一聲,囑咐傅庭筠:“你到時候別東張西,盡量低著頭,有誰和你說話,你一概不用理會,自有我應付,最好別讓人看到你的臉。”
阿森聽到那聲咳嗽如夢驚醒,忙將傅庭筠用過的涼簟、瓷枕,喝水杯子,吃飯的筷子都收起來出了門。
傅庭筠心裡卻有些苦。
他是怕被人認出來吧?
沒想到傅庭筠也有藏頭藏尾的時候,可見人說話行事都不要太滿。
低下頭,應了聲“好”,
聲音悶悶的,緒很低落。 趙九爺不知是為哪般,也不想知道――他隻要安全地把這子送到渭南舅舅家,就算是完所托了。他也會離開陝西。從此天各一方,再無相見之日。
Advertisement
他轉出了門。
傅庭筠收斂緒跟了出去。
破廟外有片樹林。和碧雲庵的鬱鬱蔥蔥不同,這裡的樹木像被曬幹了似的垂著枝條,掛滿了灰蒙蒙的塵土,顯得垂頭喪氣的。
阿森正把用過的件往停在破廟前的一輛獨小推車上裝。
滿天的晚霞映紅了他們的臉龐,也染紅了樹林,平添幾分寂寥。
“走吧!”趙九爺聲音顯得有些繃悵然,“此非久留之地!等他們吃完了糠麩野菜,就該吃草樹皮了。”
傅庭筠駭然:“不,不會吧?”
“怎麼不會?”阿森走了過來,“我還看見人吃土呢!”他已經把東西都捆好了,“爺,我們可以走了吧?”他嘀咕道,“這麼一大片林子,隻有我們三個人,我覺得心裡的――要是那幫流民找過來可就糟了。”
趙九爺沒有說話,走過去把獨小推車上的車袢掛在了脖子上,對傅庭筠道:“你坐上來吧!”
“啊!”傅庭筠瞪大了眼睛。
這種獨小車是鄉間常用的,隻有副車架子,全靠推車的人推前面的那個木子得力,不比馬、騾子或驢,全靠人力的。
沒有想到他會推。
“我也想給你找輛馬車,”他淡淡地道,“隻是這個時候但凡是個活都進了肚子,你就將就將就吧!”
說得好像在嫌棄似的。
“我不是這個意思!”傅庭筠忙解釋道,“我見阿森往車上裝東西,我還以為這是拉的呢!”
阿森聽提到他的名字,瞇著眼睛笑起來,指著推車:“東西都堆在右邊,左邊就是留著給你坐的。”又道,“我在車上鋪了床夾被,肯定不會硌著。”然後眼地著,一副“你快坐上去,很舒服”的模樣。
Advertisement
傅庭筠還是有些猶豫。
雖然不像六堂姐那樣珠圓玉潤,可也不像七堂姐那如柳扶風,右邊已經堆了些七八糟的什了,再加,也不知道他推不推得?這萬一要是摔下來了……想到那次被趙九爺駭得從老槐樹上摔下來子骨痛了好幾天就有些後怕。
趙九爺卻不耐的磨磨蹭蹭,斜了一眼:“難道您想一直走到渭南去?”
“不是……”話已經說到這個份上了,他又是一片好心,就算是擔心,傅庭筠也隻好著頭皮坐了上去。
“走了!”阿森興高采烈地朝前跑,率先上了樹林旁的一條土路。
趙九爺推著車跟在他後。
車子顛簸,好像隨時會被甩出去似的,車輾在地上,揚起一塵黃土,往鼻子裡直鑽。
傅庭筠很難,隻好地把包袱抱在懷裡。
趙九爺輕聲地提醒:“抓住捆什的繩子。”
傅庭筠忙“哦”了一聲,立刻抓住了繩子。
找到了依靠的地方,人也就坐穩了。
走出林子,是條驛道。
道路平整寬敞,與土路不可同日而語。
傅庭筠這才有了點坐車的覺。
打量周圍的景致。
路兩邊都是田,遠遠的,還可以看見幾座農舍和農舍高過屋頂的大樹。已是黃昏,卻沒有看見炊煙。田裡沒有莊稼,黃黃的土都裂了,旁邊的小裡看不到一水。四周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響,走在路上,讓人磣得慌。
“怎麼旱了這樣?”傅庭筠失聲,“今年豈不是沒有收?”
雖然長在閣閨,卻是做為當家主母教養的,田莊上的事也略知一二。一年沒有收,對不過是減了收益,對那些種田為生的人卻是要命的事。雖然聽說慶、鞏昌大旱,商州、同州到是流民,可日子照常的過,那些也不過是聽說,此時親眼看見,自然極為震驚。
Advertisement
趙九爺沒有做聲。
阿森卻小聲地道:“前幾天賣個人還給換三碗白面,這幾天,不要錢都沒人買了,隻好眼睜睜地看著被死……”
這是傅庭筠完全不能想像的事。
“府為什麼不開倉放糧?”傅庭筠覺得自己的聲音有些尖厲。
沒有人回答,隻有車子碾在地上的“骨碌”聲。
傅庭筠回頭向趙九爺。
他的神很沉靜,可繃的下頜卻泄了他心。
不知道為什麼,傅庭筠覺得心頭一松,心平和了不。
沒有朝廷之命,府也不敢隨便開倉放糧。
“巡大人應該奏請皇上派人來陝西督辦流民之事才是。”道,“否則出了什麼事,他也難逃其咎。”
趙九爺目視著前方推著車,好像沒有聽到的話似的。
傅庭筠等了半天等不到他的回答,有些失地轉過去。
“皇上一心想要做文治武功的千古聖君,”後卻響起他平淡得有些呆板的聲音,“自熙平二十八年對河套用兵以來,征調糧草不下千萬石,陝西又產糧之地,征調猶為頻繁。陝西巡董翰文乃前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莫英伯的門生,莫英伯與現任閣首輔沈世充有罅隙,董翰文隻得迎合帝心以保位,新糧未庫即送存糧北上。如今大旱,隻怕他想開倉放糧也無糧可放!”
這豈是一般人能知道的事,能說出來的話!
傅庭筠不道:“九爺是做什麼的?”
“我不過是個遊江湖的一介莽夫罷了!”趙九爺說著,角閃過一嘲諷的笑意,“茶館裡聽別人說些朝中大事,也跟著人雲亦雲而已!姑娘聽聽就算了,不必放在心上。”
是嗎?
傅庭筠默然。
如果有一天,別人問是誰,恐怕也隻能像他這樣回答別人吧!
突然間,覺得他離很近。
※
O(∩_∩)O~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482 章

皇後天天想和離
他是手握重兵,權傾天下,令無數女兒家朝思暮想的大晏攝政王容翎。她是生性涼薄,睚眥必報的21世紀天才醫生鳳卿,當她和他相遇一一一“憑你也配嫁給本王,痴心枉想。”“沒事離得本王遠點,”後來,他成了新帝一一“卿卿,從此後,你就是我的皇后了。”“不敢痴心枉想。”“卿卿,我們生個太子吧。”“陛下不是說讓我離你遠點嗎?”“卿卿,我帶你出宮玩,”
139.7萬字8.33 514932 -
完結250 章

愛卿,龍榻爬不得
魏無晏是皇城裏最默默無聞的九皇子,懷揣祕密如履薄冰活了十七載,一心盼着早日出宮開府,不料一朝敵寇來襲,大魏皇帝命喪敵寇馬下,而她稀裏糊塗被百官推上皇位。 魏無晏:就...挺突然的。 後來,鎮北王陶臨淵勤王救駕,順理成章成爲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攝政王。 朝中百官紛紛感嘆:奸臣把持朝政,傀儡小皇帝命不久矣! 魏無晏:好巧,朕也是這麼想的。 慶宮宴上,蜀中王獻上的舞姬欲要行刺小皇帝,攝政王眸色冰冷,拔劍出鞘,斬絕色美人於劍下。 百官:朝中局勢不穩,攝政王還要留小皇帝一命穩定朝局。 狩獵場上,野獸突襲,眼見小皇帝即將命喪獸口,攝政王展臂拉弓,一箭擊殺野獸。 百官:前線戰事不明,攝政王還要留小皇帝一命穩定軍心。 瓊林宴上,小皇帝失足落水,攝政王毫不遲疑躍入宮湖,撈起奄奄一息的小皇帝,在衆人的注視下俯身以口渡氣。 百官:誰來解釋一下? 是夜,攝政王擁着軟弱無骨的小皇帝,修長手指滑過女子白皙玉頸,伶仃鎖骨,聲音暗啞:“陛下今日一直盯着新科狀元不眨眼,可是微臣近日服侍不周?” 魏無晏:“.....” 女主小皇帝:本以爲攝政王覬覦她的龍位,沒想到佞臣無恥,居然要爬上她的龍榻! 男主攝政王:起初,不過是憐憫小皇帝身世可憐,將“他”當作一隻金絲雀養着逗趣兒,可從未踏出方寸之籠的鳥兒竟然一聲不吭飛走了。 那便親手將“他”抓回來。 嗯...只是他養的金絲雀怎麼變成了...雌的?
40.5萬字8.18 12559 -
完結23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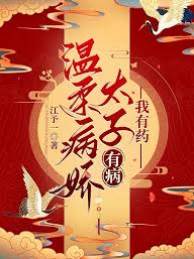
溫柔病嬌太子有病,我有藥
【古言甜寵 究極戀愛腦深情男主 雙潔初戀 歡快甜文 圓滿結局】 謝昶宸,大乾朝皇太子殿下,郎豔獨絕,十五歲在千乘戰役名揚天下,奈何他病體虛弱,動輒咳血,國師曾斷言活不過25歲。 “兒控”的帝後遍尋京中名醫,太子還是日益病重。 無人知曉,這清心寡欲的太子殿下夜夜都會夢到一名女子,直到瀕死之際,夢中倩影竟化作真實,更成了救命恩人。 帝後看著日益好起來,卻三句不離“阿寧”的兒子,無奈抹淚。 兒大不中留啊。 …… 作為大名鼎鼎的雲神醫,陸遇寧是個倒黴鬼,睡覺會塌床,走路常遇馬蜂窩砸頭。 這一切在她替師還恩救太子時有了轉機…… 她陡然發現,隻要靠近太子,她的黴運就會緩緩消弭。 “有此等好事?不信,試試看!” 這一試就栽了個大跟頭,陸遇寧掰著手指頭細數三悔。 一不該心疼男人。 二不該貪圖男色。 三不該招惹上未經情愛的病嬌戀愛腦太子。 她本來好好治著病,卻稀裏糊塗被某病嬌騙到了手。 大婚後,整天都沒能從床上爬起來的陸遇寧發現,某人表麵是個病弱的美男子,內裏卻是一頭披著羊皮的色中餓狼。 陸遇寧靠在謝昶宸的寬闊胸膛上,嘴角不禁流下了悔恨的淚水。 真是追悔莫及啊~
42.5萬字8.18 7922 -
完結212 章

將軍她又美又颯,權臣甘拜裙下
【女扮男裝將軍vs偏執權臣】人人都說將軍府那義子葛凝玉是上趕著給將軍府擦屁股的狗,殊不知她是葛家女扮男裝的嫡小姐。 一朝被皇上詔回京,等待她是父親身亡與偌大的鴻門宴。 朝堂上風波詭異,暗度陳倉,稍有不慎,便會命喪黃泉。 她謹慎再謹慎,可還是架不住有個身份低微的男人在她一旁拱火。 她快恨死那個喜歡打小報告的溫景淵,他總喜歡擺弄那些木頭小人兒,還次次都給她使絆子。 起初,溫景淵一邊操著刻刀一邊看著被五花大綁在刑架上的葛凝玉,“將軍生的這樣好,真是做人偶的好面料。” 后來,溫景淵將她圈在懷里,撥弄著她的唇,“姐姐,先前說的都不作數,姐姐若是喜歡,我來做你的人偶可好?” 葛凝玉最后才知道,昔日心狠手辣的笑面虎為了自己賭了兩次,一次賭了情,一次賭了命。 排雷:1、女主穿越人士,但沒有過多的金手指,情感線靠后 2、作者起名廢 3、架空西漢,請勿考究
39.9萬字8 6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