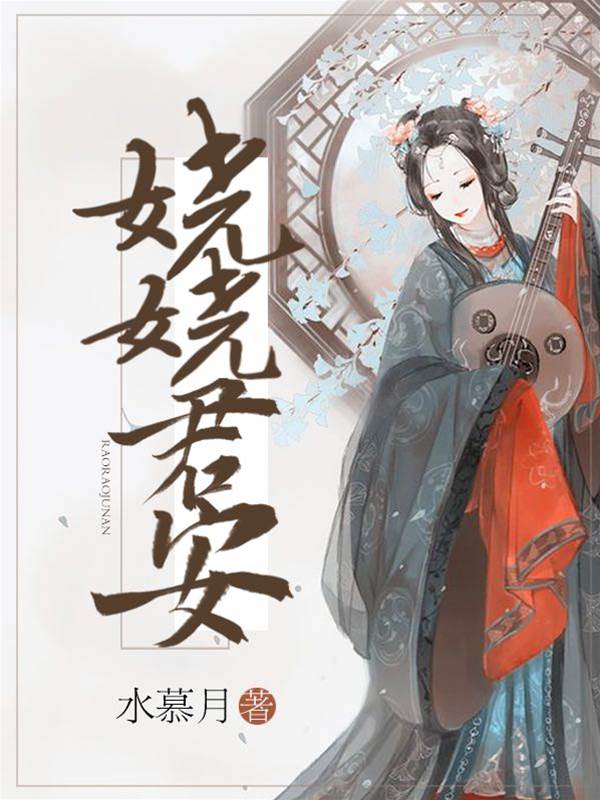《春雪欲燃》 第72章 第72章 開口 “喜……喜……”……
第72章 第72章 開口 “喜……喜……”……
“這幾日休沐, 學宮無事。”
沈荔嗓音輕,撒了一個無傷大雅的小謊,“所以, 就來看看。”
為了添幾分可信, 不讓人看出挑燈注解石經的倦怠,還擡起清麗和的臉來, 很是篤定地點了點頭。
蕭燃似乎懂了, 湊近道:“你是不是……”
沈荔對上他那雙能進心底的眼睛, 有些張地咽了咽嗓子。
“……來查崗的?”
聽完蕭燃的後半句,沈荔那顆無從安放的心便撲通一聲摔了下來, 懵怔間, 竟然鬼使神差地點了下腦袋。
反應過來, 忙搖首, 兩顆溫潤的珍珠耳鐺也隨之搖曳生:“不是, 我沒有……”
“是也沒關系,隨便查!”
蕭燃坦然一笑, 眼中染著明晃晃的得意與縱容。他手, 輕輕了微紅的臉頰,姿態親昵又帶著些許頑劣的逗弄。
下一刻,他忽而張開雙臂, 不由分說地將擁懷中。
“抱一個。”
溫熱的薄在耳尖上飛快一, 又臉蹭了蹭,笑音低沉,震得耳廓麻, “你能來,我很高興。”
沈荔猝不及防磕他懷中,呼吸都滯了一瞬。接著, 悉的澡豆清香縈繞鼻端,如同他這個人一般幹淨而蓬,不講道理地肆意將包裹其中。
不由翹起角,蝶翼般的眼睫微微垂落,擡手回擁住了年矯健的腰肢。
夢魚說,只要主邁出一步,許多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然後呢?
是否……應該再說點什麽?
正當沈荔心慌意地打磨腹稿之際,有人來了。
兩名親兵送來了熱騰騰的魚湯與油脂盈的炙羊,并兩碟清脆爽口的野菜,目不斜視地布完晡食後,又目不斜視地退下。
Advertisement
沈荔臉皮薄,忙推開蕭燃,坐直子。
“慢著。”
蕭燃喚住那兩名親兵,板著臉吩咐道,“去取一張絨毯,三床……不,四床錦被來,要幹淨的。”
沈荔道:“不必,我帶足了和綢被,讓商靈送來便是。”
“行,你的東西肯定比我的講究。”
蕭燃折回來,有條不紊地將晡食一一陳列沈荔面前,“趕了這麽久的路,了吧?這個季節的野菜最是脆,嘗嘗看。”
說罷,他複又想起什麽,舀魚湯的手遲疑起來:“我記得,你不喜歡吃魚?”
沈荔有些訝然,隨即搖首:“只是不吃有刺的魚,會卡住。”
從小就不會吐魚刺,旁人做來輕而易舉的事,于而言卻難若登天。
無論如何小心翼翼,總是會被埋伏在雪白魚中的微末小刺劃傷嚨。
因此,沈府的膳夫從不做刺多的河魚。要麽片薄如蟬翼的魚膾,淋上吊了一宿的高湯,燙出最鮮爽的口;要麽燉骨頭的濃湯,濾淨渣滓,才敢小心翼翼地嘗上幾口。
武將對飲食并不挑剔,王府的魚都是整條呈上,鮮筷。
卻沒想到,竟被蕭燃記在了心裏。
“你嚨小,的確容易卡住。”
他笑了聲,舀了半碗白無渣的魚湯。
不知想到了什麽,他忽而安靜下來,視線落在紅潤的瓣上,目漸深漸燙。
沈荔不解地回看他。
半晌,福至心靈般,腦中閃過那些被他抵在榻間,霸道到間窒息的深吻,雪腮便不可抑止地洇開薄紅。
輕咳一聲,別開了眼。
“天尚早。”
蕭燃沒由來說了這麽一句,而後低頭勾笑,專心篩查魚湯中的蔥末與小刺。
燭花炸開的嗶剝聲間或響起,如同夫妻倆無藏的心跳,灼熱而清晰。
Advertisement
商靈就在此刻進來,躡手躡腳地送上幾張簇新的錦被。
“你先吃著,我去鋪床。”
蕭燃將那碗挑的極為幹淨,雪白鮮香的魚湯放至面前,起去屏風後收拾起來。
被褥一掀,沈荔便聽到了叮叮當當的滾落聲。
什麽服、金鈎帶、銅錢,甚至還有一把寒凜冽的匕首,和兩張得起皺的河道圖紙……
沈荔撚著瓷勺的手頓在半空,著地上那堆散的什,半晌才找回聲音:“……你究竟在床上藏了多東西?”
蕭燃將那些東西拾起來,連同褥子團一團,一本正經道:“事先不知你要來,未曾收拾。武將嘛,都這樣……”
說話間,他已換上幾層新錦被,又以掌心了厚度,這才滿意地拍拍手,轉而將案上散落的兵書與信箋疊放齊整。
沈荔的目隨著他忙碌的影轉,忍不住問:“這些信,為何不寄出去?”
莫非是因不回,所以賭氣了?
蕭燃微不可察地一頓,隨即轉過來,漫不經心地笑道:“我又不會寫那些駢四儷六,花團錦簇的華麗文章。記的都是些瑣碎雜事,今日吃了什麽,路上看到了什麽,夜間又夢到了什麽……”
一提到他那個夢,沈荔便覺周的有些翻湧,又按捺不住好奇,遲疑道:“除了馬車,你還夢到了什麽?”
“馬背上。”
“……”
“樹林裏。”
“……”
“還有……”
蕭燃撐著案幾,每說一句,便朝近一分,低沉的嗓音裹挾著毫不掩飾的求,“去年春蒐時,帶你去的……那條飛瀑下。”
最後一句,幾乎是著的耳畔落下,灼熱的呼吸燙得指尖微蜷。
沈荔眼睫抖,腦中一片空白,無論如何也設想不出那是怎樣荒唐的畫面,只僵直端坐著,全然忘了反應。
Advertisement
蕭燃這才低低地笑出聲來,迫驟然消散,親了親的臉頰。
“你看,都是些不討人喜歡的大白話。既無風雅,也無趣,說不定看得人眼睛疼,還要勞你費神去燒。”
他不甚在意地說完,起要將信箋收櫃中。
下一刻,碗勺撞的脆響傳來,下裳被輕輕拽住。
蕭燃回過頭來,看到了沈荔那雙清亮麗的眼睛,比往常更添幾分水瀲滟的人之。
“你的信,我都收著,不曾燒毀。”
這樣說著,眸有些閃爍,攥著他袍角的手了,鼓足勇氣,“喜……”
“嗯?”
蕭燃沒太聽清。
“喜……喜……”
斷斷續續蹦出的字眼兒,說得沒頭沒尾。
心跳得太快了,呼吸快要停滯,全然沒留意方才急切間倒的魚湯正沿著案幾淌下,滴落在一塵不染的天水碧紗上。
蕭燃深知是最好潔淨的,遂了然道:“洗?是要洗漱嗎?”
沈荔愣住了。
“已經差人去燒水了。”
年俯收拾好碗筷,又替拭了拭擺,安道,“怕你用不慣此的水,特地讓人從山上運了山泉來,要費些時間。你等一下啊,我去安排。”
沈荔在這座簡單的青廬中,泡了個不那麽安心的澡。
怎麽會這樣呢?
浸在熱水中,渾渾噩噩地想:為何講學時能引經據典,侃侃而談,縱使講上一個時辰也游刃有餘,而今面對蕭燃,卻連那最簡單的幾個字也說不出口?
之事,一向是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一旦錯過那個天時地利人和的契機,再想要說出口,便總覺得有些突兀和輕浮。
當蕭燃理完營中事務,寬上榻時,看到的便是這樣一幕——
沈荔整個人蜷在錦被裏,背對著他,面朝牆壁,只出一小截白玉般的後頸,莫名出一悶悶的懊喪。
Advertisement
“沈荔?”
蕭燃掀開綢被,從背後擁住,滾燙的息沿著耳廓往下……
才發現已經睡著了。
借著屏風外進的昏去,的眉心微微攏著,也不知是太累了,還是在同誰置氣。
同誰置氣呢?
蕭燃從翻湧的念中回神,忽而頓不妙:莫非是那些馬背、樹林之類的渾話,惹生氣了?
……
沈荔的確太累了。
一天一夜的顛簸,使得一沾枕頭,便如沉水底,將那些紛雜懊惱的愁緒一同卷了夢鄉。
夢中正努力地同蕭燃說著什麽,瓣張合,卻怎麽也發不出聲音。
越是焦灼,間便越是。
就這般掙紮著,而後被一陣突兀的顛簸撞醒,意識尚未徹底回籠,便有難言的異自深寸寸炸開。
沈荔睜開眼,終于溢出聲來:“……蕭燃!”
他竟然趁睡著時,就這麽進來了!
“你一直在夢中我的名字,我只好……嗯,弄醒你了。”
蕭燃的聲音著耳朵響起,氣息既啞又沉,“做噩夢了?嗯?”
沈荔咬了瓣,哪裏還說得出話?
“不行……”
“沒事,我輕點。”
他輕輕扳過的臉來,細的吻碾過的眉眼、鼻尖,最終覆上的,“我在這,沈荔。”
話雖如此,但他卻是半分也沒有收斂。沈荔不得不擡手撐著牆面,以免被他頂撞上去。
漸深漸急,所有未盡之言和不安的懊悔,都在此刻化作了真實的,在彼此的呼吸間燒得滾燙。
托蕭燃的福,這一覺睡得十分香甜。
再次醒來時,已是日上三竿,外頭傳來了震天地的演武聲。
蕭燃并不在營中。
沈荔找到他時,他正神清氣爽地立在昨日那片農田旁,指揮上百名民夫通改道。
“你別過來!這裏泥水多,容易陷。”
蕭燃隔著田壟招呼,又轉大力拍了拍農的肩,低聲代了幾句什麽,這才大步走來。
沈荔擡指挑開冪籬垂紗,問道:“昨晚便見你榻上放著許多河道圖紙,這是要作甚?”
“改道洩洪,順便試一試農們新造的水車。”
蕭燃牽著沈荔的手,將引至道旁涼的樹下,就這麽頂著一斑駁的樹影,朝笑道,“此事若辦妥,則百年之,此地百姓可不旱澇之苦。”
聞言,沈荔心神微。
“許多腸轆轆的黔首,只看得到眼前的粥碗。”
若有所思道,“興建水利帶來的裨益尚需時間的考驗,你做的這些,或許還不如楊皇後施舍的一勺稀粥,更得民心。”
“那又如何?這些事,總要有人去做。”
蕭燃靠著樹幹,懶洋洋抱臂閑談,“阿姊同我商議過,要開設一座新學宮,如鴻都門學那般,不拘泥于儒、經二學,而是招攬天下律法、醫、農事、營造方面的人才。省得朝中上下,都是世家舉薦上來的門生故吏。”
沈荔偏頭看他,眼底有細碎的芒浮現。
蕭燃指去勾的掌心:“看我作甚?替你哥著急了?”
沈荔搖了搖頭,揚起淺笑:“只是沒想到,殿下除了征戰殺敵,還有如此宏圖偉願。”
“打仗也好,治水也罷,都是在其位謀其職罷了。”
蕭燃將拉來跟前,低聲問,“將來,你幫不幫我?”
沈荔擡眸,正撞進他這雙張揚深邃的眼中,打了一上午的腹稿,就這般咽回了腹中。
總覺得,在這個討論家國大事的時刻談論兒私,頗有些不合時宜……
……
“所以,你便回來了?”
學宮教司署中,崔妤不可置信地瞪大眼。
沈荔鋪紙研墨,很是認真道:“休沐假短,再不,便趕不上今日的早課了。”
崔妤扶額,似是欽佩,又似是無奈:“雪大老遠跑這一趟,豈非什麽都沒改變?”
“還是有所改變的。”
比如,蕭燃又開始給送那些字句滾燙的家書。
又比如,此刻正提筆潤墨,學著給他回信:【一切安好。勿念。】
“此事是我思慮不周,不曾想你遠道而去,時間倉促,的確很難開口。”
崔妤含笑勉勵,“我們雪能邁出第一步,于郡王來說,便已是莫大的嘉賞……對了,他何時回來?”
提及歸程,沈荔眼底也有了輕淺的笑意:“約莫再過六七日。”
“那倒是快了。”
崔妤想了想,很快有了新的主意,“既然你上回未能順利說出口,是因了風月相襯。不曾找到水到渠的契機。那此番,你便尋一曲水流觴的雅境,待月盈庭,花前柳下,再把盞言歡,將你的心意細細道來。”
沈荔聞言,眸微微一亮。
這個可行。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2229 章
帝凰之神醫棄妃
大婚當天,她在郊外醒來,在衆人的鄙夷下毅然地踏入皇城…她是無父無母任人欺凌的孤女,他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鐵血王爺.如此天差地別的兩人,卻陰差陽錯地相遇.一件錦衣,遮她一身污穢,換她一世情深.21世紀天才女軍醫將身心託付,爲鐵血王爺傾盡一切,卻不想生死關頭,他卻揮劍斬斷她的生路!
448.5萬字8.38 388648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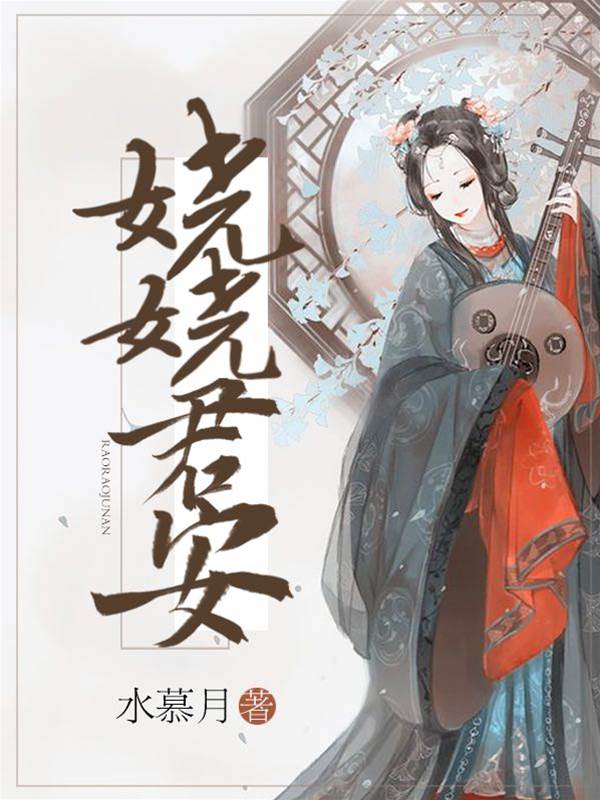
嬈嬈君安
原想著今生再無瓜葛,可那驚馬的剎那芳華間,一切又回到了起點,今生他耍了點小心機,在守護她的道路上,先插了隊,江山要,她也絕不放棄。說好的太子斷袖呢!怎麼動不動就要把自己撲倒?說好的太子殘暴呢!這整天獻溫情的又是誰?誰說東宮的鏡臺不好,那些美男子可賞心悅目了,什麼?東宮還可以在外麵開府,殿下求你了,臣妾可舍不得鏡臺了。
16.6萬字8 14823 -
完結648 章
重生后,我成了渣男他皇嬸
因道士一句“鳳凰棲梧”的預言,韓攸寧成了不該活著的人。外祖闔府被屠,父兄慘死。太子厭棄她卻將她宥于東宮后院,她眼瞎了,心死了,最終被堂妹三尺白綾了結了性命。再睜開眼,重回韶華之時。那麼前世的賬,要好好算一算了。可慢慢的,事情愈發和前世不同。爭搶鳳凰的除了幾位皇子,七皇叔也加入了進來。傳說中七皇叔澹泊寡欲,超然物外,
116.3萬字8.18 58167 -
完結242 章

教不乖,佞臣替人養妹被逼瘋
【傳統古言 廢殺帝王權極一時假太監 寄人籬下小可憐 倆人八百個心眼子】少年將軍是廝殺在外的狼,窩裏藏著隻白白軟軟的小兔妹妹,引人垂涎。將軍一朝戰死沙場,輕躁薄行的權貴們掀了兔子窩,不等嚐一口,半路被內廠總督謝龕劫了人。謝龕其人,陰鬱嗜殺,誰在他跟前都要沐浴一番他看狗一樣的眼神。小兔落入他的口,這輩子算是完……完……嗯?等等,這兔子怎麽越養越圓潤了?反倒是權貴們的小團體漸漸死的死,瘋的瘋,當初圍獵小兔的鬣狗,如今成了被捕獵的對象。祁桑伏枕而臥,摸了摸尚未顯孕的小腹。為了給兄長複仇,她忍辱負重,被謝龕這狗太監占盡了便宜,如今事得圓滿,是時候給他甩掉了。跑路一半,被謝龕騎馬不緊不慢地追上,如鬼如魅如毒蛇,纏著、絞著。“跑。”他說:“本督看著你跑,日落之前跑不過這座山頭,本督打斷你的腿!”
42.7萬字8.18 1579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