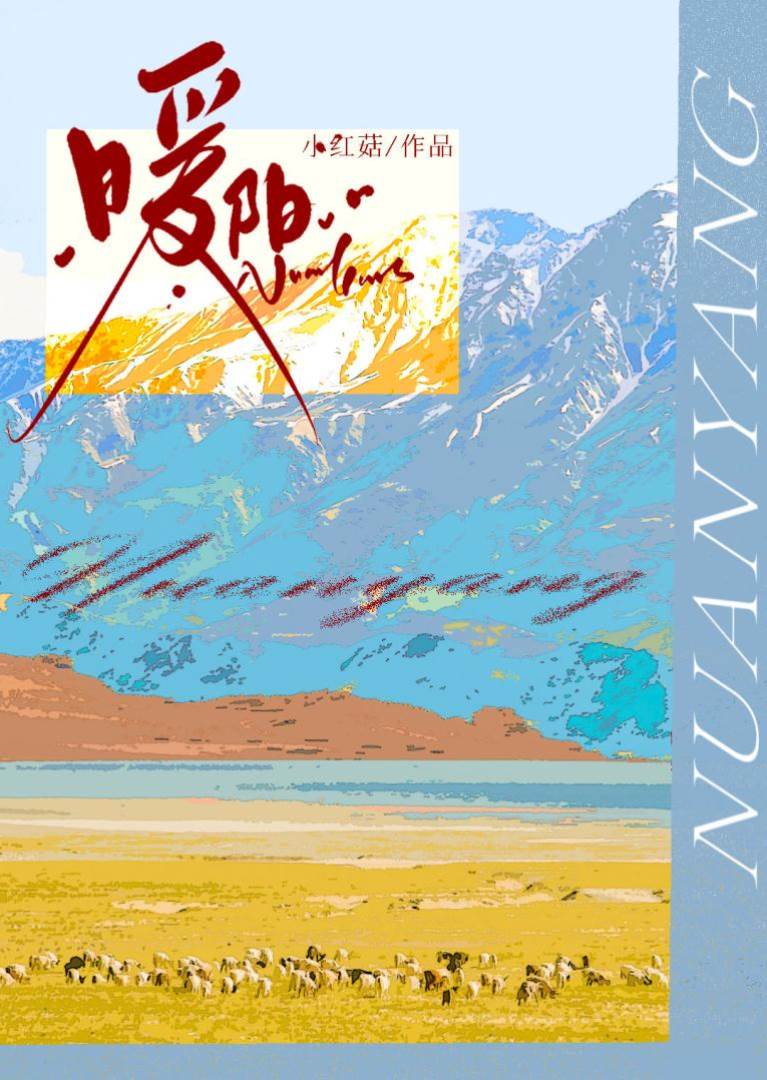《分手后,港圈大佬強制愛!》 第1卷 第194章 放她走
病房是亮的,傾斜的暖意將地面照亮,割裂在瓷板的碎漸漸爬上部,站在病床旁,不可置信的怔愣許久。
指尖掐掌心,是痛的。
他說要放走?
京初懷疑自己聽錯了,可真對上他無波無瀾的黑眸時,捕捉到他眼里曾經不會有的愫——失。
親自在他心口開了一槍,他是應該對失,再在知道真要他的命時,心也該碎裂。
心了下,閉了閉眼,“謝謝。”
得償所愿后,心好似也沒多輕松。
拖著疲憊的轉朝門口走,背后是他冷沉一聲,“站住。”
眼睫一,呼吸發,回張向他,“還有事嗎?”
鶴行止深看一眼,貪,不舍的織在一起,晦的被霧剝開,他用力到像是在道別。
“Amy以后不會再教你,但我有件禮送給你。”
他從桌上拿了份文件,遞給。
京初以為會是離婚協議書,結果是法國藝舞學院的課程恢復通知。
「京初士,貴方再次誠邀您校。」
金閃閃的校徽在指尖劃過,京初鼻尖酸,沒等慨完,男人的聲音低緩砸來,“天南地北任你闖了。”
抬起頭,鶴行止勾起一笑,“阿京,我們沒有結婚。”
怔愣,一顆淚悄然從眼尾滾落,余看見他抬起手,又放下,“證是假的,我知道你不愿意嫁給我。”
即便是放走,他也要讓走的干干凈凈。
他的聲音又啞又,也哽進嚨里。
干在倒轉,爬離腳步時,染上致的側臉,睫羽一,男人嘆息聲,“你走吧。”
腳步生了,定立許久,闔眸,任由一滴淚從下頜滾落,清脆的在地板綻開。
京初一步步離開病房,腳尖及冷瓷磚,能背后跟的一道灼熱視線,狠心,關上門。
Advertisement
隔絕開,安靜數秒。
病房猛地響起一聲破裂的巨響。
微,立馬有保鏢沖進去,旋起的一陣風將發吹晃,堪堪落回肩頭時,呢喃:“鶴行止,保重。”
病房門悄悄合攏,遮住男人猩紅不甘的眼,帶走留下的最后一愫。
京初打車去了別墅,只帶走了屬于自己的東西,摘下璀璨的婚戒放在房間的書桌上,指尖上去,那晚的余溫仿佛還在。
垂睫,拎著行李箱出門,待了半年多,箱子里的空間都裝不滿。
關上房門,隔壁書房門開了。
頓住腳,震驚的發現本該在醫院的鶴行止出現在眼前,張退后半步。
男人冷淡掃過提的行李箱,“收拾好了?”
“嗯。”
他結滾了下,讓出一條道。
與他而過,那日夜相擁的氣味就要遠離,他倏地拽住的手腕。
京初順著他青筋凸起的手背上,凝過他眉眼的苦寂,垂頭,很輕嘆息聲,“鶴行止,你又想做什麼呢?”
他眼睛紅潤,聲音苦,“你說過,喜歡我。”
“嗯。”
“那為什麼不喜歡了?”
一直一直這樣下去不好嗎。
京初低喃,“因為沒有以后了。”
他渾一震,握的指一寸寸松開的,佝僂的背影著消頹的枯寂。
他像一棵老樹,永遠丟失了土壤。
捧著他傷的一顆心,心打包好,送還回樹下,于是,他只能仰,著的背影,不疾不徐,緩慢的撤離他的世界。
他知道,留不住的。
鶴行止倚靠在墻,雙手捂住臉頰,淚從指溢出,他眼睛曾翻涌過的意被水花無熄滅,這一刻,他世界陷了混沌的黑跡。
良久,他腔抖著,仰頭笑聲,“怎麼連個擁抱都不給我啊。”
Advertisement
“阿京。”
“你要我怎麼活呢。”
輕飄飄說走就走,帶走他的一切,呼吸,氧氣,在走后,都變的虛無起來。
連房間里,的笑依稀還在,他貪的凝,淚模糊一切,記憶死命的只記住——你向我的每一個眼神。
他怎麼好過。
他怎麼保重。
他好不了了。
他快要死了。
帶走了一切。
唯獨丟掉了他。
--
京初下樓,管家心幫提行李箱,掃過紅潤的眼尾,嘆息聲,“你們這些小年輕,啊啊什麼的,最折騰人了。”
“算了,圖個無怨無悔吧。”
等車到的時候,管家拉著行李箱出來把車裝上去,擁抱下,拍拍的背,若有似無看了眼樓上主臥。
“京初,鶴先生子偏執,認死理,對你的偏激蠻橫,但他”
“只過你一個。”
“不用原諒他,但也別恨他了。”
京初垂簾,輕應聲,坐回車上時,最后一次凝這棟別墅,發現某個房間亮起燈盞,一個影藏了又藏,還是很明顯。
角輕扯,吸了下鼻子,釋然朝司機說:“我們走吧。”
安靜的車,司機聽點鄭潤澤版本唱的苦歌,磁音溢出時,順著倒影的景,記憶模糊一個點。
歌曲:《想你的夜》
原唱:關喆
“分手那天 我看著你走遠
所有承諾化了句點
獨自守在空的房間
與痛在我心里糾纏
我們的 走到了今天
是不是我太自私了一點
如果可以重來我會為你放棄一切
想你的夜 多希你能在我邊
不知道你心里還能否為我改變
想你的夜 求你讓我再你一遍
讓再回到原點”
京初眨了下眼,角莫名嘗到一抹咸,看飄進手心的雨水,關上窗。
是雨,不是淚。
Advertisement
是離別,不是再見。
飛機越過海岸城,隔絕開這座城市下起的一片雨。
到法國,已是凌晨。
重新住回家庭房,奔波幾小時,呂玉玲早睡下,京初睡不著,在房間收拾行李。
打開行李箱時,渾僵住。
箱子白外殼,里面黑底層本來空的一角,被塞進不屬于的東西。
抱著睡的小熊玩偶。
一把小而鋒利好掩藏的防匕首。
冒藥,腳傷藥,痛經藥。
恍惚記起,那次在維港雨夜,他說:
“冒藥按時吃藥,天冷不能因為漂亮就穿的,外面混混一堆,隨時帶點防的,知道嗎?”
還有,學校這邊的課表竟然和Amy老師給上的一模一樣,確保一落地,不會有跟不上課程的煩惱。
原來,他早就在試著道別。
淚已決堤,孩抱著一堆藥蹲在地上,失聲痛哭。
最不了他了,明明狠心強勢卻又像溫和的風繞在耳邊吹。
他要怎麼樣?
滾燙的灼燒了,哽咽時,就連呼吸都是痛的。
這一瞬間,也分不清心的究竟是個什麼。
大概是,又又恨吧。
和他——
“分開,兩敗俱傷。”
--
深秋,法國天氣適宜,安頓下來,撲進課程中,閑來無事出校走走,一風,淺笑莞爾。
和朋友前去打車時,背后響起一道低磁男音——
“京初”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638 章
新婚嬌妻寵上癮
(桃花香)一場陰謀算計,她成為他的沖喜新娘,原以為是要嫁給一個糟老頭,沒想到新婚之夜,糟老頭秒變高顏值帥氣大總裁,腰不酸了,氣不喘了,夜夜春宵不早朝!「老婆,我們該生二胎了……」她怒而掀桌:「騙子!大騙子!說好的守寡放浪養小白臉呢?」——前半生所有的倒黴,都是為了積攢運氣遇到你。
245.9萬字8 30971 -
完結256 章

別和我撒嬌
痞帥浪子✖️乖軟甜妹,周景肆曾在數學書裏發現一封粉色的情書。 小姑娘字跡娟秀,筆畫間靦腆青澀,情書的內容很短,沒有署名,只有一句話—— “今天見到你, 忽然很想帶你去可可西里看看海。” …… 溫紓這輩子做過兩件出格的事。 一是她年少時寫過一封情書,但沒署名。 二是暗戀周景肆六年,然後咬着牙復讀一年,考上跟他同一所大學。 她不聰明,能做的也就只有這些了。 認識溫紓的人都說她性子內斂,漂亮是漂亮,卻如同冬日山間的一捧冰雪,溫和而疏冷。 只有周景肆知道,疏冷不過是她的保護色,少女膽怯又警惕,會在霧濛濛的清晨蹲在街邊喂學校的流浪貓。 他親眼目睹溫紓陷入夢魘時的恐懼無助。 見過她酒後抓着他衣袖,杏眼溼漉,難過的彷彿失去全世界。 少女眼睫輕顫着向他訴說情意,嗓音柔軟無助,哽咽的字不成句:“我、我回頭了,可他就是很好啊……” 他不好。 周景肆鬼使神差的想,原來是她。 一朝淪陷,無可救藥。 後來,他帶她去看“可可西里”的海,爲她單膝下跪,在少女眼眶微紅的注視下輕輕吻上她的無名指。 二十二歲清晨牽着她的手,去民政局蓋下豔紅的婚章。 #經年,她一眼望到盡頭,於此終得以窺見天光
45.4萬字8 21446 -
完結1693 章

離職后我懷了前上司的孩子
作為總裁首席秘書,衛顏一直兢兢業業,任勞任怨,號稱業界楷模。 然而卻一不小心,懷了上司的孩子! 為了保住崽崽,她故意作天作地,終于讓冷血魔王把自己給踹了! 正當她馬不停蹄,帶娃跑路時,魔王回過神來,又將她逮了回去! 衛顏,怒:“我辭職了!姑奶奶不伺候了!” 冷夜霆看看她,再看看她懷里的小奶團子:“那換我來伺候姑奶奶和小姑奶奶?”
165.2萬字8.18 38138 -
完結201 章

雙時空緝兇
【01】南牧很小的時候就遇到過一個人,這個人告訴他:絕對不要和溫秒成為朋友。 日長天久,在他快要忘記這件事的時候,他遇到了一個女生,那個女生叫做:溫秒。 【02】 比天才少女溫秒斬獲國內物理學最高獎項更令人震驚的是,她像小白鼠一樣被人殺害在生物科研室,連頭顱都被切開。
38萬字8 179 -
完結8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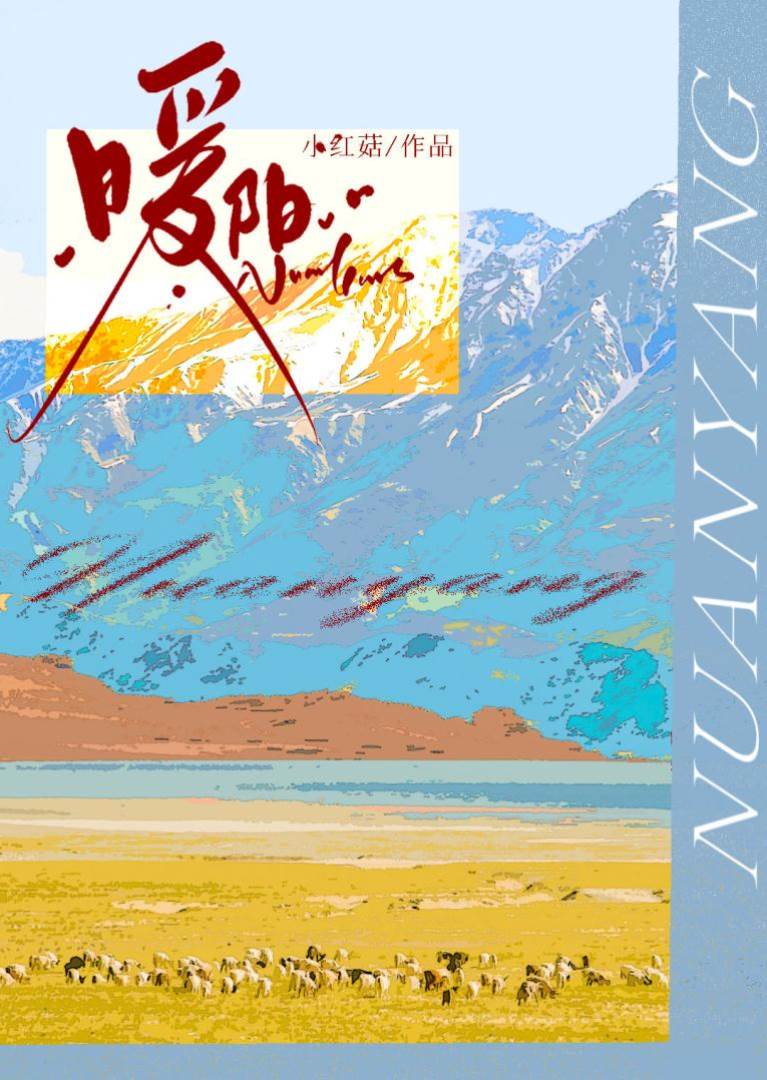
暖陽[先婚後愛]
文冉和丈夫是相親結婚,丈夫是個成熟穩重的人。 她一直以爲丈夫的感情是含蓄的,雖然他們結婚這麼久,他從來沒有說過愛,但是文冉覺得丈夫是愛她的。 他很溫柔,穩重,對她也很好,文冉覺得自己很幸福。 可是無意中發現的一本舊日記,上面是丈夫的字跡,卻讓她見識到了丈夫不一樣的個性。 原來他曾經也有個那麼喜歡的人,也曾熱情陽光。 她曾經還暗自竊喜,那麼優秀的丈夫與平凡普通的她在一起,肯定是被她吸引。 現在她卻無法肯定,也許僅僅只是因爲合適罷了。 放手可能是她最好的選擇。 *** 我的妻子好像有祕密,但是她不想讓我知道。 不知道爲什麼他有點緊張,總覺得她好像在密謀一些重要的事情,但是他卻無法探尋。 有一天 妻子只留下了一封信,說她想要出去走走,張宇桉卻慌了。 他不知道自己哪裏做得不夠好,讓她輕易地將他拋下。 張宇桉現在只想讓她快些回來,讓他能好好愛她! *** 小吳護士:你們有沒有發現這段時間張醫生不正常。 小王護士:對,他以前除了工作之外,基本不發朋友圈的,現在每隔幾天我都能看到他發的朋友圈。 小吳護士:今天他還發了自己一臉滄桑在門診部看診的照片,完全不像以前的他。 小劉護士:這你們就不知道了吧,張醫生在暗搓搓賣慘,應該是想要勾起某個人的同情。 小王護士:難道是小文姐?聽說小文姐出去旅遊了,一直還沒回來。 小劉護士:肯定是,男人總是這樣的,得到了不珍惜,失去了纔會追悔莫及。
22.5萬字8 9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