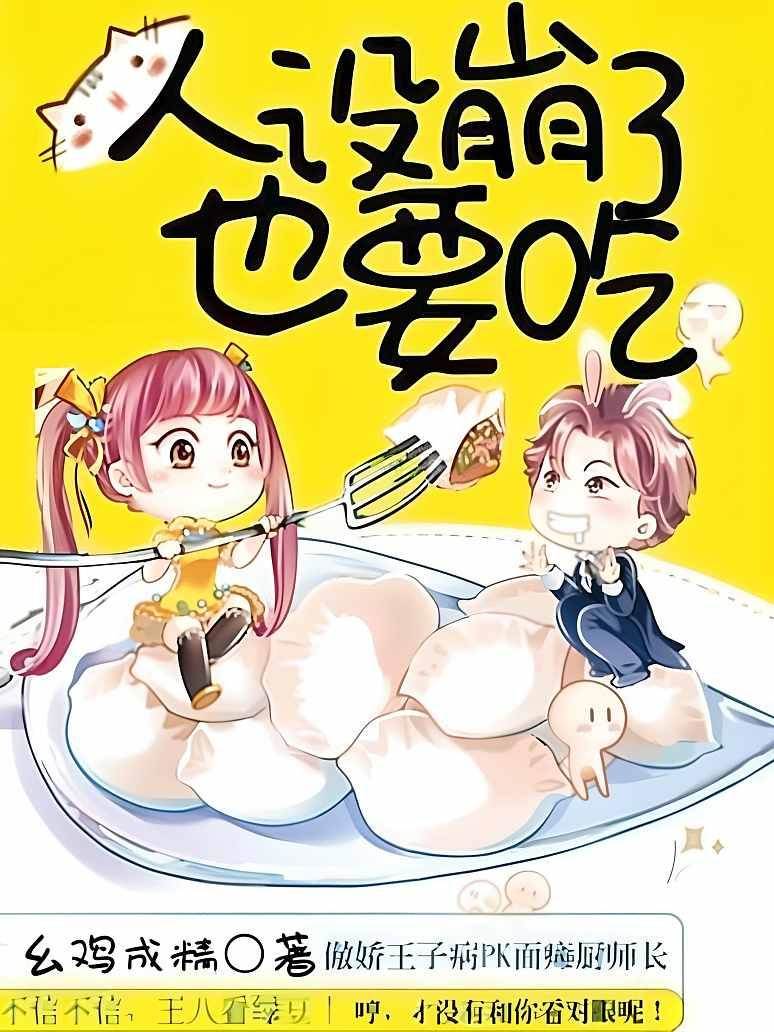《陸總眼紅失控,說好的高不可攀呢》 第143章 我來送禮的
宋澤暗暗咽下里的酒,立刻站得筆直。
沈譽白也收起了吊兒郎當的模樣,神恭敬。
蘇沫默默看向桑晚,小聲問,“這誰呀?”
桑晚心里已經猜到,畢竟這個車應該不是一般人開得起的。
車門打開。
陸家的老管家福伯,先下了車,隨即恭敬地拉開后座車門。
一只锃亮的龍頭拐杖,先探了出來。
接著,一個穿深中山裝,神矍鑠,不怒自威的老人,從車上走了下來。
陸老爺子。
桑晚沒有想到他回來,心猛地一沉。
下意識地站了起來,看向陸庭州。
陸庭州起將人攬在懷里。
低聲在耳邊道:“不會有事的。”
陸老爺子后,福伯手里捧著一個古樸的紫檀木盒。
老爺子目平靜地掃了一眼院子里的氛圍,最后視線落在陸庭州上。
小院里原本熱鬧的氛圍,因為他的到來,這一刻僵住。
所有人的目都聚焦在他上。
桑晚想上前打招呼,畢竟領了證,這個人就是公公。
雖然有過不愉快,但他畢竟已經表了態。
剛抬,被陸庭州拉住。
他將扯回自己懷里,不聲繼續攬住,迎上老爺子的目,神平靜。
“您怎麼來了。”
陸庭州的聲音,平靜無波。
而桑晚的心跳,了一拍。
像是拐了人家兒子,被人家長抓包一樣。
空氣里,只剩下燒烤架上油脂滴落的滋滋聲,顯得格外刺耳。
陸啟明瞪了自己兒子一眼。
那雙歷經風霜的眼睛,氣勢冷冽。
良久,陸啟明緩緩開口,威嚴不減,依然很有震懾力。
“領證這麼大的事,不跟家里說一聲,是不是太不懂規矩了?”
陸庭州摟住桑晚,鏡片后的眸,冷得像冰。
“我的事,不需要向任何人報備。”
Advertisement
“這會兒說我沒規矩,在我需要學規矩時,也沒見你教我。”
父子倆的對話,針尖對麥芒,火藥味十足。
沈譽白和宋澤他們大氣都不敢出。
陸啟明握著拐杖的手,青筋暴起。
他深吸一口氣,似乎在竭力制著怒火,語氣里竟帶上了一罕見的疲憊。
“我承認,為了選家族的繼承人,我對你關心不夠。”
“甚至……用了很多不該用的手段去磨礪你。”
他頓了頓,聲音沉了下去。
“現在想想,我確實不是一個合格的父親。”
這話一出,連陸庭州都微微怔住。
陸啟明將目轉向桑晚,目和。
“了家,以后要相親相。”
“晚晚,也要承擔起一個妻子的責任,多關心庭州,支持庭州。”
桑晚還沒來得及回應。
陸庭州一聲冷笑,打破了這短暫的平和。
那笑聲里,滿是譏誚和涼薄。
“自己做不好的事,就指別人幫你收拾彌補?”
“算盤打的真相,算盤珠子都蹦我臉上了。”
他一字一頓,聲音不大,卻字字誅心。
“我娶老婆,是為了讓被,讓幸福。”
“不是讓來替你善后的。”
“你沒給過的東西,憑什麼要求來給?”
空氣,徹底凝固。
陸啟明的臉,瞬間漲紅,翕,卻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他被自己最引以為傲的兒子,當著所有人的面,剝下了所有的偽裝和面。
難堪,憤怒,還有一無法言說的狼狽。
院子里的氣氛,僵得幾乎要裂開。
就在這時。
一只的小手,輕輕抬起,捅了捅陸庭州堅的胳膊。
力道很輕,卻不容忽視。
陸庭州繃的下頜線,瞬間一松。
他側頭,看向后的桑晚。
人沖他輕輕搖了搖頭,眼里的擔憂和安,讓他眼里的戾氣,奇跡般地平息了下來。
Advertisement
他閉上了。
這一幕,清清楚楚地落在了陸啟明的眼里。
他活了一輩子,人中的人,瞬間就明白了。
自己跟這個兒子的關系能不能緩和,癥結,全在這個剛過門的兒媳婦上。
陸啟明揚揚手,“罷了罷了,我來不是見你的。”
“今天我還主要有兩件事,一是給我兒媳婦送禮,二還是給我兒媳婦送禮。”
他從福伯手里接過紫檀木盒,走到桑晚跟前。
“我不是老古板,非要改口,該給改口費,這是我這個做長輩的,送你的賀禮。”
陸庭州眉峰一挑,揶揄道:“這會兒開始結了。”
“我的太太,想要什麼,我都能給。”
“勞您在這里,顯自己的能耐。”
“不會說話就閉。”陸啟明被他噎得差點一口氣沒上來,瞪了他一眼。
“我給的這份禮,你還真給不了。”
他說著,將手里的木盒,遞向桑晚。
“打開看看。”
桑晚猶豫地看了陸庭州一眼,見他沒有反對,才小心翼翼地接了過來。
盒蓋打開。
里面靜靜躺著的,一個滿綠的翡翠手鐲,還有一份文件。
最上面的幾個字,赫然是——
【房產轉讓合同】
地址那一欄,是工作室。
桑晚的心,猛地一跳。
這老爺子……好大的手筆,他確實來送禮的。
“手鐲是我們陸家的家傳之,現在給你。這份兒合同是我送你的工作室開業的賀禮,希你和庭州琴瑟和鳴,家庭幸福穩固,事業節節攀升。”
陸庭州從桑晚手里接過拿過那份文件。
快速掃了一眼后,他的目,陡然一。
緩緩轉,走到沈譽白面前,將他剛打開的一瓶啤酒,“砰”的一聲,拿走,放在了桌上。
作不大,卻帶著一山雨來的迫。
沈譽白正看戲看得起勁,被他這一下弄得莫名其妙。
Advertisement
“陸三,你干嘛?”
陸庭州抬眸,鏡片后的眼神,涼颼颼的。
“我上個月找你,讓你爺爺賣給我。”
“你說什麼?”
沈譽白努力回憶。
“我說……不是我說,是我們家老爺子說,那是我爺爺的心頭,誰來都不賣。”
“那你現在給我解釋一下。”
陸庭州將那份合同,拍在沈譽白面前的桌上。
“這是什麼?”
沈譽白郁悶地湊過去,只看了一眼,整個人都傻了。
眼睛,瞬間瞪得像銅鈴。
“臥槽?”
他兩眼一黑,差點當場昏過去。
“這事我真不知道。”
他猛地跳起來,一把揪住自己的頭發,哀嚎起來。
“陸三,三哥,我發誓,我是真的不知道啊。你讓我問,我真的問了。”
“這絕對是我爺爺背著我干的,你應該問問陸叔,他是怎麼騙了我爺爺。”
他哭喪著臉,指著一臉淡定的陸啟明。
陸啟明看著他這副活寶樣,終于出今晚第一個真切的笑容。
“釣魚贏得。”
一句話,不知道真假。
沈譽白,卻徹底蔫了。
院子里的氣氛,也因為他這麼一鬧,緩和了不。
桑晚看著眼前這戲劇的一幕,心里五味雜陳。
走到陸啟明面前,拿起一旁的茶壺,恭恭敬敬地為他倒了一杯溫熱的普洱。
“爸。”
輕輕地,了一聲。
陸啟明端著茶杯的手,幾不可查地抖了一下。
桑晚的聲音,溫又堅定。
“謝謝您的禮,我很喜歡。”
“您放心,以后,我會和庭州好好過日子。”
抬起頭,目清澈,直視著這位掌控著龐大家族的男人。
“作為他的妻子,我會把我所有的,都給他。盡我所能,讓他開心,讓他到家的溫暖。”
的目,掃過陸庭州,又回到陸啟明上。
Advertisement
“以前的事,或許有很多憾。”
“但您看,現在一切都還不晚。”
“只要用心,所有的缺憾,都可以慢慢彌補的。”
現在一切未晚。
所有的缺憾,都可以彌補。
這句話,像一溫的刺,扎進了陸啟明的心里。
他殺伐果決一生,虧欠最多,也最說不出口的,就是眼前這個小兒子。
老人家的眼眶,毫無預兆地,微微泛了紅。
他端起茶杯,掩飾地抿了一口,嚨里,卻像是堵了一團棉花,又酸又。
這個兒媳婦……
兒子的眼不錯。
“謝謝你,孩子。”
這份認可,沉甸甸的,幾乎讓桑晚眼眶發熱。
然而,這份難得的溫,卻被一陣刺耳的手機鈴聲,無地撕裂。
是陸啟明的私人電話。
能打到這個號碼上的,都不是小事。
陸啟明接起,只“喂”了一聲,臉就變了。
那張剛剛緩和下來的臉,以眼可見的速度,寸寸結冰。
幾秒后,他像是聽到了什麼天大的笑話,又像是到了逆鱗,拐杖猛地砸著地面。
龍頭拐杖重重地磕在青石板上,發出“咚”的一聲悶響。
“放你娘的屁!”
一聲暴喝,中氣十足,震得燒烤架上的串都抖了三抖。
沈譽白和宋澤,張得能塞下一個蛋。
什麼時候見過老爺子這麼罵人。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493 章

甜心玩火:誤惹霸情闊少爺
訂婚宴當天,她竟然被綁架了! 一場綁架,本以為能解除以商業共贏為前提的無愛聯姻,她卻不知自己惹了更大號人物。 他…… 那個綁架她的大BOSS,為什麼看起來那麼眼熟,不會是那晚不小心放縱的對象吧? 完了完了,真是他! 男人逼近,令她無所遁逃,“強上我,這筆賬你要怎麼算?”
90.4萬字8 37776 -
完結155 章
她不乖!要哄
【爆甜輕松 雙潔治愈 野性甜寵 校園】【嬌縱隨性大小姐x邪妄傲嬌野少爺】“疼!你別碰我了……”季書怡微紅的眼圈濕霧霧的瞪著頭頂的‘大狼狗’,幽怨的吸了吸鼻子:“你就會欺負我!”都說京大法學系的江丞,眼高于頂邪妄毒舌,從不屑與任何人打交道,只有季書怡知道背地里他是怎樣誘哄著把她藏在少年寬大的外套下吻的難舍難分。開學第一天,季書怡就在眾目睽睽之下惹了江丞不爽。所有人都以為她要完。可后來眾人看到的是,大魔王為愛低頭的輕哄:“小祖宗,哪又惹你不高興了?”季書怡永遠記得那個夜晚,尋遍了世界來哄她的江丞跪在滿地荊棘玫瑰的雪夜里,放下一身傲骨眉眼間染盡了卑微,望著站在燈光下的她小心翼翼的開口:“美麗的仙女請求讓我這愚蠢的凡人許個愿吧。”她仰著下巴,高高在上:“仙女準你先說說看。”他說:“想哄你……一輩子。”那個雪夜,江丞背著她走了很遠很遠,在他背上嬌怨:“你以后不許欺負我。”“好,不欺負。”——————如果可以預見未來,當初一定不欺負你,從此只為你一人時刻破例。你如星辰落入人間,是我猝不及防的心動。
24.2萬字8 17171 -
完結1206 章

相親當天,閃婚了個億萬富翁
【甜寵+先婚后愛+傲嬌男主】 相親當天就鬧了個大烏龍,安淺嫁錯人了。 不過,錯有錯著,本以為一場誤會的閃婚會讓兩人相敬如賓到離婚,安淺卻驚訝地發現婚后生活別有洞天。 她遇到刁難,他出面擺平。 她遇到不公對待,他出面維護。 安淺天真的以為自己嫁了個錦鯉老公,讓她轉運,卻萬萬沒想到,自己嫁的竟然是億萬富翁!
192萬字8.18 17167 -
完結7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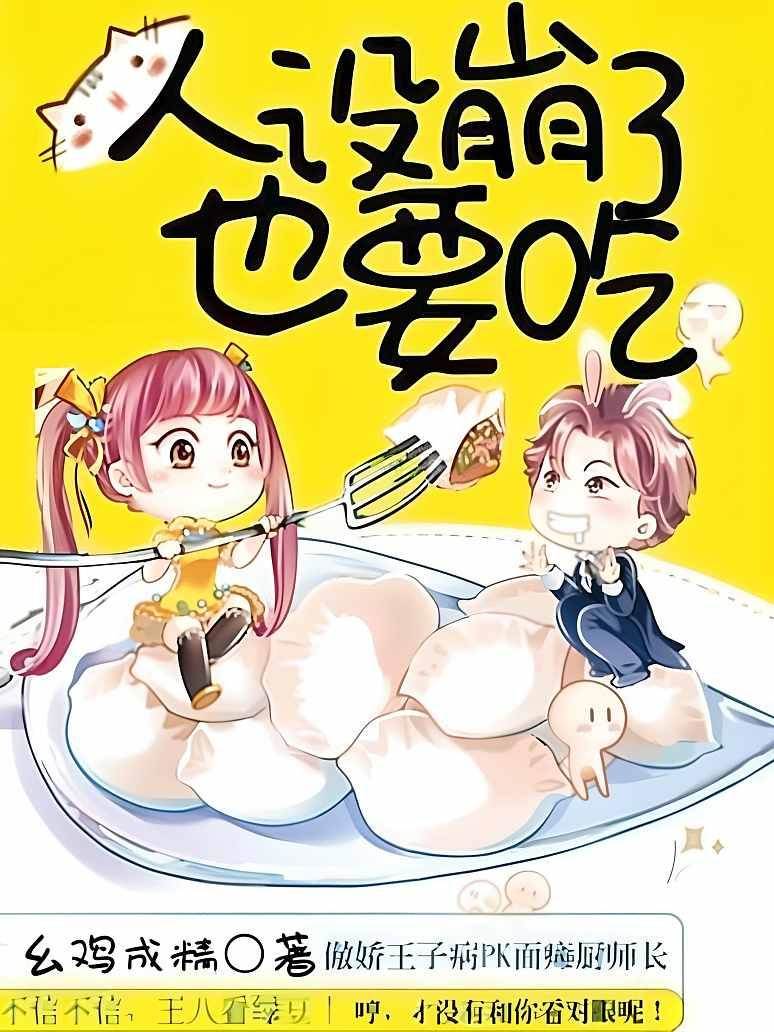
人設崩了也要吃
【那個傲嬌又挑剔的王子病和他面癱很社會的廚師長】 當紅明星封人盛,人稱王子殿下,不僅指在粉絲心中的地位高,更指他非常難搞。直到有一天,粉絲們發現,她們難搞的王子殿下被一個做菜網紅用盤紅燒肉給搞定了…… 粉絲們痛心疾首:“不信不信,王八看綠豆!” 季寧思:“喂,她們說你是王八。” 封人盛:“哼,才沒有和你看對眼呢!” 季寧思:“哦。” 封人盛:“哼,才沒想吃你做的綠豆糕!” 季寧思:“滾。”
17.1萬字8 7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