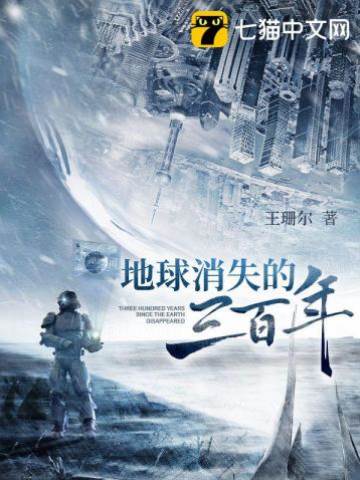《豪門獨寵:秦少的影后小祖宗》 第1卷 第120章 落荒而逃
“不懂了吧,這就做突擊檢查。”
姜暮眉弄眼地看著男人,絕對絕對不會承認是自己帶不娃了。
然而,卻忽略了秦深對的了解。
秦深挑眉:“你確定?”
這些年來,秦太太查崗的次數屈指可數,別說什麼突擊檢查,就是請都懶得過來。
依他看……
這個所謂的突擊檢查可能是跟胖閨有關。
“那當……”
同一時間,旁邊的甜寶也發出了疑問。
“麻麻,什麼是豬幾檢查,又,又豬幾檢查什麼哇?”
團子小手扯扯,仰著胖嘟嘟的小臉看向姜暮。
眼里滿是疑和不解。
檢查是幾道噠。
作為一名不怎麼喝水的小孩兒來說,只要是跟在秦深的旁,自己拎的水杯都要檢查好幾遍,不為別的,就是想看小孩兒有沒有乖乖聽話。
如果沒喝,就會被揪著小耳朵被念叨。
久而久之。
小孩兒也對檢查這個詞有了大致了解。
可是……
可是介個突擊是什麼東西哇——
Advertisement
文化程度不高的團子表示有些被難住。
而面對閨的提問,姜暮自然就不能再隨隨便便的開玩笑。
了小家伙的腦袋瓜子。
語重心長的:“寶寶,就是突然過來的意思。”接著,又補充緣由:“你爸他老是忘記吃飯,這次除了帶你過來找他玩兒,我們還有一個任務,就是監督他吃飯呢。”
“噢~”
聽完的團子似懂非懂的點點頭。
仔細看的話你會發現的眼中帶著一興。
原來爸爸也和自己一樣老是忘記喝水!
要批評!
于是好不容易逮到機會說教的團子是正義凜然,小大人似的,皺起淺淺的眉就開始佯裝不悅:“不可以,爸拔你要乖乖吃飯——”
“不吃泥就長不高了哇!”
“長不高,矮矮一個愣!”
“咦~真矮的哇——”
團子繃著表,小短手指指點點,那小模樣像極了秦深著胖臉說教時的樣子。
不可以,甜寶你要乖乖喝水——
Advertisement
不喝水你就拉不出臭臭——
拉不出,笨笨一個娃,嘖嘖嘖,真笨——
正所謂是天道好回,蒼天饒過誰。
不一樣的話,相同的語氣,在這一刻是直接還給了曾經也像唐僧念箍咒一般嘮叨個不停的秦深上。
其實姜暮倒也沒說假。
一忙起來的秦深經常是廢寢忘食,雖說最后也會吃,可是午餐時間他真的就可以生生拖到下午時分再用餐。
要不是言朝朝。
都不知道男人能把自己忙到這個程度。
一通數落。
秦深的沉默震耳聾。
姜暮也就算了……
這呆瓜躍躍試又激的小表是怎麼回事?
真是膽了,竟敢對老子說起教來了。
正要小孩兒算賬時。
“咚咚咚——”
沒有關的門被人從外面敲響。
“進。”
門打開,進來的人是言朝,他手上拎著的袋子是從食堂里打包回來的盒飯,是姜暮吩咐他去買的。
“夫人,飯買回來了。”
Advertisement
微笑,放下,轉離去。
敬業的言朝是一句廢話都沒說就干脆利落地離開了辦公室。
就——
落荒而逃。
說實話,那速度快得是團子想開口找他玩兒都來不及說出口。
眼的。
明眼人都看得出小人兒的可惜。
可是很快就來不及可惜了,因為老父親已經一把住了的胖臉。
“你剛才說我什麼?”
“長不高?”
“矮?”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586 章
穿到跟殘疾大佬離婚前
遲清洛穿進一本狗血小說,成了商界殘疾大佬作天作地的小嬌妻。小嬌妻驕縱任性,飛揚跋扈,還紅杏出牆。遲清洛穿來當天,原主正因為爬了娛樂圈太子爺的床上了熱搜。大佬丈夫終於同意跟她離婚。遲清洛:“老公我愛你,之前跟你提離婚是我一時糊塗。”輪椅上的大佬眸色深沉:“你糊塗了很多次。”不不,從今開始,她要改邪歸正,渣女回頭金不換。可是漸漸的大佬好像變得不一樣了,對她說抱就抱,說親就親。嗯?大佬不是淡薄情愛,隻把她當擺設的麼?遲清洛眨眨眼:“好像有哪裡不對。”大佬將小嬌妻圈入懷中,指腹摩擦著她的唇珠,聲音嘶啞:“哪裡不對?”
105.1萬字8 63196 -
完結2618 章

財閥小嬌妻:謝少寵上癮!
記者采訪富豪榜首謝閔行,“謝總,請問你老婆是你什麼?”謝閔行:“心尖兒寶貝。”記者不滿足,又問:“可以說的詳細一點麼?”謝閔行:“心尖子命肝子,寶貝疙瘩小妮子。”這夠詳細了吧?記者們被塞狗糧,欲哭無淚,準備去采訪某小妮子,“謝少夫人,請問你丈夫是你什麼?”小妮子認真思索,纔回答:“自……自助取款機?”男人不高興,於是,月黑風高夜,最適合辦壞事,某小妮子向老公求饒……
430萬字8.18 633245 -
完結309 章
離婚夜植物人老公蘇醒了
嫁給植物人老公的第三年,她被繼婆婆和白月光逼著強行簽下離婚協議。簽字的那一晚,植物人傅先生蘇醒,將她摁進懷中。“我同意離婚了嗎?”繼婆婆要她打掃衛生,傅先生:“我睡了三年,傅家已經窮得連仆人都請不起了嗎?”假閨蜜嘲諷她窮酸,傅先生:“一千萬以下的東西也配叫奢侈品?”渣公公想對她執行家法,傅先生:“你敢動我女人一根毫毛試試!”但喬安好凌亂的是,這男人一邊說“你這種女人也配我憐惜”,一邊又總是突然襲擊抓著她玩親親,年度第一口嫌體正直Bking真是非你莫屬。
56.2萬字8 43149 -
完結10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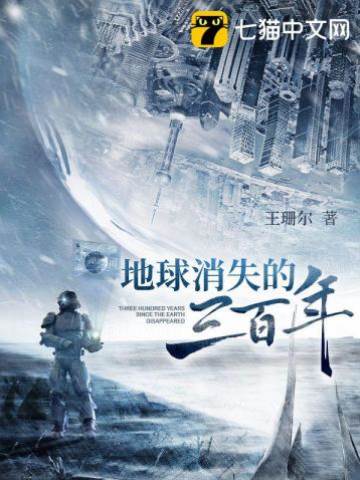
地球消失的三百年
故鄉是什麼?是游者遠行的錨,亦是旅者終歸的夢。 但當離鄉的尺度,從陸地山川,變為光年星河; 當離鄉的歲月,從經年數載,變為幾代人相隔。 故鄉之于游子,終究是…錨無定處,夢難尋歸。 踩在紅土之星上的少年們,第一次抬頭仰望無垠的宇宙,映入眼簾的,是璀璨的星河,與星河下深沉的茫然。 故鄉不過是一組毫不起眼的三維坐標,抽象而虛無。 但對那些堅定的歸鄉者而言:故鄉遠非空洞的坐標,而是永遠鮮活而寫實的,閃爍在他們的心中。
26.4萬字8 113 -
完結127 章

她浴缸里的魚
身爲遊家大小姐,遊夏過着衆星捧月般的生活。一張純欲臉無辜又清冷。 誰也不知道。高高在上的小天鵝藏着一顆怎樣期待破格的心。 被家族告知即將與陌生男人聯姻,又得知對方早有金屋藏嬌的真愛後。 遊夏憋了一夜,最後伸出手,指了個絕頂帥、身材爆好的男人解氣。 第二天清醒,遊夏偷偷摸摸打算立刻走人,結果手剛搭上門把準備開門時—— “這就走了?”身後,男人嗓音低靡。 分明心虛到不敢回頭,偏要裝身經百戰,落荒而逃前,遊夏爲了不輸面子,淡定道: “昨晚很盡興,你是我睡過最棒的男人。” 身後男人有一秒沉默。 遊夏甩上門,淡定瞬間破碎,尖叫捂頭逃走。 — 遊家與京圈頂級名門屈氏強強聯姻,一場雙豪門的世紀婚禮震驚整個名流圈。 可婚後遊夏哪哪都不滿意。 尤其討厭屈歷洲那種僞君子做派。看似清貴優雅,克己復禮,永遠衣冠端正,也永遠的寡淡無趣。 遠比不上那晚的男人生野風流。偶爾一個旖旎回味,就足以令她腿軟。 爲了成功離婚,能讓屈歷洲反感的事遊夏順手都做了遍。 她在家大搞派對,在外處處留情,恃靚行兇,作天作地。以爲屈歷洲撐不了幾天,誰知對方始終態度淡淡。 — 直到那晚屈歷洲出差,遊夏在外面喝得爛醉,回家直接睡倒在別墅內的樓梯上。 感應燈隨來人步調怦然打射,光亮又光滅。 遊夏恍惚睜開眼,來不及反應,下一秒脣上驀然被強吻的攻勢比窗外的暴雨更烈。 “你的吻技還是隻有這種程度麼?”男人停下來,啞然謔笑,“結了婚也不見半點長進。” 居然是那個男人。 遊夏掙扎的動作在惶惑中僵滯。 黑暗中她看不清對方的臉,所以無從知曉一向在她面前紳士疏離的男人,她的丈夫,此刻眼神裏壓抑着怎樣惡劣病態的破壞慾。 “是不是覺得婚姻生活很無聊。”屈歷洲擡手,修瘦指骨緩慢蹭撫過她的肩頭,吐字虛迷, “想不想重溫你說最棒的那晚?” “再盡興一次。”
32.4萬字8 13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