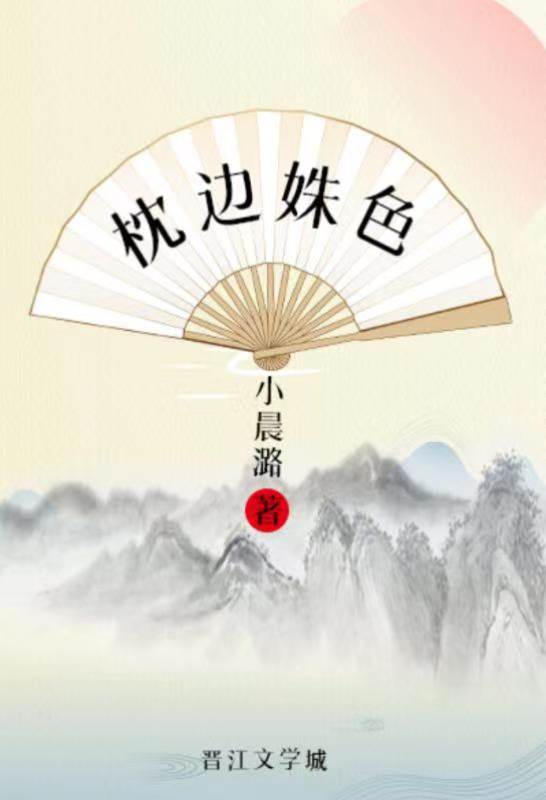《箏簫誤:重生之錯惹清冷太傅》 第1卷 第13章 人有千面,心有千變
上了島卻沒了船,不亞于今日最后一個晴天霹靂。
他們的船夫居然背棄約定,不怕得罪鎮國公府?
祝箏看了一眼溫泊秋不不慢的臉,得罪鎮國公府是不行,得罪一下溫泊秋,可能真的會無事發生。
果然聽得溫泊秋開口,“真是連累祝姑娘了。”
祝箏窘然道:“本就是……”
唉,算了。
天漸漸昏暗下去,江上已經沒什麼船只的影子了。兩人到尋了一遍,島上備用的船恰巧都不在,江面上只余下不遠還停著一艘妝點華貴的畫舫,燃著輝煌的燭火。
溫泊秋遂帶著祝箏去畫舫前求助,“借問是哪位同僚的船,可否捎帶我們一程?”
話音落,船上的珊瑚珠簾,探而出一個頎長影。
祝箏兩眼一黑,方才的話說早了,這才是最后一個晴天霹靂。
“太傅大人,原來是您的船!”溫泊秋臉上帶著慶幸,向容衍解釋緣由,“天晚了,晚輩正愁沒辦法回去,船公明明是一早付好了定金的,不知為何竟然失了約。”
容衍聽完,目雖是看向的溫泊秋,但卻好像穿過他,徑直落在了一旁的祝箏上,淡淡作了評價。
“人有千面,心有千變。”
祝箏耳后一涼,立即聽出了話外之音。
的做法如此拙劣,早就料到了會得罪容衍,這句表面在說船夫,實際上是在暗諷被愚弄的話,接著也不算虧。
祝箏角抿著僵的笑意,悄悄又往溫泊秋背后了,隔開容衍的視線,從牙里出一句話,“要不還是別叨擾太傅大人了……”
相比于登上容衍的船,滯留在島上過夜好像更容易活命一些。
祝箏聲與溫泊秋商量,“溫公子,要不再等等好了。”
溫泊秋還沒來得及說話,已然轉的容衍忽然冒出一句,“二位當心,島上多蝰蛇,喜黃昏覓食。”
Advertisement
真是要命,祝箏平生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的就是蛇。
祝箏驚疑:“真的嗎?”
溫泊秋點頭:“瑤島植草茂,難免會生些蛇蟲。”
祝箏:“快上船!”
船艙燃著燭火,容衍、祝箏和溫泊秋三人圍著一張茶桌坐下。
茶桌并不大,幾人離得很近,近的祝箏可以聞到太傅大人上淡淡的冷梅味兒,讓想起冬日清晨里,開在前堂的一樹臘梅。小時候,經常攀折一枝放在房中,比熏香還要好聞。
溫泊秋起倒了一杯茶,率先打破了上船后的沉默,客套道,“多謝太傅大人對我們施以援手。”
燭火映在容衍眼中明滅幾回,他瞇了瞇眼,好半晌才接過茶杯,擱在桌上,又不知道從哪拿出條絳紫的帕子,了他那雙白玉一樣的手。
茶室一時默然。
溫泊秋出一個溫和的笑,臉上卻難掩難堪之。
“水不經人手。”容衍淡淡抬眉,“見諒,不習慣。”
祝箏不免對溫泊秋的難堪同。
坊間流傳容衍是奉了天詔直接任命的太傅,年紀輕輕就平步青云,即便冷淡之也難掩那種金相玉質的驕矜。
與,與溫泊秋都不一樣,他們看似生在豪門大家里風無兩,實則仰人鼻息,看人臉。
從小雖挫磨,但不論闖什麼禍都一直有姐姐護著,萬幸自由自在地長了一刺。
而溫六旁出在鎮國公府中,大抵無人護佑,才養出這一無悲無喜的溫吞子。
祝箏突然到一陣悲哀,對他生出不同病相憐之。
若有朝一日,按計劃真的了鎮國公府,不妨教教他如何做到中帶刺,哪怕任人拿時,也要冷不丁別人痛上一回。
思緒飄遠時,容衍卻拿起茶壺給倒了一杯茶。
Advertisement
“當不起大人的茶。”祝箏推了推杯子,“小心弄臟了手。”
話出了口,祝箏才后知后覺一時圖個上痛快,忘了對面是什麼人。
抬頭果見容衍淡漠的眸落在臉上,神意味不明。
溫泊秋大約看出在為他出頭,急忙接過茶杯解圍,“我剛好口了,多謝大人。”
容衍按下杯沿,“的。”
溫泊秋又放下,“失禮了。”
一杯茶也夠扭如此久,察覺到兩人的視線都落在自己上,祝箏干脆地端起茶杯一口氣喝干了。
溫泊秋看豪放地牛飲,溫聲關切道,“方才還腹中不適,還是慢點喝。”
大約是因旁人在,他聲音的很低,聽起來尤為和親切,滿懷擔憂。
祝箏笑笑,“多謝溫公子……”
兩人你一言我一語時,一旁的容衍忽然起了,惹得兩人同時抬頭,還沒來得及問太傅大人意何為,船頭不知是了什麼還是遇到了大浪,猛地一傾。
劇烈的抖震地宮燈上的燭臺都倒了,骨碌碌的滾落在地,祝箏也連人帶椅整個往側邊倒去。
燭火滅掉的一瞬間,沒摔個四腳朝天,反而被人摟住了肩背,淺淡的冷梅香氣霎時將團團包圍。
借著暮的暗,祝箏看清了面前這個人的眉眼。
真是折了壽!倒進了容衍懷里。
早知如此寧愿摔個狗吃屎,真是怕太傅大人拿著那條帕子,把自己全上下都一遍。
溫泊秋也摔倒在地上,半晌才爬起來,下意識尋找祝箏,“你沒事吧,祝……”
祝箏悚然,一口氣爬起來撲過去捂住他的,“祝你健康!”
夭壽,差點他直接揭了老底。
船閣之中一時靜的出奇。雖然燭火尚未重燃,但月明亮,過船窗映的幾個人仍有一層銀邊似的虛影。
Advertisement
祝箏覺后頸一涼意,緩緩回過頭,湖面折著微,照亮了容衍的半張臉,他的眼神冷的像要把人活剮了。
祝箏連忙,“太傅大人,我不是心的,實在是……”
“過來。”容衍聲音的很低。
祝箏一愣,過去?茶室不大,他們三個人都只隔半人距離,不是已經在這兒了嗎。
還沒等想明白怎麼“過去”,手臂上傳來一力道,將向后拉了過去,祝箏輕呼一聲,旋即到手被握住,綢質的帕子裹住了的指尖。
祝箏:……
抬頭看向容衍,他不自己手,反而的干什麼?
帕子在指腹上掠過,兩人的指尖難以避免的挲,若有似無的讓心中一。
在這不明不白的境地,心里第一個冒出的念頭,居然是他的手果然很涼,骨節分明又修長,像是玉石一般的。
祝箏掙了下想回手,竟然沒有掙開。
“別。”容衍抓的更了。
他還敢出聲,祝箏生怕溫泊秋看出些什麼,不敢再拉扯,一時心急只好把寬大的袖垂下,蓋住他們握的一雙手。
可這一蓋,容衍不知道誤會了什麼,停住了拭的作,用力地反手一抓,整個手上來握了。
祝箏的手被嚴合地包在掌心,那層薄薄的帕子橫亙在兩人的雙手之間,了糟糟的一團,隔開了他掌心里的涼意,可又詭異地出些蓋彌彰的纏綿之意。
船仍在晃,祝箏的心也跟著不安地飄搖,一半是因為被握的手,一半是怕溫泊秋發現了蹊蹺。
容衍扶起椅子,扯著祝箏轉過,拔的量擋在和溫泊秋之間,把擋了個嚴實。
船窗外水聲如鼓,冷月銀輝灑落,勾勒出眼前人清絕的廓,容衍微微皺著眉,清冽的眼睛看起來生人勿近,好像醞釀著暗涌的波濤。
Advertisement
祝箏糟糟的腦袋中忽然清明了一刻,容衍了溫泊秋要,了溫泊秋也要,好像溫泊秋是什麼避之不及的臟污之一樣。
太傅大人一向行事守序從容,從不見他為什麼事過陣腳,端的是喜怒不形于,這是頭一回在他臉上看出明顯的緒,難不……
難不他和溫泊秋有什麼過節?
祝箏越想越覺得有可能,他們倆說話明顯不太絡的樣子,要真是有過節,偏偏還撞上一個同船,真是一起倒了大霉。
很快,隨侍進來稟告是遇到了暗流,并將燭火一一重燃上。
可容衍竟還沒有松開的手。
祝箏僵著脊背坐的筆直,旁人看只是坐的離太傅大人近了些,近的擺都搭在了一起,怎麼也不會想到,底下蓋著的是一雙牢牢扣的手。
一旁的溫泊秋并未發現什麼異樣,因他自被祝箏捂過之后,臉就紅的像煮的蝦子,手足無措地僵在原地,好像丟了魂兒一樣。
祝箏萬念俱灰地閉了閉眼睛,今天真是不宜出門,一整天真是從早演到晚,心俱疲。
靜夜沉沉,浮靄靄,畫舫近岸,水波被輕緩地破開,須臾又合上,圈圈波紋向遠淡開。
三人一時各有心,都沒再言語。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385 章

登堂入室
元執第一次遇見宋積雲的時候,宋積雲在和她的乳兄謀奪家業; 元執第二次遇見宋積雲的時候,宋積雲在和她的乳兄栽贓陷害別人; 元執第三次遇見宋積雲的時候,宋積雲那個乳兄終於不在她身邊了,可她卻在朝他的好兄弟拋媚眼…… 士可忍,他不能忍。元執決定……以身飼虎,收了宋積雲這妖女!
72.5萬字8.18 8869 -
完結1000 章

逆天神醫妃:鬼王,纏上癮
“王爺,不好了,王妃把整個皇宮的寶貝都給偷了。”“哦!肯定不夠,再塞一些放皇宮寶庫讓九兒偷!”“王爺,第一藥門的靈藥全部都被王妃拔光了。”“王妃缺靈藥,那還不趕緊醫聖宗的靈藥也送過去!”“王爺,那個,王妃偷了一副美男圖!”“偷美男圖做什麼?本王親自畫九十九副自畫像給九兒送去……”“王爺,不隻是這樣,那美男圖的美男從畫中走出來了,是活過來……王妃正在房間裡跟他談人生……”墨一隻感覺一陣風吹過,他們家王爺已經消失了,容淵狠狠地把人給抱住:“要看美男直接告訴本王就是,來,本王一件衣服都不穿的讓九兒看個夠。”“唔……容妖孽……你放開我……”“九兒不滿意?既然光是看還不夠的話,那麼我們生個小九兒吧!”
176.8萬字8.18 149187 -
完結972 章

一胎三寶:神醫娘親腹黑爹
四年前,被渣男賤女聯手陷害,忠義伯府滿門被戮,她狼狽脫身,逃亡路上卻發現自己身懷三胎。四年後,天才醫女高調歸來,攪動京都風起雲湧!一手醫術出神入化,復仇謀權兩不誤。誰想到,三個小糰子卻悄悄相認:「娘親……爹爹乖的很,你就給他一個機會嘛!」讓天下都聞風喪膽的高冷王爺跟著點頭:「娘子,開門吶。」
175萬字8 25431 -
完結1546 章

醫女天下:冷麵王爺欠調教
被嫡姐設計,錯上神秘男子床榻,聲名狼藉。五年後,她浴血歸來,不談情愛,隻為複仇,卻被權傾天下的冷麵攝政王盯上。“王爺,妾身不是第一次了,身子早就不幹淨了,連孩子都有了,您現在退婚還來得及。”垂眸假寐的男子,豁然睜開雙目,精光迸射:“娶一送一,爺賺了。”
268.2萬字8 25872 -
完結37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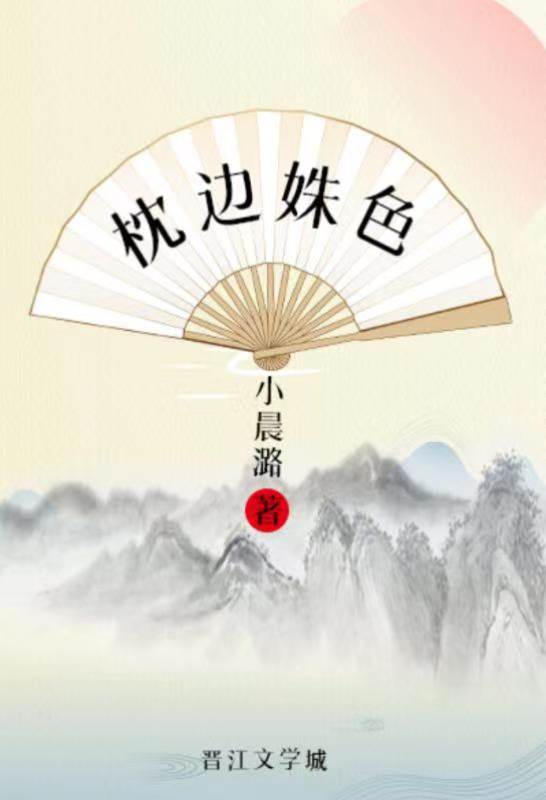
枕邊姝色(重生)
阮清川是蘇姝前世的夫君,疼她寵她,彌留之際還在爲她以後的生活做打算。 而蘇姝在他死後,終於明白這世間的艱辛困苦,體會到了他的真心。 得機遇重生歸來,卻正是她和阮清川相看的一年。她那時還看不上阮清川,嫌棄他悶,嫌棄他體弱多病……曾多次拒絕嫁給他。 再次相見。蘇姝看一眼阮清川,眼圈便紅了。 阮清川不動聲色地握緊垂在身側的右手,“我知你看不上我,亦不會強求……”一早就明白的事實,卻不死心。 蘇姝卻淚盈於睫:“是我要強求你。” 她只要一想到這一世會與阮清川擦肩而過,便什麼都顧不得了,伸手去拉他的衣袖,慌不擇言:“你願意娶我嗎?”又哽咽着保證:“我會學着乖巧懂事,不給你添麻煩……我新學了沏茶,新學了做糕點,以後會每日給你沏茶喝、給你做糕點吃。” 她急切的很,眸子澄澈又真誠。 阮清川的心突然就軟成一團,嗓音有些啞:“願意娶你的。” 娶你回來就是要捧在手心的,乖巧懂事不必,沏茶做糕點更是不必。
58.5萬字8 6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