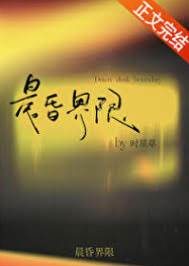《皮囊》 第93章 if線 或許,或許他適當地低一下頭…
“我還會把我和我老公上-床的視頻發給你。”
他的手放在的後頸,覺到那只手的力道在逐漸加大。
男人的聲音低沉中著磁。他低頭,和鼻梁著的肩游走。像親吻,又像是野在進食前輕嗅獵的味道。
但他的有意無意從皮上掃過,有點,聲音傳進的耳邊。
“我讓人給你打一把貞鎖,如何?”他的手指輕輕按住脖頸上的一個地方,淡聲詢問,“知道這是哪裏嗎。”
不說話。
他心的為科普:“頸脈,我稍微用點力你就會暈死過去。等你醒來的時候,或許貞鎖已經戴在了你的上。只有我能打開。”
蔣寶緹一點也不害怕。
不擔心宗鈞行真的會這麽做。
他不會的。
或許是一種直覺,也或許是能夠到。
他每次都只是將警告說的非常嚇人,但沒有一件是真的在蔣寶緹上實施過的。
適當的化了態度,兼施:“你放我回去好不好,我……我偶爾會回來看你,或者你也可以去港島找我。我有好多朋友們和男朋友都是異國。”
他只是輕笑:“Tina,哪怕是‘狗’,我都必須確保他們的脖子上只套上了我手裏的狗繩,更何況是人。”
他需要絕對的掌控和占有,而不是分隔兩地。
顯然,他不可能願意為了一個人而放棄自己提早規劃好的商業路線。
至在未來十年,他的發展中心都集中在歐洲。
畢竟不同國家的政策大不相同,限制多,手續步驟也多。他嫌麻煩。
蔣寶緹不再說話,兇地瞪著他。
宗鈞行笑容溫,手在臉上輕輕拍了拍:“談不妥就翻臉?養不的白眼狼。不該去救你,應該讓你死在外面才好。”
Advertisement
他用最溫的語氣說了最狠的話。
甚至站直,站在床邊,握住的腳踝將重新拉到自己面前。
被這突如其來的強大力道弄得猝不及防,直到恥骨撞到他的大,才反應過來。
男人寬厚的肩蟄伏下來。
高大拔的材,強悍而有力的,此時全都蓄勢待發。
他將包裝袋撕開,低下頭,在的注視下氣定神閑地重新戴好。
對比起來,他手背上的青筋都顯得沒有那麽誇張可怖了。
蔣寶緹看了眼自己的小,又看了眼他繃,更顯遒勁的手臂。
下意識地咽了咽口水,果真如他所說的那樣,自己的小還沒有他的手臂。
無論是男巨大的力量差異,還是二人的型制。蔣寶緹覺得自己能夠弄傷他,全部是因為後者的忍讓與縱容。
“既然談不妥,那就閉上繼續。”
他彎下腰,帶來的影和野般強勢危險的侵略,鋪天蓋地的向了。
……
然後就是現在了。
蔣寶緹昏昏沉沉,睡到第二天。
有些憔悴,或許是由于昨天的事。
但并沒有往心裏去,洗了個澡換上服慢吞吞地下樓。
和宗鈞行的關系如今變得十分詭異。從前的溫順乖巧,和強勢霸道的宗鈞行完互補。
但現在的可以說是無時無刻都踩在宗鈞行的雷點上蹦迪。
誇張的煙熏妝,拉長的眼線。
頭發戴的是假發,前段時間讓人從國代購來的,上萬一頂,純手工,真發編的。
倒還好,沒那麽誇張,白金,長卷發披散,戴了一頂鴨舌帽。
搭配上的煙熏妝和那對大圈耳環後,有種頹靡的。
像在叛逆期的芭比。
倒是很符合當下這個階段的蔣寶緹。
前幾天和媽咪通話中得知,爹地將接了回去,昨天二人還一起吃飯了。
Advertisement
說到這裏時,媽咪的聲音裏帶著一些甜。
蔣寶緹愣了很久。爹地不是打算將媽咪送回鄉下嗎,怎麽又突然將人接了回去?
思考了很久,最後所有線索都指向同一個人。
-
今天的打扮將Saya嚇了一跳,後者略帶遲疑,還以為這位是Tina小姐的朋友。
直到開口說話,聽到悉的聲音,Saya才確認是。
“Saya姐姐,您昨天烤的曲奇餅還有嗎?”
Saya的視線落在的臉上,愣了許久。今天的Tina小姐和往常很不一樣。
平日裏的穿著打扮都十分致,眼可見的貴氣大小姐。
吹彈可破的白皙皮,的像是剛剝殼的蛋,尋不見孔。占盡年齡優質的那張臉上膠原蛋白富,眉目明豔,偏又多出幾分我見猶憐的。人忍不住想要憐惜。
而現在……
仍舊明豔出衆,卻是完全不同的覺。
現在的簡直就是徹頭徹尾被寵壞的驕縱大小姐。
Saya吞下詫異,輕聲致歉:“隔夜後口會變差,昨天您一直沒下樓,我拿去給福利院的小孩們分去了。”
蔣寶緹點了點頭。
Saya說:“您要是想吃,我再去烤一點?”
“不用了。”蔣寶緹有禮貌地拒絕,“我今天不知道怎麽,有點苦,所以想吃點甜的。”
Saya說:“今天做了沙拉,我去給您拿一些。”
“不了。”再次拒絕,“我沒什麽胃口。”
最近在穿著上很是低調,就連包也是普通的帆布包。
至始至終都沒有看餐廳的另一個人。哪怕他的存在強到讓人完全無法忽視。
對方同樣一言不發,一杯熱喝了半個小時。
蔣寶緹走出去,咳嗽了幾聲。嗓子有點幹。大概是上火了。
Advertisement
待人走遠後,男人這才放下手中那份看了半小時仍舊連第一行都沒看完的財經報紙。
作從容地將報紙折好,隨手扔進垃圾桶中,然後吩咐Saya,晚上煮些梨子水。
Saya眼觀鼻鼻觀心地點頭,并不多問。
這幾天家裏的氛圍一直很怪,給人一種很和諧,卻又像是假象的和諧。
白天沒什麽流的二人,晚上倒是整夜整夜地流。像是將所有緒都發洩在了那方面。
白天越恨,晚上做的越狠。
Saya每天早上五點過來協助廚房料理食材,二樓的靜仍舊沒有停止。
Kroos先生的上總是帶著傷,大多都是咬傷或是指甲的劃痕,Tina小姐也沒好到哪裏去。
總是腫的,甚至連走路都沒辦法將并攏。稍微到就會被刺激到彎下腰。
Kroos先生更是直截了當地讓Saya這段時間多給煮些補和恢複力與氣的湯藥。
至于是在哪裏耗費掉了力和氣,答案不言而喻。
蔣寶緹不領:“不需要你假好心。”
他輕笑:“我只是不希你下一次又會在我幹到起勁的時候,昏死在我懷裏。”
先是一愣,隨後眼睛了一下,最後移開目。睫了,眼底流淌的都暗淡了。
抿得的,一副強忍委屈的倔強模樣。
宗鈞行的心髒莫名被這副神輕微刺痛。
“我……”遲疑片刻後,他放緩了語調,手向。
似乎是想要解釋,為自己剛才鋒利冷漠的話道歉。
他最近的確有些‘失控’
但蔣寶緹已經跑上了樓。
那天晚上家裏倒是難得的平靜。
Kroos先生在客廳坐了一整晚。一言不發。
偶爾會朝二樓某個大門閉的房間看一眼。
Advertisement
他很沉默,卻不是以往的冷淡與傲慢。
而是另一種緒。Saya看不懂,但猜想,應該是一種不太好的緒。
否則他也不會喝那麽多酒,那麽多煙。
Saya到底是沒能堅守住自己的職業底線,去找William詢問這件事。
那位沉默寡言的男人面無表的警告:“這不是你有資格過問的,做好自己事。”
Saya立刻不敢再開口。
或許是對方總被Tina小姐用言語訓來訓去,說他是機人,還說要扣掉他的電池。導致Saya忘了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William對Tina小姐溫順沒有脾氣,是因為Kroos先生。
如果沒有Kroos先生友這層關系,恐怕在第一次手去找他後頸上的電池時,手臂骨頭就被William給卸掉了。
到了第二天,蔣寶緹終于肯從房間裏出來。將自己櫃裏的那些服統統拿去捐掉了。
那些都是宗鈞行買給的。
之所以記得如此清楚,因為這些都是他喜歡的風格。
乖乖風格。
蔣寶緹才不喜歡。
去死吧!
現在的和在青春叛逆期的兒沒有任何區別,而宗鈞行這位daddy,顯然比真正的爹地了幾分慈。
——當然,不是指蔣寶緹自己的爹地。
接了同學的邀請,去參加一個深夜派對。妝都化好了,離開時卻到剛好從書房出來的宗鈞行。
他看到臉上誇張的妝容,又看了眼斜挎在肩上的包。立刻明白要做什麽。
一言不發地將拉進盥洗室。
蔣寶緹想要離開,剛撲到門邊,被他輕松拉走。
他將門從裏面反鎖,當著的面把鑰匙扔進馬桶中沖走。
“你要做什麽……”蔣寶緹只能大聲呼喊Saya。
宗鈞行無于衷地看呼救。
他沒有給答案,而是用另一個問題讓自己認清現實:“你覺得他們為什麽會聽你的話。”
他無比冷靜,卻也無比尊貴。高高在上的姿態一如往常。這讓蔣寶緹開始心虛。
深的西裝馬甲將他的冷淡氣質再次拔高。
宗鈞行不可能先低頭的,清楚這一點。但于此同時,也不可能低頭。
他休想。
所以這一次的冷戰就是死局。他們之間可能會一直這樣持續下去。當然,宗鈞行想要強迫同樣簡單。
雖然目前這個程度本算不上強迫。
可他的耐心是有限的,總有被耗的那一天。
“我知道是因為你,這裏的所有人對我好都是因為你,包括學校的教授,還有平時遇見的那些的人……不過也無所謂,反正我在港島過的也是寄人籬下看人臉的生活,我已經習慣了。”
說這些的本意并不是為了賣慘博同,以現在的境,賣慘對來說就是示弱。
不可能這麽做。
甚至恨不得立刻去醫院做個加固手,將全的骨頭都化一遍。
每次因宗鈞行的強態度而短暫生出服念頭的時候,都想給自己跪下。
——求求你有點骨氣。
之所以說這些,只是為了表達自己的決心。
可對方在聽完說的這番話後,那雙眼睛卻變得更加沉,那風雨來的翳氣場令後背發涼。
“所以,這就是你無論如何都要回去的家?”他的聲音有些不太正常的嘶啞。
沒想到他會問出這個問題。蔣寶緹愣了一下:“再怎樣那裏也是我的家。”
“這裏也可以是。”他說。
“不是。我們沒有緣關系。”
他的視線落在的小腹上,充滿暗示的一段話:“有個辦法可以讓我們的緣連接在一起。”
蔣寶緹過了很久才反應過來。
捂著自己的肚子後退。
才不要懷他的孩子。
宗鈞行似乎也很快清醒,他角微挑。眼底的輕嘲不知是在笑,還是笑自己。
那天的派對沒能去,宗鈞行讓卸妝不肯。最後還是他自己親手替卸掉的。
將拉到洗手臺前,一點一點替去臉上化妝品留下的痕跡。
他之所以會,是因為之前有過類似的經驗。
蔣寶緹很貪睡,力也不足,很多次他還埋在的裏,就已經昏死過去。
上一次宗鈞行不清楚臉上的妝容需要卸掉,導致帶妝睡了一整晚的,第二天一直在嗔埋怨。
“帶妝睡覺很傷皮的!”
宗鈞行不懂這個,但他還是記住了的委屈。
所以無論有沒有化妝,抱著去洗澡時,他都會仔仔細細地將整張臉用卸妝油清理一遍。
往往第二天都會換來雀躍地親吻。
“你真好,還幫我卸妝。獎勵你親我一百下。”
而現在,不不願地坐在那裏,眼睛裏全是不服氣。
宗鈞行的太xue突然一陣陣地發脹。
他擡手按了按,鋪天蓋地的疲憊在此刻湧了上來。
他最近開始思考,將留在自己邊的做法是正確的嗎。
或許,或許他適當地低一下頭,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還是個孩子,可以任。或許,他也該服一次。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205 章

晚安,蘇醫生
作為一名醫術精湛的外科醫生,卻被人用威脅用奇葩方式獻血救人?人救好了,卻被誣陷不遵守醫生職業操守,她名聲盡毀,‘病主’霸道的將她依在懷前:“嫁給我,一切醜聞,灰飛煙滅。”
35.7萬字8 19772 -
完結209 章

日日招惹,矜貴男主被勾纏失控了
【極限撩撥 心機撩人小妖精VS假禁欲真斯文敗類】因為一句未被承認的口頭婚約,南殊被安排代替南晴之以假亂真。南殊去了,勾的男人破了一整晚戒。過後,京圈傳出商家欲與南家聯姻,南家一時風光無限。等到南殊再次與男人見麵時,她一身純白衣裙,宛若純白茉莉不染塵埃。“你好。”她揚起唇角,笑容幹淨純粹,眼底卻勾著撩人的暗光。“你好。”盯著眼前柔軟細膩的指尖,商時嶼伸手回握,端方有禮。內心卻悄然升起一股獨占欲,眸色黑沉且壓抑。-商時嶼作為商家繼承人,左腕間常年帶著一串小葉紫檀,清冷淡漠,薄情寡欲。卻被乖巧幹淨的南殊撩動了心弦,但於情於理他都不該動心。於是他日日靜思己過,壓抑暗不見光的心思,然而一次意外卻叫他發現了以假亂真的真相。她騙了他!本以為是自己心思齷鹺,到頭來卻隻是她的一場算計。男人腕間的小葉紫檀頓時斷裂,滾落在地。-南殊做了商家少夫人後,男人腕間的小葉紫檀被套入了纖細的腳踝。男人單膝跪地,虔誠的吻著她。“商太太,今夜星光不及你,我縱你欲撩。”從此,做你心上月。
31.5萬字8.18 15202 -
完結156 章

掌心獨寵:錯撩權勢滔天的大佬
【雙潔 先婚後愛 頂級豪門大佬 男主病嬌 強取豪奪 甜寵 1V1】人倒黴,喝涼水都塞牙去中東出差,沈摘星不僅被男友綠了,還被困軍閥割據的酋拜,回不了國得知自己回敬渣男的那頂「綠帽」,是在酋拜權勢滔天的頂級富豪池驍“能不能幫我一次?”好歹她對他來說不算陌生人“求我?”看著傲睨自若的池驍一副不好招惹的模樣,沈摘星咬牙示弱:“……求你。”聞言,男人突然欺身過來,低頭唇瓣擦過她發絲來到耳邊,語氣冷嘲:“記得嗎?那天你也沒少求我,結果呢……喂、飽、就、跑。”為求庇護,她嫁給了池驍,酋拜允許男人娶四個老婆,沈摘星是他的第四個太太後來,宴會上,周父恭候貴賓,叮囑兒子:“現在隻有你表叔能救爸的公司,他這次是陪你表嬸回國探親,據說他半個身家轉移到中國,全放在你表嬸的名下,有900億美元。”周宇韜暗自腹誹,這個表叔怕不是個傻子,居然把錢全給了女人看著愈發嬌豔美麗的前女友沈摘星,周宇韜一臉呆滯周父嗬斥:“發什麼呆呢?還不叫人!”再後來,池驍舍棄酋拜的一切,準備入回中國籍好友勸他:“你想清楚,你可能會一無所有。”池驍隻是笑笑:“沒辦法,養的貓太霸道,不幹幹淨淨根本不讓碰。”
28.6萬字8 15484 -
完結578 章

億萬寵婚:神秘老公狠兇猛
他是A市帝王,縱橫商界,冷酷無情,卻唯獨寵她!“女人,我們的契約作廢,你得對我負責。”“吃虧的明明是我!”某宮少奸計得逞,將契約書痛快粉碎,“那我對你負責!讓你徹底坐實了宮夫人的頭銜了!”婚後,宮總更是花式寵妻!帶著她一路虐渣渣,揍渣女,把一路欺負她的人都給狠狠反殺回去。從此人人都知道,A市有個寵妻狂魔叫宮易川!
106.2萬字8.18 5443 -
完結19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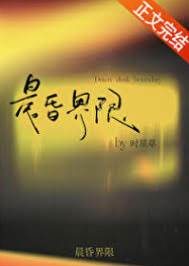
晨昏界限
林霧有些記不太清自己和陳琢是怎麼開始的,等她後知後覺意識到事情變得不對勁時,他們已經維持“週五晚上見”這種關係大半年了。 兩人從約定之日起,就劃分了一條明顯的,白天是互不相識的路人,晚間是“親密戀人”的晨昏界限。 而這條界限,在一週年紀念日時被打破。 - 人前不熟,人後很熟的故事TvT
27萬字8 564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