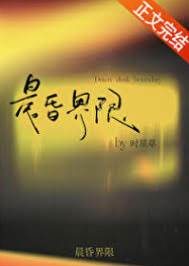《金總,太太又帶小姐離家出走了!》 第1卷 第137章 太驚悚了!
這是一群專門在國外向國行騙的團伙。
胡闖想暴揍他們一頓,卻發現沒有下手的地方,這些人挨得太慘了。
而且錢已經還了回來,胡闖報了警,讓警方來拿人。
這個團伙不知已經騙了多人的汗錢,案子一旦破了,是件大功。
負責此案的警察納悶:“您是怎麼抓到他們、并把他們引渡回國的?”
胡闖:“......”
他知道個鬼。
這不是陳奇送來的嗎。
胡闖去了陳奇公司。
不知為何,陳奇助理張兮兮攔住他:“胡|總、胡|總,陳總有客,正在忙...”
“什麼客,”胡闖向來不客氣,“那我等五分鐘,他趕送客。”
“您、您稍等。”
助理匆匆忙忙地敲門,進了老板辦公室。
胡闖越看越可疑。
陳奇是誰的人。
是金北周的!
胡闖知道這點,哪怕金北周死在那場炸中,陳奇也是簽了賣契的,他永遠是金北周的人。
誰有這麼大的能耐,不僅立刻抓到了在國外行騙的團伙,還轉將這個團伙送給了胡闖。
胡闖被做局的事目前只有嘉木的人知道。
除非有人在背地里關注他。
而這個“關注”,不帶有惡意。
胡闖可不相信是陳奇。
他跟陳奇沒這麼深的。
短坐半分鐘,胡闖起,隨手拉了個人詢問:“你們這后門在哪?”
對方支支吾吾指了個方向。
胡闖點頭,火急火燎地趕了過去。
他走的安全通道,又黑又暗,拐角是綠森森的指示牌。
可胡闖心臟在跳。
跳到他耳鳴。
媽的。
你|他|媽最好是這樣。
最好是他幻想的這樣。
不然他就掘了那座墳,把某只鬼的祖宗都罵八千遍。
Advertisement
到了后門,呼啦啦沖進眼底,胡闖盯著前方那群人,一時間愣神住。
那群人明顯是從后門先他一步出去的。
幾位西裝筆的英男,簇擁著一位高瘦的男人,男人黑黑,背脊拔,長優越,整個背影宛若削薄的竹片。
要問胡闖認不認識。
就是化灰他都記得這個背影,這個后腦勺的主人。
他們兩歲相識,五歲相知,什麼焦安、駱興都是過客,只有胡闖才是他屹立不倒的真發小。
太驚悚了。
實在太驚悚了。
胡闖竟然停在原地,連聲音都發不出來。
就在昨天他還去上過墳,給某人燒了數不清的元寶紙錢,生怕他在地下沒錢花。
結果呢。
他媽居然又活了!
胡闖想沖上前,兩只腳卻死死黏在原地。
那群人已經到了停車場,旁邊英男彎腰,恭恭敬敬地打開車門。
下一秒。
胡闖電火石地沖了過去,一把推開旁邊人,生猛地拽住某個即將上車的男人。
所有人都錯愕住。
胡闖作極快,惡虎撲食似地掀掉他棒球帽和口罩。
兩人四目相對。
那麼烈,那麼亮,亮到胡闖眼睛都在痛,在辦公室對著路櫻嚎啕痛哭的眼又開始流出眼淚。
“m的,你他m的,”胡闖哆嗦,反反復復就這兩句,“我|草你祖宗了我,遭了你這種朋友,m的...”
男人臉冷白,失去的白,并不是被他嚇到,像是一直不是很好,勉強維持生命征的模樣。
胡闖邊流淚邊罵:“老子給你上了一年的墳,你現在告訴老子,你沒死?老子燒的錢都被誰冒領了?”
Advertisement
周圍死寂。
風從耳畔拂過,眾人甚至能聽見樹葉飄落。
“金北周!”胡闖忽然怒吼,“你|他|媽說話!”
男人一雙丹長眸,薄略抿,開口時聲線偏啞:“你可以繼續當我死了。”
“...我|草你媽,”胡闖喃喃,“這種話你都能說出口。”
金北周撥掉他手,淡聲:“別往外說。”
“......”胡闖破口大罵,“那你回來干什麼?你回來是干什麼的!”
金北周線僵直。
胡闖險些痛哭流涕:“你不如一直別回來,我們就當你死了,然后呢,你躲在暗看我們為你傷心好玩對吧??”
場面沉默。
半晌,金北周:“別哭了,像只被游客喂了辣椒結果辣到眼睛的大狒狒。”
“......”
日。
你媽。
胡闖一拳頭砸他后背。
金北周形微不可察的踉蹌,眉宇不經意擰住,略微痛苦的神。
“胡|總!”旁邊人急停,“家主剛做過手,您不能這樣!”
“......”胡闖愣了,“手,什麼手?”
“沒什麼,”金北周表恢復平靜,“我還有事...”
“我管你有什麼事,”胡闖矮腰,先他一步鉆進車,“我要跟!”
“......”
邊人請示的眼神。
金北周輕抿了下:“隨他。”
胡闖一點都沒客氣,在車里東西,最后把座椅放低,半躺的姿勢,大爺似地吩咐司機:“扔罐啤酒來。”
司機回頭詢問。
“不用問他,”胡闖還在生氣,“他已經自難保了!”
金北周坐在另一側,車門被人從外關掉。
“給他。”
Advertisement
司機從車載冰箱掏出罐啤酒遞過來。
“嘶——”啤酒冒泡的聲回在車。
胡闖直接用手了,往車豪華的座椅上一蹭,一副熊孩子找揍的調調:“說吧。”
沒人理他。
胡闖眼尾撇過去:“要不,我找小櫻櫻來跟你談。”
金北周瞳孔了下,終于愿意給他回應:“你別說。”
“怎麼,”胡闖呵笑,“千辛萬苦的回來,手剛做完,恢復期都沒過吧,難道不是為了老婆孩子?”
“......”
胡闖靠近了些,盯著他:“回你爸那兒了?我剛聽那些人喊你,家主?家里斗結束了?”
金北周嚨里發出個音:“嗯。”
一個不含半點溫度的字,回答了胡闖所有問題,波瀾不驚地掩蓋住這一路艱難與辛酸。
“那可牛了,”胡闖諷道,“赫赫有名的世界級大佬,功名就了,回來看看我們這些小人?”
金北周撇臉,冷若冰霜地看他一眼。
“我只是想親眼看看們好不好,”他啞著嗓子,“沒想打擾任何人。”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813 章

爹地又來求婚啦
喬沫沫嫁給了一個植物人,安安份份的守著活寡,卻被神秘男人奪了清白,給老公戴了一頂綠帽子,喬沫沫內疚不己,某天醒來,老公翻身將她壓住,老公醒了怎麼辦?人前,他冷漠霸道,手腕鐵血,人后,卻是個寵妻狂人,喬沫沫藏起孕肚,提出離婚,卻不料,被男人強悍拽入懷。“帶著我的孩子,要去哪?”男人邪魅問他。“你的孩子?”喬沫沫睜圓雙眸。慕少撕掉偽裝的面具后,馬甲滿天飛,喬沫沫氣的扶墻吐血,這種老公,還能要嗎?
197.2萬字8 29573 -
完結19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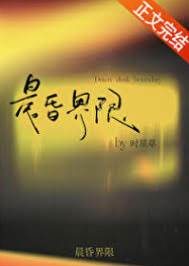
晨昏界限
林霧有些記不太清自己和陳琢是怎麼開始的,等她後知後覺意識到事情變得不對勁時,他們已經維持“週五晚上見”這種關係大半年了。 兩人從約定之日起,就劃分了一條明顯的,白天是互不相識的路人,晚間是“親密戀人”的晨昏界限。 而這條界限,在一週年紀念日時被打破。 - 人前不熟,人後很熟的故事TvT
27萬字8 564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