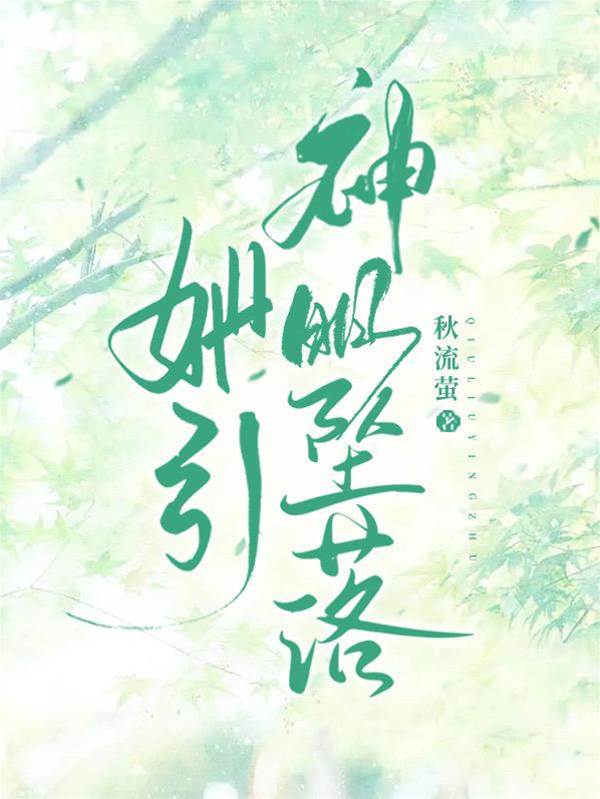《致命牽引》 第二百五十三章
有莊念在,就永遠有重新開始的勇氣。
那一刻顧言的腦子里只有這一個想法。
他抓了莊念的手,十指相扣的模樣,然后帶著莊念的手一起在對方頭頂上了。
莊念隨著作微微瞇了瞇眼睛,稍一抬肩膀像只討人喜歡的貓咪,罕見的出些天真的笑意。
他們沒有親吻也沒有擁抱,唯有十指扣著,卻覺得所有的事都剛剛好,足夠了。
楊舒從衛生間回來之后顯得有些焦慮,杯子里的茶沒的很快,不時就看一眼手機。
“顧叔叔那邊發生什麼事了嗎?”顧言也看了一眼腕表,隨手給楊舒又添了一杯普洱。
距離楊舒的那句‘很快’已經過去了將近四個小時。
無論對方是坐飛機地鐵又或是走高速的私家車,這會都應該到了。
楊舒將手機屏幕上鎖,一閃而過的手機壁紙上,是和顧穆琛在老宅時的合照。
顧言之所以記得這麼清楚,是因為那張照片是用顧穆琛買個他的第一臺單反相機拍下來的。
當時楊舒抱著他,親吻他的額頭,說他將來或許能為一名優秀的攝影師。
顧言的眸暗了暗,莫名覺得杯子里的茶葉過于苦了。
“你怕時間來不及的話,我們可以找個折中的地點面。”顧言放下茶杯,依舊是親切而禮貌的微笑著說。
楊舒擱在茶桌上的手貌似變得有些僵,但很快又松弛下去,平靜的說,“可以,我讓對方發定位過來。”
很快撥通了電話,長久的忙音一直響到提示音后自掛斷,這種況連續了幾次,楊舒秀一簇,面頰上急出了一不正常的紅。
沉默片刻,楊舒很快撥通了另一個號碼,在接通之前似乎想到了什麼,快速掃一眼顧言說,“我出去打個電話。”
Advertisement
顧言笑了笑,沒說話。
“你們兩個在做什麼?青川呢?”等楊舒離開房間,顧言睨了一眼邊的莊念,語氣里沒有半分責怪,只是疑。
乘著話音,顧言的電話已經撥了出去。
夏青川那邊接電話接的倒是很快,“這貨嚴得很,再給我兩個小時。”
夏青川說話時息很重,同時對面傳來幾聲類似重撞出的悶響。
顧言落在膝上的另一只手拇指和食在一起輕輕攆了攆,仿佛嘆了口氣,又或者沒有,“我知道你們的懷疑,但我們沒有時間求證了,我不能拿顧氏去冒險。”
顧言說話時很在長句中強調那麼多個‘我’字,說明他此刻自我意識非常強烈,并沒有面上表現出的那麼平靜理智。
戴淑惠在他眼皮底下失蹤,楊舒和顧氏集團又在他以為周全的況下發生了現在這樣棘手的事。
不只是楊舒在他做決定,他自己也在自己,要盡快做出決定。
“怎麼不能了!”夏青川那邊憤怒的語調穿聽筒傳莊念耳中,“顧氏是你的?跟你有半錢關系?”
“顧言,一路走過來有多不容易這些話我不想再反復提醒你。”乘著話音,夏青川那邊仿佛有人悶聲痛,又被下一次劇烈的撞聲打斷,“這件事你媽上的破綻那麼多,連莊都看得出來,你真一無所知?”
“算了。”夏青川長吁一口氣,“我只問你,你有沒有想過,沒有了錢你要怎麼照顧你邊的這些人?你還拿什麼保護你想保護的人?”
這一次顧言沉默了將近半分鐘的時間,然后出口袋里的煙敲出一,走到窗邊點燃。
茶室后院柵欄支的很高,擋住了吵嚷的街景,圍著的是一片小花田,迎春花已經開的團團簇簇。
Advertisement
原該是一片燦然,卻因為最近雨連連,明黃的小葉片懨懨垂著。
“問出什麼了?”顧言將煙吸進半只,緩緩開口說。
夏青川頓了頓。
顧言問出這樣的問題,就代表他需要從楊舒上找問題,找他們兩個口中的破綻,這對他來說太難,也太疼了。
“今晚顧氏集團確實要開東大會。”夏青川那邊徹底安靜了下來,聲音也跟著沉了幾個調,“但...姓顧那個說和謀權篡位什麼的沒關系,你媽在顧氏坐的還很穩。”
“不知道是姓顧那孫子太嚴還是他真的不知道幕,他也不知道楊舒究竟要做什麼。”夏青川第一次在顧言面前直呼楊舒的名字。
顧言嗯了一聲,“讓我想想。”
話說到這里就應經足夠了。
問題既然不是出在顧氏集團上,那就該是沖著他的GN來的。
只要顧言冷靜下來,或者說只要他愿意思考,那麼莊念看到的事他只會看的更清楚。
楊舒雖然恨他,但不至于要用這種手段來要他的GN,不屑將他的東西和顧氏集團混為一談。
GN不是楊舒要的,那麼楊舒要的...
就該是戴淑惠。
GN應該只是楊舒用來和背后那個人換戴淑惠的籌碼而已。
而要讓他一無所有的,試圖用奪走他的一切來讓他乖乖聽話的人,當然只會是唐周。
“真是繞了好大的一個圈。”顧言吸進最后一口煙,將角落里的煙灰拖近,煙點在里面利落掐滅,他說,“讓顧叔叔管好了再來,別傷到臉,合同我們正常簽。”
掛電話之前,顧言又讓夏青川單獨查了一下這位‘顧叔叔’的私人賬目。
代完要辦的事,他轉走回莊念邊落座。
“還要簽?”莊念從顧言那通電話里已經聽了個大概,他猜對了。
Advertisement
他的眼神乘著滿滿的憂心,在視線對上顧言那雙眼睛時因為愧疚躲開一瞬又很快轉回去道歉,“我怕你會傷心...沒第一時間和你說整件事...有點怪。”
顧言抿著長出一口氣,了他的臉,“想不想知道顧氏集團今晚的東大會是為了做什麼?”
莊念眨了眨眼,用力點頭。
那雙桃花眼在人前是從容淡然,在顧言面前總會不自覺流出幾分乖順。
顧言笑了笑,“我沒猜錯的話,大概是要追回我那位顧叔叔手里的所有份。”
“不是都賣給你了,怎麼追回?”莊念問。
顧言徐徐說了很多法律上的相關事由,莊念似懂非懂,大概的意思就是在某種特定的況下,簽署的份轉讓合同是可以撤銷的。
這個‘某種特定的況’不用切實發生,顧氏集團的法務總會有辦法令其發生。
“如果你和顧叔叔的合同不立,那他不是也要把GN還給你?豈不是大家都白忙活一場?為什麼?”莊念認真的問。
“GN不是顧叔叔的,大概在今天的合同簽署之后就會為我媽媽的,然后在今晚之前再轉手給...”顧言看了看莊念,將莊念鬢邊凌的頭發捋順,緩緩說,“唐周。”
莊念淺的瞳仁驀地一震。
“所以,只要你媽媽不松口,不把GN還給你,你就沒辦法再繼續上訴,到時候顧氏集團的份不是你的...”莊念突然抓住顧言的手,用兩只手將其握在手心里,“GN也不是你的了。”
是,唐周就是看準了顧言對楊舒百依百順這一點,所以要讓楊舒來摻和這一趟渾水。
只要楊舒為計劃里的其中一環,牽扯到法律,顧言就沒辦法。
到時候哪怕楊舒只是像打發乞丐一樣給顧言幾十萬或幾百萬,或者像當初將顧言趕出顧家那樣決絕狠辣,什麼都不給...
顧言沒辦法。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連載4114 章
罪妻來襲:總裁很偏執
易瑾離的未婚妻車禍身亡,淩依然被判刑三年,熬過了三年最痛苦的時光,她終於重獲自由,然而,出獄後的生活比在監獄中更加難捱,易瑾離沒想放過她,他用自己的方式折磨著她,在恨意的驅使下,兩個人糾纏不清,漸漸的產生了愛意,在她放下戒備,想要接受這份愛的時候,當年車禍的真相浮出水麵,殘酷的現實摧毀了她所有的愛。
361.9萬字8 23603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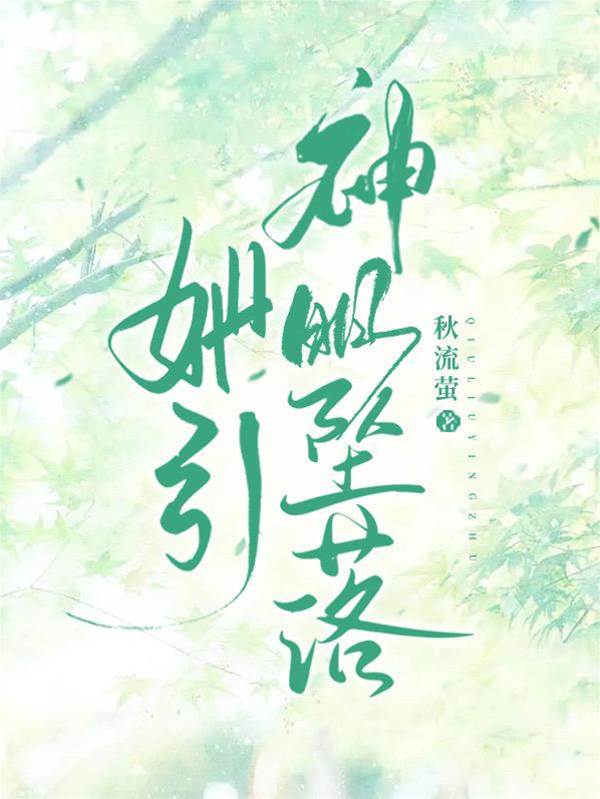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5509 -
完結311 章

昨夜燈暖
三年前,蕭叢南被迫娶了傅燼如。人人都道,那一夜是傅燼如的手段。 於是他一氣之下遠走他鄉。傅燼如就那樣當了三年有名無實的蕭太太。 一夕鉅變,家道中落。揹負一身債務的傅燼如卻突然清醒。一廂情願的愛,低賤如野草。 在蕭叢南迴國之後。在人人都等着看她要如何巴結蕭叢南這根救命稻草的時候。 她卻乾脆利索的遞上了離婚協議書。
51.4萬字7.82 115868 -
完結120 章

豪門小可憐?不,是你祖宗
豪門小可憐?不,是你祖宗小說簡介:宋家那個土里土氣又蠢又笨的真千金,忽然轉性了。變得嬌軟明艷惹人憐,回眸一笑百媚生。眾人酸溜溜:空有皮囊有啥用,不過是山里長大,
22.5萬字8.46 589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