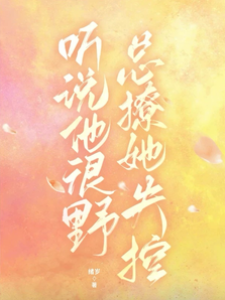《危情泰蘭德》 第1卷 第60章 我的錯
回這雙發狂野的瞳孔,知道他吃了虛無的醋,心里有些好笑。
良久他問,“剛才在外面沒遇見什麼奇怪的人吧?”
黛羚裝作一臉平靜,抬頭問他,什麼奇怪的人。
昂威說拉蓬說在后門見你了,說還給他們指了個方向。
他說的時候眼底倒是平靜,不像是質問。
黛羚心里一驚。
“拉蓬?你說那個警察頭頭?哦,我在后門氣,突然就竄出來幾個男人,問我見沒見過有人在那邊,我怕他們追著我不放就隨便給他們指了個方向。”
昂威薄扯了一下,有一下沒一下地挲細鬢角的碎發,“你膽子大,敢給警察指方向,不怕他們拿槍崩你。”
“我一沒犯法二沒得罪他們,他們憑什麼崩我。”
這是實話。
昂威漆黑的眼珠睨著車窗外的斑斕夜,瞳孔一寸一寸浸霓虹,辯不得,“以后不要一個人去那沒有路燈黑漆漆的地方,不安全。”
點了點頭,試探問道,“那個拉蓬是什麼人?看起來大。”
昂威撓鬢角,睨一眼,“怎麼,對他有興趣。”
黛羚搖頭,說那人看起來很兇,在別墅見過一次,跟著阮夫人過來的。
一聽阮妮拉的名字,那人眼神沉了一下,臉孔變得冰冷和森,沒有再說話,也識趣不再問。
車子在一個地方停穩,車窗上響起兩聲清脆的叩響。
昂威冷眸降下車窗,坤達從外探了頭,“爺,夫人在車里等您。”
他大拇指朝一旁指了指,盡頭停著一輛黑轎車,牌子看不清,像是一輛奔馳。
兩道刺目的白向前方,看出去,周圍至幾十號警察,他們匿在大霧之中,像一匹匹狼。
黛羚看清楚這里堆滿了集裝箱,應該是港口某個角落。
Advertisement
昂威渾厚的嗓音嗯了一聲,側拍了拍的背,讓乖乖在車里等他,要不了多久。
他下了車,窺見他臉驟然變冷,立在風中發飛揚,港口一盞巡邏燈柱掃過男人的鬢角,那樣倨傲輕狂的背影,讓人不寒而栗。
坤達給他點了煙,昂威了兩口才抬腳緩緩走向那輛停在盡頭的黑轎車。
接下來的一切聽不見也看不見,只有靜靜等待。
第六告訴,今晚港口那場槍戰,還有出現在酒店后門那個傷的男人,都與他有關。
那輛車門是從里面被踹開的,沒過多久,昂威一臉怒氣下了車,他起伏的口涌著脈噴張的憤懣,從未看他如此怒過,那張沉的臉和猩紅的眼此刻能將世間萬一切撕碎的氣勢。
后漆黑的車,只看清穿著警察制服的阮妮拉,面凝重地靠在一旁,梳著溫婉的發髻,凝眉目視前方,沒什麼溫度。
昂威了坤達過去,走至岸邊,臉是黑的,叉著腰似乎沉了沉氣,“我要知道那艘船在哪里,現在。”
坤達面難,“現在估計已經到了公海,追不回來了,今晚都把人手放到了這邊,那邊只有幾個小兄弟,誰能想到他們會找到存放那艘船的位置,調虎離山之計,我們被暗的人狠狠耍了一把。”
談話之間,又有幾個警察走了上去,拉蓬領頭,昂威似乎在質問他們,他脊背直,氣勢上明顯旁邊那些人一頭,天生的王者風范。
“那艘船什麼時候什麼手續出去的。”他視線冷冷掃眾人。
坤達思索了一下,“正常通關出去的,走的鋼材,阮副署長也不知道這個消息,估計是上面有大老虎開的閘。”
拉蓬也了話,“船是在這邊開火的幾乎同時從東邊出的海,這邊他們放了人引我們上鉤掩人耳目,我們追出去正好中了他們的計,讓我們誤以為他們著了我們的道,沒想到里應外合,他們幾乎配合得天無,那艘船就這樣在眾目睽睽之下開走了,背后這位爺不是普通人,他有咱們行的消息也有上面的人配合,屬實水太深。”
Advertisement
他瞟著昂威和坤達,話語之間有種責怪的意味,“這次的行說好的萬無一失,不然我們也不會這麼賣命,看來不僅阮副署長要遭殃,恐怕下面的兄弟們也要牽連,爺,這次栽了個實在跟頭啊,怎麼收場。”
坤達怒氣沖沖,上前一把揪住拉蓬的領,眼神就能把人殺死,“他娘的你有資格質問爺,說不定就是你們警局的鬼。”
拉蓬塊兒沒坤達大,但氣勢不弱,一雙戾氣十足的眼睛平靜挑釁他,“達爺,這怎麼能算質問呢,你問問你自己,這次行您安排大半,我們聽您指揮,要說紕,怎麼也得從你這查起,您說是不是?”
從他們的只言片語里,黛羚大概提取出了報。
今晚在曼谷港的行,昂威聯合阮妮拉想要引人著道,來個甕中捉鱉,卻沒想到被暗那人識破伎倆,派了人和他們周旋的同時,開走了本被藏起來的一艘船。
猜想,那艘船里有著很重要的東西,或許是這場事件的導火索。
兩人口舌之爭,旁的手下勸阻扭一團。
過海上反的輝,瞧見背對眾人的男人姿匿在半明半暗里,鶴立拔,一言不發,不知在思索什麼。
等來那人再進車,是在半小時后。
這場事件的前因后果不知,但明顯結果不盡人意,不然也不會見到他發這麼大怒,平日只有他耍別人,今日一事,他必定不太舒服。
昂威仰頭靠在椅背,雙叉開來,單手扯松了領帶,呼出一口悶氣,低聲吩咐船叔,回家。
無任何防備,那人默默扯過的手,閉著眼一句話也再沒有說,也讀得懂空氣,沒有煩他。
回了海湖莊園,昂威獨自在后院泳池邊坐著煙,他了多久已經記不清楚,只知道他吻上來的時候已經睡著。
Advertisement
窗紗舞之下,那人強欺而上,從上到下擁住整個,一只手將的脖子托起,那個吻帶著濃烈的侵占和怒意,讓全繃。
他的明明炙熱,但一無以言說的寒意卻包裹全,有些慌,拼命掙扎,就像快要窒息。
“別這樣,我來事了。”嗚咽著推他,男人的膛卻強壯得像一頭牛。
那人霸道咬的耳垂,不理會的反抗,將雙手狠狠在兩側,用撕開了上所有的遮蔽,從上到下刻意的恥痕跡。
黛羚低聲求饒,他卻被泄憤的沖昏頭腦,不管不顧著釋放他下噴薄而出的。
那一夜,他的襯衫都沒褪去,暴戾蠻橫席卷,這個過程就像一場風暴,讓狼狽憤。
結束時,眼角落了一滴淚,他自顧自地去了浴室洗澡,不理會床上的凌不堪。
這是第一次,他毫不顧忌的。
他洗了澡后,將房間里的臺燈打開,他腰上胡圍了一塊白浴巾,頭發和膛上掛著晶瑩剔的水滴,遮住那雙清冷鋒利的眼,和他眼底真實的緒。
他對著床上抱著被子一言不發凝視墻角的黛羚,良久,俯吻掉了眼角那滴淚。
將額前濡的頭發挽到耳后,似乎帶了些歉意的溫,“好了,別哭了,我的錯。”
說什麼也不理會他,他只好為仔細拭了,將重新抱回床上。
后半夜,他似乎又重新恢復了理智,輕輕拍著的背,耐哄睡。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25 章

難以招架,裴總每天都想強取豪奪
【1V1 雙潔 強取豪奪 強製愛 男主白切黑 天生壞種 追妻火葬場】裴晏之是裴家的繼承人,容貌優越,家世極好,外表溫潤如玉,光風霽月,實則偽善涼薄,是個不折不扣的壞種。他從小就感受不到所謂的感情,不會哭不會笑,就連這條命都是拽斷了一母同胞哥哥的臍帶才留下來。裴家人都說他是沒有感情的瘋子,因此把人送到道觀養了十多年。直到他18歲那年斬獲大獎無數,才被裴家人歡天喜地接回來。都以為他會改邪歸正,殊不知,惡魔最會偽裝。*江予棠自幼性格木訥,沉默寡言,是放在人群裏一眼看不到的存在。一次偶然的機會當了裴晏之的私人醫生。都說裴晏之性格溫柔,教養極好。江予棠對此深信不疑。直到兩人交往過程中,他步步緊逼,讓人退無可退。江予棠含淚提了分手。可招惹了惡魔,哪有全身而退的道理。往日裏溫潤如玉的男人像是被惡魔附體,對她緊追不舍,把人壓在牆上,語氣又壞又惡劣,“你要和我分手?換個男朋友……”後來的後來,男人抓著她的手,小心翼翼貼在臉上,嗓音裏滿是祈求,“棠棠今天能不能親一下?”從此以後,上位者為愛強取豪奪,搖尾乞憐。【沉默寡言醫學天才女主X表麵溫潤如玉實則陰暗瘋批偽善涼薄男主】
22.6萬字8.18 17507 -
完結72 章

遲來童話
城南池家獨女池南霜從小千嬌百寵,衆星捧月,是洛城圈內出了名的矜縱任性。 偏偏在二十四歲生日這天,被池老爺子安排了一樁上世紀定下的娃娃親,未婚夫是洛城地位顯赫的謝氏掌權人謝千硯,據說明朗俊逸,只是鮮少露面。 衆人皆道這門婚事佳偶天成,老爺子更是態度堅決。 氣得她當場把生日皇冠扔在地上,放言: “我要是嫁給謝千硯我就不姓池!” 抗婚的下場是被趕出家門,千金大小姐一朝淪落爲街頭商販,自力更生。 在屢屢受挫之際,是隔壁的窮小子宋宴禮多次出手相助。 對方溫柔紳士,品貌非凡,且人夫感十足,除了窮挑不出別的毛病。 相處中逐漸淪陷,池南霜毅然決然將人領回家。 老爺子聽說後,氣得抄起柺杖就要打斷這“軟飯硬吃”小子的腿。 然而柺杖卻沒能落下來—— 窮小子緩緩轉過身來,露出一張熟悉的臉。 “爺爺,”他溫柔地笑,“不是您說,只要我把南霜追到手,這門親事就還算數嗎?” 池南霜:???
24.8萬字8 160 -
完結12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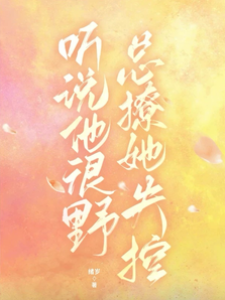
聽說他很野,總撩她失控
【真心機假天真乖軟妹VS假浪子真京圈情種】【雙潔+甜寵蘇撩+暗戀成真+雙向救贖+破鏡重圓+復仇he】 多年前,姜家被迫陷入一場爆炸案中,姜知漾在廢棄的小屋被帶回周家。 這棟別墅里住著一個大少爺,很白很高、帥得沒邊也拽得沒邊。 他叫周遲煜。 第一次見他,他的眼神冷淡薄涼,那時的她十三歲,卻在情竇初開的年紀對他一見鐘情。 第二次見他,她看見他和一個漂亮性感的女生出入酒吧,她自卑地低下頭。 第三次見他,她叫了他一聲哥哥。 少年很冷淡,甚至記不住她名字。 “誰愿養著就帶走,別塞個煩人的妹妹在我身邊。” —— 高考后,姜知漾和周遲煜玩了一場失蹤。 少年卻瘋了一樣滿世界找她,他在這場騙局游戲里動了心,卻發現女孩從未說過一句喜歡。 “姜知漾,你對我動過真心嗎?” 她不語,少年毫無底氣埋在她頸窩里,哭了。 “利用、欺騙、玩弄老子都認了,能不能愛我一點……” —— 他并不知道,十年里從未點開過的郵箱里,曾有一封名為“小羊”的來信。 上邊寫著:周遲煜,我現在就好想嫁給你。 他也不知道,她的喜歡比他早了很多年。 —— 年少時遇見的張揚少年太過驚艷,她才發現,原來光不需要她去追逐,光自會向她奔來。
22.1萬字8 9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