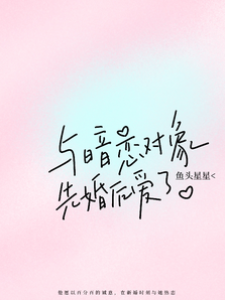《辦公室里不許成精》 第一百四十二章 姐夫
他給了一個極溫的吻。
比雪花更,上的往心里蔓延,在心頭開出一朵紫的小花兒。
而后更多的花朵隨著親吻開放,一路上升,像方才那些的飛舞的泡泡糖,輕盈、亮,好多好多,本數不清,隨著漾的溫暖的春風,輕易開滿了心中原本空虛無的山崗。
蘇唯仰起臉,放松地著他點在臉頰的親吻,原本的一張,兩分忐忑,都隨著心頭花兒的開放,抖落在麻的腰間,再也覺不到。
許是他的親吻一不紊,許是他的懷抱堅實可靠,又或許是這開闊的環境安閑的氛圍,亦或是熱水泡澡讓人疲散的理結果,大腦想了千百種原因都沒想清楚,已經誠實地做出了反應。
吻落在的眼角,淚落他的襟。
唐岑微微一頓,又吻上的眉。沿著眉骨描繪,吻上眉心,重重地,像刻印。而后他將摟了,在他穩重的心跳上,平靜地告訴:“一切都會好的。”
他像安一個小孩兒般,一下一下地順著蘇唯的背脊,直到蘇唯揪住他領的發抖的手,漸漸松了力氣。
黑暗中,低低的泣聲消失了,化作一陣沉默。
像蓄力。
“我的家,要散了。”
良久,蘇唯終于打開了話匣子。
“我父親非常看重我們的學業,如果不是大事,不會讓蘇嘉一請假回來。”
“我父母吵架了許多年,只是這一次,我知道是不一樣的。”
“其實從蘇嘉一離開灣城去外地上大學那天開始,我已經覺到媽媽的改變。還是我媽媽那張臉、那副子,像媽媽從前那般留在家里,但開始學習獨自旅行,開始更激烈地維護自我,的心逐漸輕松,輕松得足以從窗戶飄出去。”
Advertisement
“我是為到高興的...但我原以為,起碼會等到看我出嫁的那一天才會離開,我以為常掛在邊的這件事,會是所執著的東西。”
“所以,我時而避免找到對象,時而又安我有了你。我以為我扯著風箏的那條線,吊著的期,推遲那一天的到來。可最終還是因為我的事,搞砸了。要走了。”
“唐岑,我是不是很自大?以為自己能夠控制住這一切?”
“我是不是很自私?在家里那麼痛苦,我卻想留下。”
蘇唯不再說話,唐岑也沒有開口,只是輕地吻過的頭頂心,將側臉在的額上,給了無聲的支持和安。
夜漸涼,他的懷抱很暖,蘇唯往他心口湊了湊,貪婪地尋求更多。
唐岑終于開口,一字一句地道:“沒有哪個小孩不想...留下媽媽。”
聲音漸漸沉穩:“蘇唯,‘任何可能出錯的事最終都會出錯’,只要你母親錯誤的生活還在繼續,這個結局就是必然...而不是因為你做錯了什麼。”
他的懷抱松開一公分,方便看到他的眼睛,他的眼神溫,聲線更溫:“你已經很努力了,只是...可憐了些。”
酸氣上涌,決堤而下,嘩啦啦流了滿臉。唐岑靜靜地任哭泣,適時地遞上紙巾,在嗆住的時候拍一拍的后背,耐心得本不再像是那座冰山,而是可靠的、不會搖的后盾。
哭累了,蘇小可憐沉沉睡去。唐岑抬了抬被得發麻的肩膀,了幾乎失去知覺的雙,咬牙站起,將心的姑娘藏進被窩里。
一夜溫存,蘇唯睡得安穩,連夢都沒做。
早晨,是被聲音吵醒的。
Advertisement
電窗簾緩緩一層層拉開,發出清淺的軌聲,智能家居的語音伴隨著輕松的音樂緩緩響起:“早上好,現在時間早晨六點整。兩小時天氣晴朗,室外氣溫十二攝氏度,空氣質量優適合晨跑,日出將在6:分發生。接下來是晨早行業要聞速報...”
蘇唯著惺忪的眼睛坐起,確認自己在一張陌生的床上。
沒有兩百平,就是一張普通的兩米寬大床。理論上那個霸總也沒有從被子里鉆出來并發出一聲慵懶的“早安”,而是禮貌地敲了敲房門:“起床了嗎?要跟我去晨跑嗎?”
“稍等!”
蘇唯了個懶腰,真不想離開被窩。
但床邊的運服那麼嶄新漂亮,門外等著的男人更佳,自然是想跟他攜手共同迎接日出,走新的一天的。
海邊跑步,棧橋看日出,回到住做好整理,再喊上剛起床的蘇嘉一吃早餐。蘇嘉一打著呵欠,邊喝橙邊抱怨道:“姐,你今天怎麼這麼早過來了?就為了來蹭酒店的早餐?”
蘇唯臉紅,沒說話。
哪里敢講,是昨晚沒回去。
蘇嘉一倒也沒打算問到底,又去管唐岑:“岑哥,你怎麼也起這麼早?明明昨晚那麼晚還來找我借廁所洗澡。”
蘇唯:“借廁所洗澡?”
“對,”唐岑著蘇唯,“昨晚我去樓下找嘉一借了洗手間。畢竟我那里兩水管壞了,流了一夜,像河一樣,本停不下來。”
蘇唯僵了僵:“沒人問你。”
好在蘇嘉一沒聽出什麼,隨意地關心了唐岑的水管兩句,又講起他今天穿的新款限量版球鞋。天南地北的拉扯了幾句,蘇嘉一道:“姐,我們今天回家嗎?”
蘇唯下意識看了眼唐岑。
Advertisement
唐岑在桌下牽住的那只手用了用力,的心一下子定了。平靜地道:“明天吧,明天我們一起回去。你今天再玩一天,臉上應該就消腫了。”
蘇嘉一抗議:“不出門嗎?沒有娛樂很無聊的。”
“可以把娛樂搬去酒店,”唐岑提議,“或者我讓人接送。我給你一個電話,想要什麼,盡管開口。”
“好耶!”蘇嘉一大聲歡呼。
蘇唯:“你會不會太縱容他了?”
“哪有!”蘇嘉一直接倒戈,“這是岑哥疼我。”
蘇唯無語:“蘇嘉一你昨天還說‘不會被糖炮彈打倒’...”
蘇嘉一:“才不是炮彈!姐姐,我姐夫對我好,你應該支持才對。”
姐夫...嗎?
蘇唯看向唐岑,后者得意地看著笑。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連載900 章

馬甲大佬是個小作精
【文文設定無腦、微玄幻、無邏輯】阮初好不容易從異世穿回來,卻穿到了一個三個月大的小嬰兒身體裡。三個月會遊泳,被阮家認為不祥,被丟到外婆家一養就是十七年。十七年後再度回阮家,抱歉,你們各位都高攀不起本祖宗!……【醋精禁慾係大佬vs萌軟小仙女大佬】初見,她與他夜色朦朧中相遇,她一針紮了他打包扛走。第二次見麵,他把她抓回去丟進蛇堆裡……第三次見麵,他躺在她床上……阮初:“我會救你!”傅冥:“你救我一命,我護你一世……”ps:男主身中劇毒,女主會醫術再加多重馬甲,強強聯合!
123.1萬字8 23559 -
完結412 章

虐死夫人后沈少他瘋了
五年前,一場荒唐的婚姻,將他們捆在一起。十年暗戀,她終于鼓足勇氣,對他說:“我喜歡你,你就不能試試,也喜歡我嗎?”他卻冷言冷語說:“我瘋了才會喜歡你。”可后來,她離開的第一年,他守著她的墳墓,酒醉道:“女人多的是,我不是非你不可。” 第二年:林小冉,我沒有對不起你,你回來好不好 ?第三年:我不信,我不信你不在了,只要你醒來,我們試試。 ...林小冉消失的第五年,沈懷瑾瘋了......
61.8萬字8 562746 -
完結501 章

重生后我和渣男離婚了
夏梓木含著金湯匙長大,二十二歲時下嫁顧淮西。她以為只要她一直跟在他身后,他總會回頭看她一眼。然而,她所有的好,他都不屑一顧。她撞得頭破血流,他也未曾看她一眼。重活一世,她毅然決然提出離婚。這一次,她要為自己而活,珍惜每一個真正在乎她的人。
90萬字8.38 599034 -
完結554 章

人間婚色
那年,十八歲的溫延珵是來餘音家的“灰姑娘”。 這年,餘音二十二歲,從千金名媛淪爲灰姑娘。 一句“六年前的恩還沒報”。他們閃婚了。 餘音一直都以爲他是在報恩,幫她還清了債務,給她母親治病。 殊不知,溫延珵花了六年的時間,摸爬滾打,從晦暗如深,到耀眼奪目,纔敢走到她的面前。 他們之間,他一直都在努力走九十九步。 好似一壺酸梅溫酒,他終究嚐到了甜。 她以爲的先婚後愛,不過就是他“蓄謀已久”卑微的暗戀成真。
98萬字8 4799 -
完結143 章

風箏密語
實習六個月,眼看要轉正卻被關係戶擠走,程鳶走投無路,攔住公司總裁,理直氣壯開口: “我想去你的公司工作,能幫我走後門嗎?” 對方不屑,擡眸看向她,居高臨下:“條件?” 男人穿着筆挺的西裝,身材優越,語氣冰冷。 讓程鳶想起和他領證那天,他冷漠的眼神和現在一模一樣。 她攥了攥拳,鼓起勇氣試探道:“要不,離婚行嗎?” 池硯珩:“……這次算無條件幫你,下不爲例。” -- 父母安排,程鳶大學還沒畢業就懵裏懵懂結了婚。 老公長得帥,愛她寵她,朋友羨慕不已,誇她命好。 只有程鳶知道,她和池硯珩不可能是一路人。 他出身世家,年輕輕輕就坐上了總裁的位置,冷漠、強勢,殺伐果斷。 而她只是個慢熱又社恐的小翻譯。 沒過多久,她就遞上離婚協議,當晚就飛去英國,再沒回頭。 -- 兩年後,程鳶成了業內小有名氣的翻譯。 她越發冷靜、成熟,越發遊刃有餘。 那天,曼徹斯特大雪紛飛,老闆火急火燎把她找來,有個難纏刁蠻的大客戶,非她來翻譯不可。 程鳶頂着風雪闖進包廂,着急忙慌,倏然對上一雙熟悉的眼睛。 她愣在原地。 池硯珩坐在主位,說着只有他們兩人聽得懂的中文。 “我不同意離婚,所以,池太太什麼時候回家?” -- 【小劇場】 公司流傳,那個新來的實習生倒黴透了,ppt被批得一塌糊塗,老闆黑着臉,單獨把她叫去辦公室。 衆人紛紛憐憫,猜測她會不會哭着回來。 直到員工去總裁辦公室送文件。 門推開一絲縫隙,沙發上,池硯珩把人圈在懷裏,吻得意亂情迷。 程鳶被迫承受,雙手抵在他胸口,急忙阻止:“有人!你別……” 扒着門的員工如遭雷劈。 池硯珩無視她的掙扎,笑着偏頭吻下去:“出去,把門帶上謝謝。”
21萬字8 81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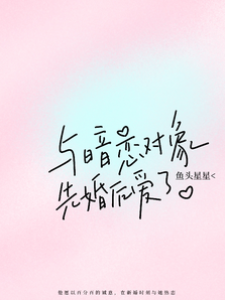
與暗戀對象先婚后愛了
【清冷美人×桀驁貴公子】江疏月性子寡淡,不喜歡與人打交道,就連父母也對她的淡漠感到無奈,時常指責。 對此她一直清楚,父母指責只是單純不喜歡她,喜歡的是那個在江家長大的養女,而不是她這個半路被接回來的親生女兒。 二十五歲那年,她和父母做了場交易——答應聯姻,條件是:永遠不要對她的生活指手畫腳。 _ 聯姻對象是圈內赫赫有名的貴公子商寂,傳聞他性子桀驁,眼高于頂,是個看我不服就滾的主兒。 他與她是兩個世界的人,江疏月知道自己的性子不討喜,這段婚姻,她接受相敬如賓。 兩人一拍即合,只談婚姻,不談感情。 要求只有一個:以后吵架再怎麼生氣,也不能提離婚。 _ 本以為是互不干擾領過證的同居床友。 只是后來一次吵架,素來冷淡的江疏月被氣得眼眶通紅,忍住情緒沒提離婚,只是一晚上沒理他。 深夜,江疏月背對著,離他遠遠的。 商寂主動湊過去,抱著她柔聲輕哄,給她抹眼淚,嗓音帶著懊悔:“別哭了,祖宗。” _ 他一直以為自己與妻子是家族聯姻的幸運兒,直到有一天在她的書中找到一封情書,字跡娟秀,赫然寫著—— 【致不可能的你,今年是決定不喜歡你的第五年。】 立意:以經營婚姻之名好好相愛 【先婚后愛×雙潔×日久生情】
26.1萬字8 9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