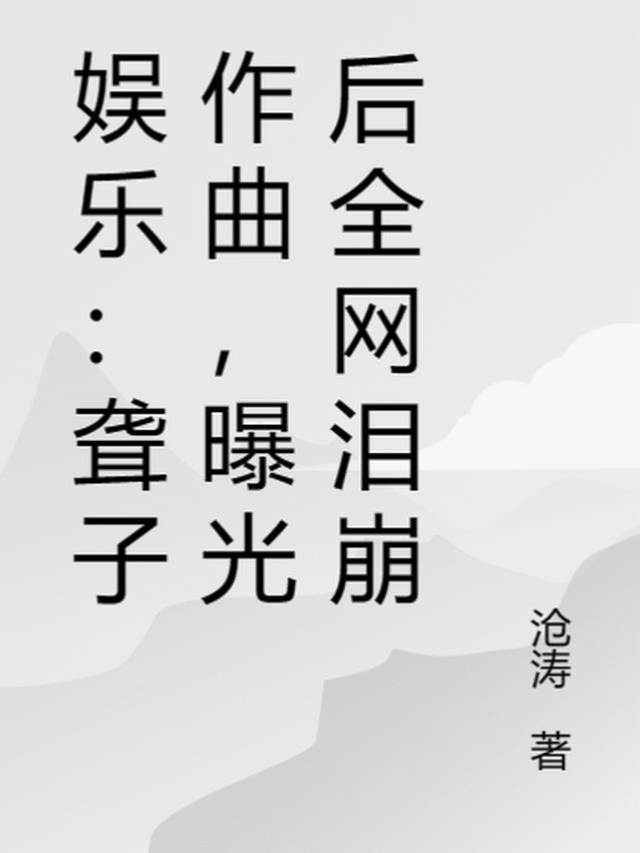《【韓娛】在元氣女團裝可愛的生活》 第2卷 番外 平行世界番外10
電視臺五樓角落似乎無人使用的演藝廳黑燈瞎火。
突然,它靠近走廊,沒有上鎖的小窗被人推開,走廊昏黃燈,映著一個穿著深紅法式格子長的瘦高生影,手利落,作干脆地從小窗翻進來。
獨自一人留在演藝廳里的人,在黑暗中瞪大雙眼,不可思議地看著這一幕。
生穿著高筒靴,靴底的質后跟敲擊木制的地板,空的大廳,回響著規律卻莫名迫十足的腳步聲。
人不由自主屏住呼吸,漆黑的房間,充滿迫的腳步聲,讓覺得誤恐怖片片場。
好在只能模糊看清齊頜短發背影的生目標明確,徑直朝著舞臺上的三角鋼琴走去。
過于詭異的劇實在人凌,林靜妍滿腦子的恐怖鬼腥畫面,悄悄蹲下,輕手輕腳,想要從小門出去。
簡單雜的鋼琴試音后,生手指紛飛間的音樂聲讓林靜妍停下腳步。
清脆亮的鋼琴聲,仿佛從萬籟俱寂的星空中傳出,一又一縷訴說著幽怨孤獨的愁思。
林靜妍好奇抬起頭,在鋼琴上的手機電筒微中,見到那個印象極其深刻的故人,電影靈的原型人,當然,是單方面的印象深刻。
舞臺上的李智允,毫不知道臺下有位意料之外的聽眾。
從外婆帶著年的按下鋼琴琴鍵開始,音樂為表達的出口。
漫無邊際的孤獨迷霧,看不見天地的邊,曾經飛揚的思想如流星怦然墜地,化作一團熊熊燃燒的烈火。
心越蒼涼,琴聲越發激昂,如同一位生命生前最后幾秒的垂死掙扎,樂聲急轉直下的同時,舞臺上方的燈亮起。
李智允停下手中作,轉頭看向舞臺前方,一個著米白西裝的人,拍手的同時,朝著走來。
Advertisement
“你是?”李智允微微瞇眼,有輕度近視,但不戴眼鏡,距離和燈都影響看清眼前人的面孔。
林靜妍滿眼驚喜地坐到舞臺邊:“我們在黎見過,你記得嗎?17年八月的黎下了一場大雨,你在雨里跟另一個戴著頭巾的生通。”
那晚的場面,說是通純屬化,林靜妍覺得更像一方單方面分手,另一方苦苦哀求的狗大戲。
只是暴雨里,其中一個生完致的容,帶著哭腔的說話聲,眼里染力十足的哀凄,一落淚,令人容心碎,仿佛全世界都錯了。
真是一場極悲劇學的電影畫面,那一刻,林靜妍腦子里構思出一出互相拯救卻不容于世的悲劇。
“喔。”李智允想起那晚有人送了一把傘:“謝謝你的傘。”
走到林靜妍邊坐下,音樂沒有平心澎湃復雜的,又開始想談了。
習慣用新的關系短暫告別當下的況,離出來,等冷靜下來后,再重新審視當下的境況。
而關系方便觀察人類,順便跟人吵架,畢竟跟朋友吵不起來,跟陌生人吵架會像個瘋子,找個男友就很方便。
不過李智允前不久才答應Grace會認真對待,之前就沒談過超過一個半月的,半年的挑戰太大。
啊,想來堅持戒煙五天后,再一次煙,Eve應該不會介意的。
于是李智允轉頭問邊人:“你有煙嗎?”
林靜妍點頭,從外套兜里掏出士香煙,見生用牙齒輕輕咬住煙頭,自然地按下打火機。
明亮而微微搖曳的焰火里,輕縹緲的煙霧里,林靜妍注視微微低垂的眉眼。
上之前疏離清冷,傲氣凜然的氣質收攏,很神奇地呈現出云霧一般的模糊飄然,神卻隨意。
Advertisement
當微微仰頭看向時,林靜妍忍不住心臉紅,明亮水潤的眼眸,像一汪靜謐的湖水,卻如漩渦人沉迷,尤其是不經意流的楚楚可憐,人走向,安。
“你似乎在勾引我?”林靜妍發誓,前一分鐘,眼前生的氣質不是這樣的勾人致命。
李智允自然地用手指夾住煙,恢復面無表的狀態:“抱歉,我不是有意的。”
聳聳肩:“為,你知道的,這種眼神十分方便找人談。”
傷時,會下意識微微展脆弱的一面,但李智允其實不太能接自己的弱,慣用偽裝修飾偶爾的脆弱。
那倒也是,林靜妍覺得沒有人能抗住那種猶如霧氣纏繞,漉漉霧蒙蒙的脆弱憂郁,是眼神就得驚人,讓人不自靠近。
李智允沒有太大的煙癮,只是習慣借助煙霧發呆,勉強收拾好心的緒,站起:“謝謝你的煙。”
“對了,方便你的名字嗎?”林靜妍全心籌備新電影工作,沒時間看新聞。
“你可以我Leslie,也可以我李智允。”名字只是一個代號,從不排斥來自原生家庭的韓文名字。
“很高興認識你,我林靜妍,你對拍戲有興趣嗎?”
“沒興趣。”
“我有一部正在籌備的電影......”
只是借傘和煙的聯系,李智允發現徹底被這姐纏上了。
走出演藝廳的路上,林靜妍喋喋不休地嘮叨的電影計劃,吹噓什麼團隊,什麼資金,還夸張地說自己在劇組可以一手遮天。
李智允終于忍不下去:“林小姐,詐騙請提前做好功課吧。雖然我幾乎不看電影,但我接過黎的電影圈。
那地方封建得要死,長就跟人上人似的,最是輕視,你這樣的年紀能在工作里發言就不錯了。”
Advertisement
從來不缺慧眼識珠的人,林靜妍聽說過眼前生在黎電影圈里的故事,趕解釋:“智允,我沒有騙人,我雖然年輕,但我家里有錢呀,我姑姑就是最大的投資方。”
兩人爭執間,李智允推開防彈的待機室,之前在短信里通知他們課程往后推遲半小時。
閔玧琪:“智允,發生什麼事了嗎?”
田玖國:“你剛才哭呢?”
李智允沒有回答任何一個人的問題,他們也沒有追問,因為他們都被后,隨著走進來的人驚呆了。
李智允敏銳察覺他們神的變化:“不會吧,智允難道跟也有接?”
什麼狗屎緣分,離開韓國時帶走了親人的骨灰和唯一的朋友,多年后再次回來,發現遍地都是莫名其妙的“人”。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連載919 章
強勢萌寶:爹地彆自大
傳聞,夜氏總裁夜北梟心狠手辣,殘忍無情。雖然長了一張妖孽的臉,卻讓全城的女人退避三舍。可是,他最近卻纏上了一個女醫生:“你解釋一下,為什麽你兒子和我長得一模一樣?”女醫生擺弄著手裏的手術刀,漫不經心:“我兒子憑本事長的,與你有毛關系!”夜少見硬的不行來軟的,討好道:“我們這麽好的先天條件,不能浪費,不如強強聯手融合,再給兒子生個玩伴……”五歲的小正太扶額,表示一臉嫌棄。
92.8萬字8 28955 -
完結1630 章

重生后,冷冰冰的大佬要把命給我
【團寵+爽文+玄學】前世慘死,重生歸來,戚溪一雙天眼看透世間妖邪之事。起初,戚溪,陸三爺懷里的小金絲雀,嬌氣的要命。后來,一線明星,娛樂教父,豪門大佬……紛紛求到戚溪面前:大師,救我狗命!陸三爺養了個又奶又兇的小嬌嬌,恨不得把自己的命都給她。“我家小朋友,身體不好,別惹她生氣。”眾人:“那個橫掃拳場,干翻全場的人是誰?”“我家小朋友膽子小,別嚇她。”眾鬼:“到底誰嚇誰?不說了,我們自己滾去投胎。”
147.4萬字8.67 559229 -
完結93 章

時光與他,恰是正好
最近年級突然瘋傳,一班那個季君行居然有個未婚妻。 一干跟季少爺自小相識的,打趣問道:阿行,你什麼背著我們偷偷藏了個未婚妻啊?季君行微瞇著眼,淡淡吐出四個字:關、你、屁、事發小立即起鬨的更厲害,大喊道:不否認那就是有咯。 終於,前面那個始終淡定的背影,有了反應。 喲,她耳朵根兒紅了。 文案二:全國高校比賽中,林惜被身穿比賽服的男人捉住,眾目睽睽之下,她黑色毛衣的領子被扯下,露出脖子上帶著的銀色鏈子,還有鏈子上墜著的戒指季君行看著戒指:你他媽戴著我送的戒指,想往哪兒跑?在年少時,遇到喜歡的人——《時光與他,恰是正好》【提示】1、傲嬌小少爺vs學霸小姐姐2、本文小甜糖,敲黑板強調,一切向甜看齊本文半架空,學校、人物均無原型哦——————————接擋小甜糖《黑白世界,彩色的他》,點進作者專欄,趕緊收藏一下吧。 文案:顏晗篇:作為手控的顏晗,一直因為自己常年做菜而有些粗糙的手有些自卑。 因為她一直想要找個有一對完美雙手的男朋友。 好友安慰她,男人的大豬蹄子有什麼好看的。 直到有一天,她在學校外面租的公寓對面搬來的男人來敲門。 顏晗看著他的手掌,心神恍惚。 端起自己剛做好的椒鹽豬蹄問:同學,要吃嗎?裴以恆篇:來體驗大學生活的裴以恆,在學校外面租了套公寓。 起初還好,漸漸,他有些煩躁。 因為對面每天做的飯實在太香了。 終於,有一天他忍不住去敲門。 門打開露出一張白嫩可愛的小臉時,他微怔。 而當她端起手中的椒鹽豬蹄問他吃不吃的時候。 嗯,他要娶她當老婆。
34.1萬字8 46732 -
連載12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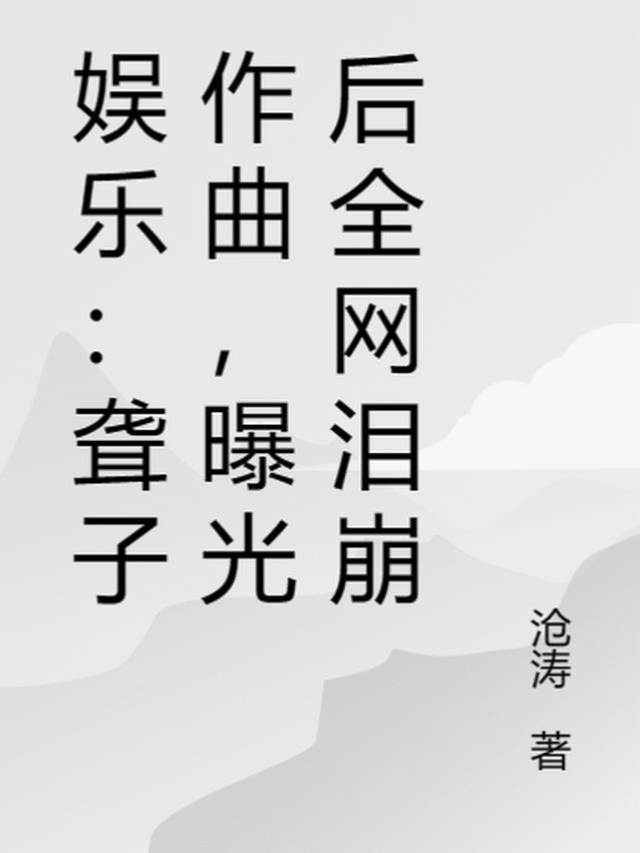
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
微風小說網提供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在線閱讀,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由滄濤創作,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最新章節及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目錄在線無彈窗閱讀,看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就上微風小說網。
23.8萬字8.18 5622 -
完結1634 章

嫁給白月光,溫總寵妻上癮
溫珩是全城姑娘的白月光。所有人都說,楚寧嫁給他,是她單戀成真。婚后溫總寵妻上癮,高調宣布:“我只忠誠于我太太。”唯有楚寧清楚,所有恩愛都是假象。他待她毒舌刻薄,從來都不屑她。他寵她護她,只拿她當刀子使,成為他所愛之人的擋箭牌。離婚那天,她揮一揮手,決定此生再也不見。他卻掐著她的腰逼到角落,“楚寧,你真是這個世上,最薄情假意的女人!”直至她在雨中血流滿地,再一次被他棄之不顧。終于明白……在溫珩心里,她永遠只排第二。楚寧:“嫁你,愛你,我有悔!”后來,他丟下一切為愛瘋魔,“傷了她,我有悔!”
286.7萬字8 5107 -
完結90 章

陸總別虐了,沈小姐帶崽跑路了
和陸霆琛在一起三年,沈薇茗卻得知他已經有了未婚妻。她默默的捏緊孕檢單想要離開陸霆琛,誰料想,他卻想金屋藏嬌。“陸霆琛,牙刷和男人不可共用!”沈薇茗忍無可忍選擇遠走高飛,誰知,陸霆琛像瘋了一樣滿世界找人。他后悔,如果早點告訴沈薇茗這只是一場契約婚姻,結果是不是會不一樣?再見面時,她已不是陸霆琛身后唯唯諾諾的小姑娘。而a市也多了個八卦,據說向來不可一世的陸總被人甩了之后就得了失心瘋。
16.1萬字8.18 477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