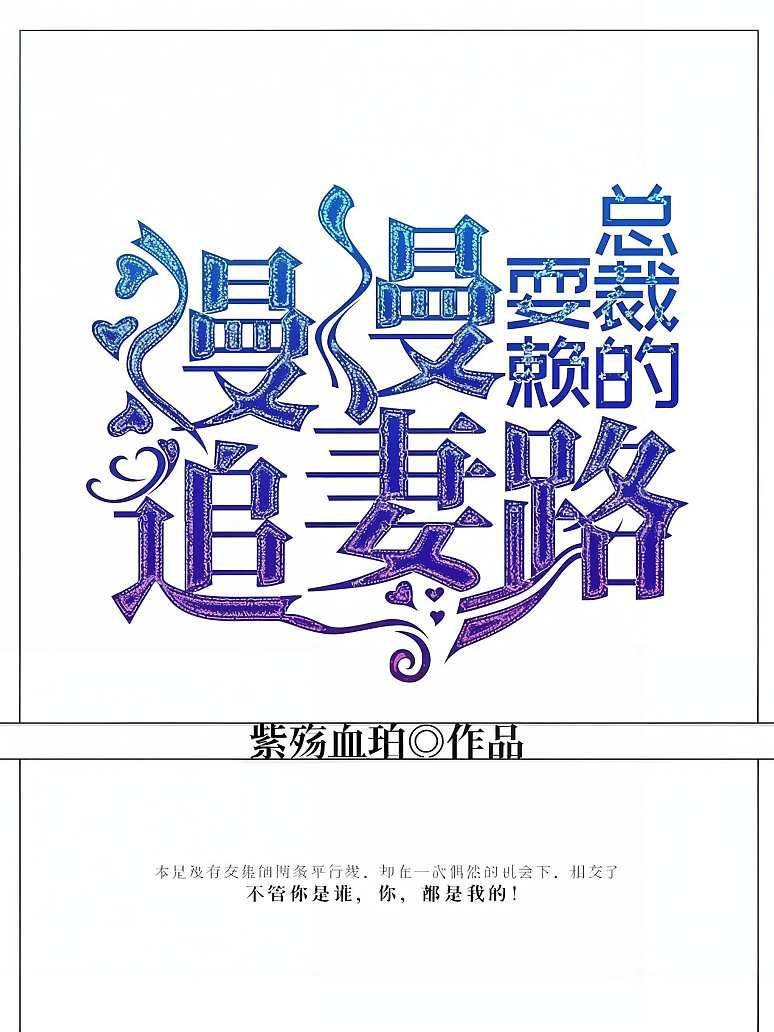《池總,你老婆改嫁了》 第1卷 第30章 你故意的?
“你說沒就沒?”綰不甘示弱,想要推開池硯舟,離開球桌。
但男人紋不,還輕著的臉頰:“總歸總也算和我若有似無地好過一陣,我怎麼舍得讓你汗水白流?”
這話說得綰的臉一陣青,一陣紅的。
“真不是你?”
“雁行又不是只有我一人的。”池硯舟忽然就松開了綰,轉點了煙。
綰也清楚,池硯舟這種大人,是他做的話,他肯定不屑于撒謊。
于是綰心里有了答案,站好之后便和池硯舟道歉。
“抱歉池總,是我誤會了您,您就看在我們若有似無好過的那一陣,原諒我的所作所為。”
池硯舟深吸了一口煙,將煙氣全都輕呼到了綰臉上,然后才說:“這張真是有些多余。”
綰又何嘗不知,池硯舟是在嘲諷用他說過的話,回懟了他。
但眼下,綰顧不得那麼多,只道:“謝謝池總大人不記小人過!”
話音落下的同時,綰邁開長往包廂外走。
池硯舟在的手到包廂門把手時,再次出了聲。
“總,你也看到了,靠維系生意,終歸不可取,提高自能力才是道理。”
Advertisement
綰背對著男人,貝齒將咬得發白。
沒有用換取生意,只是和池硯舟這人解釋這些,好像也沒什麼意義,畢竟他也只是想玩。
所以最后,只輕笑道:“謝謝池總再次賜教。”
然后,就開門大步離去。
江祁年就在包廂門口,看到綰走出來時臉不大好,連忙探頭看了看包廂的男人。
只見池硯舟正站在遠吞云吐霧,眸底滲著冷意,如同一只蟄伏在暗中的危險猛。
江祁年干脆進了包廂,從男人的煙盒里拿了煙,叼在上,邪邪地問池硯舟。
“所以昨天,你在飯局上給詣銘淵和名凱實業有合作意向,是故意的?”
池硯舟沒有正面回答江祁年,只是盯著綰背影消失的盡頭道:“某些人,值是用商換來的。”
*
另一邊,綰從私人會所離開后,直接從黑名單里找到池詣銘的號碼,撥了出去。
池詣銘應該正陪著沈千悅,接到綰的電話時,只是說了一句:“去老地方等我。”
然后,他就簡單利索地掛斷了電話。
于是,綰很快就出現在了宅附近小公園的秋千架邊上。
Advertisement
對,和池詣銘以前經常約會的地方,不是什麼浪漫約會圣地,只是這設施看起來有些破舊的小公園。
在那些被父原配刁難,哥哥姐姐兌,難過到無法睡的夜晚,總是會一個人跑到這個秋千架上呆坐著。
后來池詣銘知道后,也總會在深夜里跑出來陪,然后在后面為推著秋千架、勸解著,直到笑容重新出現在的臉上。
再次坐在這秋千架上,綰慨萬千。
后忽然有人輕推了秋千架一下,綰回頭就看到了池詣銘。
他低頭看綰一眼,又微仰著頭,給綰推著秋千。
昏暗的路燈下,他俊臉上一如既往是與繾綣。
“乖寶,我記得你以前不開心的時候,就喜歡我在背后給你推秋千……”
只是池詣銘剛推了幾下,綰就從秋千架上下來了,還冷著臉對上池詣銘。
“池二,如果你真的念著以前的分,就不要趕盡殺絕。那個項目我和陸對接了很久,眼看就要簽下來了。你突然橫一腳,算什麼意思?”
池詣銘不止沒有否認這一切,還說:“綰綰,我不橫一腳不行啊,陸笙對你機不純,是個人都看得出來。”
大學的時候,就因為陸笙在升旗臺上跟綰告白,池詣銘還和他打過一架,兩人鬧得險些被學校開除。
現在,他又怎麼可能眼睜睜地看著陸笙抱得人歸?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045 章

帝國總裁的寶貝寵妻
遭遇未婚夫背叛,她落魄至極。在她最無助的時候,莫名招惹上了他――魔鬼般尊貴的男子。他是萬人之上的帝國集團總裁,然而,最大的樂趣便是禁錮她,讓她變成和他一樣,冇人愛、冇有朋友、冇人敢親近,唯獨隻有他可以獨自占有。他,不愛便不愛,一愛便成狂,霸道、狂妄又決絕。他護她,護到極致;他寵她,寵到殘忍。他說,“你的身,你的心、從頭到腳每一處都是我的,誰要是敢染指,我便毀了誰。”
218.8萬字8.18 66416 -
完結206 章

嫁給死對頭後,我順風順水順財神
「先婚後愛 蓄謀已久」「男主前期腹黑傲嬌,後期追妻火葬場」大師說嫁給對的人後,她可以順風順水順財神。賀爺爺說嫁給他孫子後,他可以幫她救弟弟。最近點背到姥姥家,又著急救弟弟的遲晚漁不得已向死對頭低頭求婚。可惜,賀頃遲拒絕了她的求婚。遲晚漁怒,“連本小姐你都不要。”“那你要什麼?”“要飯去吧你!”沒多久,打算去哄其他男人的她,被賀頃遲攔住——“遲晚漁,你想反悔?”“這個婚是你求的,我現在答應了,你就別想逃!”
37.3萬字8 19077 -
完結448 章

肆寵嬌柔
“時硯哥,我喜歡你!”滿臉嬌羞的黎笙,喊住了抬腿即將離開的霍時硯。???“黎笙,我不喜歡你,不要做讓人厭惡的事。”嗓音冷漠夾帶著疏離,眼神只是輕輕掃了她一眼,連個正眼都沒有給。???后來這句成了她的夢魘。經常午夜時分驚醒。??她的眼中再無光,成了半入佛門的冰山美人。????時隔三年,再次相遇時。黎笙也只是跟他點頭示意,再無其他。???霍時硯望著保持距離的人兒,不再向從前一樣每次都甜甜地喊“時硯哥… ...
72.5萬字8.18 33090 -
完結12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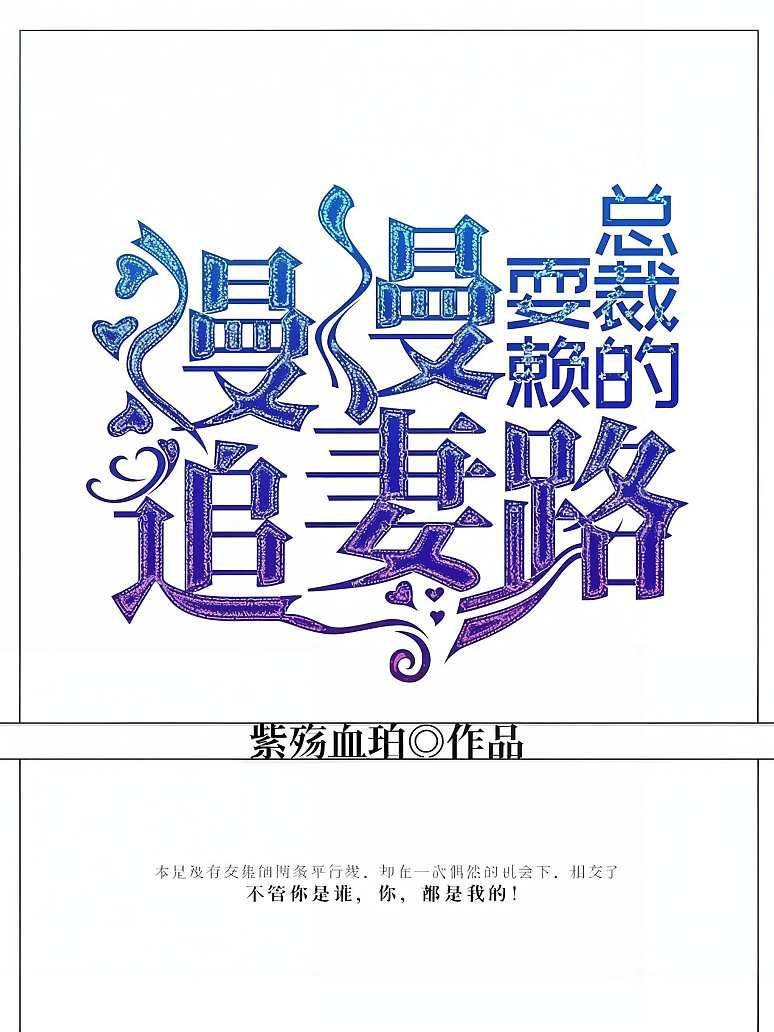
耍賴總裁的漫漫追妻路
本是沒有交集的兩條平行線,卻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事件一:“醫藥費,誤工費,精神損失費……”“我覺得,把我自己賠給你就夠了。”事件二:“這是你們的總裁夫人。”底下一陣雷鳴般的鼓掌聲——“胡說什麼呢?我還沒同意呢!”“我同意就行了!”一個無賴總裁的遙遙追妻路~~~~~~不管你是誰,你,都是我的!
27.3萬字8 17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