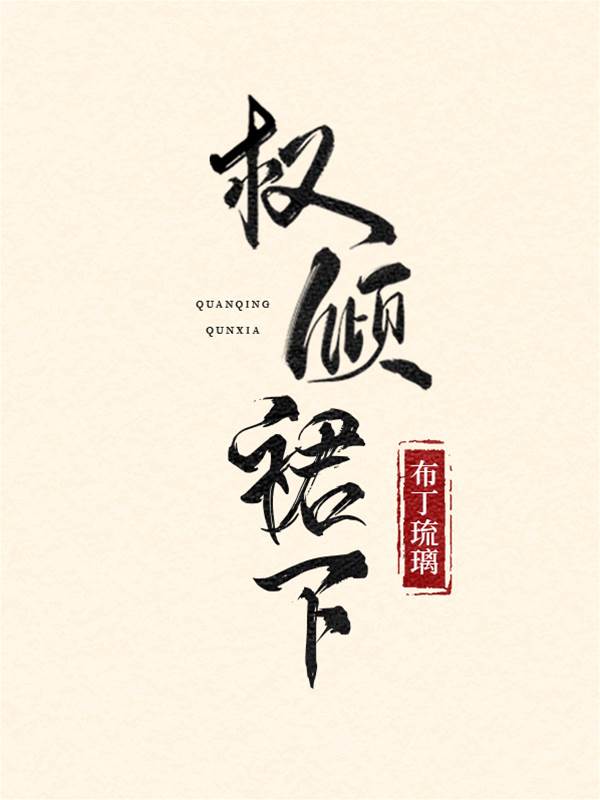《春枝纏》 開心
開心
夜深人靜, 孤男寡,一地。
母們大概也沒有想明白大半夜不睡覺把它們鬧起來是為何,但是趨于本能, 誰也不想被逮著。
所以只見月下郎在追, 在跑,而郎君……郎君找了一塊幹淨的地方, 手裏悠哉悠哉地擺弄著一只大竹簍, 好像在用枯草修修補補。
“……這是什麽況?”南星吭哧吭哧從爬上院牆, 連脖子都使出了全部力氣, 好讓腦袋剛好能卡在牆上,往裏面窺視。
蒼懷蹲坐在一旁,觀察了一陣。
“羅娘子在抓。”
“我沒瞎,我是說羅娘子為什麽在抓?”
蒼懷:“……”
這他哪知道。
別看小,能跑。
羅紈之實在追不了, 才抓到兩只, 回過頭看見謝三郎還坐在墊有大芭蕉葉的回廊上, 朦朧的線照在他的發上、服上,淡化了邊線, 好似和那陳舊的環境融為一。
“沒力了?”謝昀朝笑,善解人意道:“那你歇著,我來。”
羅紈之馬上就把手裏的一放,兩只咯咯直,已是惱怒,登時就翅膀飛撲起想要擡腳蹬, 嚇得羅紈之花容失, 慌不擇路埋頭逃竄,一頭紮進一個結實的膛裏。
驚魂未定, 挨著的腔還在震。
羅紈之拔.出腦袋,仰頭一看。
謝三郎果真在悶笑,他的眼睛微彎,亮如繁星,紅齒白,笑容難抑。
還從未見三郎笑這幅模樣。
好像一下倒回了八、九年,為一個無憂無慮的年郎。
羅紈之從他懷裏退t了出來,了撞紅的鼻尖,把淩的碎發別到耳後,仰面不懷好意道:“到三郎了。”
抓誰也別想有風度!
“好。”謝三郎不不慢把掉落的簍子撿起來,走回到群中。
Advertisement
因為他沒有任何附有攻擊的舉,所以母們在他周圍闊步閑逛,沒有立刻四散而逃。
謝昀慢條斯理用木支起大竹簍,又在木上尾端拴上一從院子角落搜尋到的細麻繩。
這幾下,羅紈之已經看出他是在設置陷阱。
他們事先沒有約定抓究竟是怎麽個抓法,所以現在的羅紈之瞧見謝三郎正大明地設置陷阱,除了目瞪口呆之外說不出他半個“不”字。
“你、你居然上帶有栗米?”羅紈之提邁過去。
設置陷阱需要放上餌。
又不傻,沒有好為何要以涉險?
“沒,我給你帶了幾塊糕,外面的廚子做的,味道很不錯。”
“……”羅紈之眼睜睜看著謝三郎把帕子裏包著的、味道很不錯的糕掰碎撒在竹簍下來,都不等他走開,就有貪吃的從他的手臂下出腦袋,大膽啄食地上的糕碎。
等他走開後,那只就著膽子徹底鑽進竹簍,“咯咯咯”得更歡,好像呼朋喚友。
羅紈之不由心想。
這些肯定還沒嘗過人心險惡,所以沒有防備之心。
若是肯定要三思而後行!
謝三郎坐回原,手裏還拽著那可以牽扯支桿的細麻繩,示意羅紈之也過來歇息。
羅紈之坐下時,裏面那只已經撅著屁埋頭大吃,還有幾只好奇地探頭探腦,還在猶豫。
謝昀把帕子裏剩下的遞到羅紈之面前,溫聲道:“你吃嗎?”
糕點的形狀已經有些被得看不出原來的廓,但上面點綴了紅的果醬可以看出原先是畫有花紋,應該是很致的。
“我想,你這麽晚應該也會了。”
酸甜味鑽進了鼻子,羅紈之不也饞了。
“三郎狡猾。”羅紈之忍不住道。
他這個法子別說是了,就是人都沒幾個逮不住的。
Advertisement
世上趨利附勢的人,都經不起。
羅紈之邊吃著糕,邊看那邊的蠢蠢。
耳邊又聽見謝昀在問:
“若你贏了,你會向我要什麽?”
糕意外地好吃,羅紈之幾口吃完了一塊,又拿起一塊,不假思索地回道:“唔,問三郎能否割,把你手下那陳管事給我,我發現他理得帳都特別清楚,若是不行的話,他那個還在當學徒小徒弟也可以……”
說起這些事,羅紈之就滔滔不絕。
在生意上越得心應手,越野心,恨不得把天下的能人巧匠都收歸“麾下”,讓可以壯大自己的生意。
謝昀隨意應了聲,沒有說好或者不好。
羅紈之瞄了他一眼,三郎好像沒有不高興,只是也沒什麽表。
也是,當著他的面開口要人不太好,以後這樣的事還是來吧。
這時另一只終于在味的食和未知的危險之中選擇了舍求吃,也勇敢進竹簍,跟同伴搶食,現在陷阱裏面已經有兩只了。
再來一只,羅紈之就要輸了。
羅紈之把糕咽了下去,時不時瞟向謝昀的手指,而他巋然不。
宛若手裏牽著的不是簡陋陷阱,而是至關要的大事。
羅紈之盯著那些,在心裏一遍遍道:“別上當、別上當。”
但母沒能和心意相通,又一只按耐不住,扭著屁了進去,“砰”地一聲,竹簍倒下,抓住了這三只貪吃。
時機恰到好,沒有一只也沒有多一只,剛好讓他贏。
勝負落定,羅紈之不由一嘆。
“是三郎贏了。”
謝昀道:“願賭服輸?”
“嗯……嗯?!”羅紈之目訝然,沒有料到謝昀忽然傾靠近。
不但如此,他的手穿過的發,指腹過的臉頰,而後五指微張,掌腹在的頸後,指.尖輕扣在咽上。
Advertisement
沒有握,也讓不能再退後躲避。
臉離得很近,羅紈之都能嗅到他上除了沉水苦香還有淡淡的千金釀。
三郎喝了酒。
喝了酒,他會比尋常更放縱。
羅紈之忍不住閉上了眼睛。
“為何閉上眼?”謝昀忽然問。
聽見聲音羅紈之又睜開雙眸,的眼睛裏充滿疑,讓謝昀不又出了笑意。
“你以為我離著這麽近是要吻你嗎?”
難道不是嗎?
羅紈之知道自己故意戲弄了謝三郎幾次,所以這次謝三郎讓賭輸了。
輸了,謝昀又靠他這麽近,若不是這個原因,還有其他?
謝昀著,一字一字緩慢道:“我想要你吻我。”
他贏了,所以可以讓做任何事。
羅紈之以為自己聽錯了,但是謝昀的眼睛盯著的,又著的眼睛,無聲卻也在催促。
羅紈之愣了下。
不知道他們這樣算什麽。
既不是奴骨的煙花,他也不是尋歡作樂的紅塵客。
除此之外。
親吻不該是相之人才能有的親嗎?
他想要這個吻,似是在要的,仿佛如此能夠證明切切實實為他了心。
羅紈之只遲疑了片刻,就把了上去。
謝昀為男子,卻也有著兩片的瓣,而且他的味道很幹淨,也很好聞,即便沾上了酒氣,也不熱.辣沖鼻,反而能與他上的氣息融合一種更加醉人的味道。
價值不菲的千金釀與舉世無雙的謝三郎,這就好比豆腐腦澆上了桂花,是錦上添花,也是上加。
若擱在一年前,羅紈之是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有朝一日會嘗到謝家那位高貴如謫仙的謝三郎的味道。
其實羅紈之也不知道如何吻,還是照著上一次醉吻時依葫蘆畫瓢,把他的兩瓣砸吧幾個來回,就好像吮人蕉花。
Advertisement
謝昀把“隨你”二字貫徹到底,任由小貓般把他的都得.漉漉。
已了秋,晚間也起了輕風,樹葉在兩人頭頂簌簌響,明明是個涼津津的秋夜,但羅紈之卻熱出了一背的薄汗。
覺得燥.熱,很想扯開襟,但這可絕非個好主意。
于是偏過臉,轉而想要後退,只是後頸上的桎梏沒放開,被在了原地,只能問:“……怎麽了?”
“就這樣?”
羅紈之從謝三郎的聲音裏聽出不滿足。
“不是這樣嗎?”辯道:“你上回就是這樣做的!”
原來羅紈之都是學他的,的任何舉、反應都出自于他。
這個想法甫一冒出,就好像沸騰的油鍋不斷拱起了熱泡。
謝昀笑道:“對,也不全對。”
羅紈之剛生出疑,謝昀就主了上來,瓣靠,嗓音既低又啞地重新教道:“先張開。”
羅紈之半信半疑地稍啓,在這一刻還不知道自己在引狼室。
下一瞬謝昀的舌尖就順利抵了進來,羅紈之再要反悔也無力回天。
只能驀然睜大眼睛,任由自己溫暖的腔.壁被細致繾綣地掃。
重新認識了何為親吻,也認識了迷意的謝三郎如何大膽、肆意。
如春風融化了冰雪,溫暖、潤,到都泛著熱.,騰著迷霧。
羅紈之覺得自己的全都要化了。
眼前溟濛一片,像是後仰倒水中,如浮萍般無助的隨著湧的水浪起落。
謝昀居高臨下吻住,讓毫無招架之力,那如狂風驟雨的深吻仿佛讓窺探到了一個不一樣的謝三郎。
不安地扭著腰,挪著地方,一方面是憋氣讓肺部承不住,另一方面是坐的地方還有他先前修框剩下的枝條,凹凸不平地被坐在了.下。
謝昀吻了吻的邊,空問了句:“怎麽了?”
羅紈之慌地用雙手用力抵住他起伏不定又實的膛,“坐、坐的地方不平,難……”
謝昀垂眼掃了一下,忽然把羅紈之架了起來,讓坐在自己的上。
“這樣便好了。”
好?哪裏好了?
羅紈之低下頭,和謝昀臉對著臉,大眼瞪大眼。
“這樣坐,不好吧?”
板直腰背,努力把自己的撐起,好讓不至于落在他上。
“你那日就是這樣主坐在我上。”謝昀的一只手扶在的後腰,另一只手依然搭在的後頸上,把了下來。
是一個細心呵護的姿態,也是一個全然控制的狀態。
不等羅紈之因回憶生出赧然,謝昀已經仰起臉,再次撬開的,深地吻了進去,這次羅紈之的香舌也慘遭俘獲。
羅紈之的骨瑟瑟發抖,卻并非是因為寒冷,而是因為裏湧出t的未知熱.,仿佛要從裏至外摧毀的意識。
驚恐這種變化,但又無力掙開,只有無意識地輕哼溢出嚨,反倒像是人的鼓勵,換來的是三郎更加溫強勢的親吻。
呼吸疊,聲聲急促。
羅紈之趁他.息的間隙,抓時間提出抗議:“這樣坐也不舒服!”
謝昀低頭看的手,的手出袖子,手背因為用力而繃起三掌骨,纖細脆弱,但卻還妄想以此撐起自己的,或者推開他的子。
“為何?”
羅紈之的臉已經夠紅了,現在連脖頸都泛紅,像是枚通紅的果子,豔滴。
往下飛快看了眼,又擡起淚霧蒙蒙的眼睛著他無聲控訴。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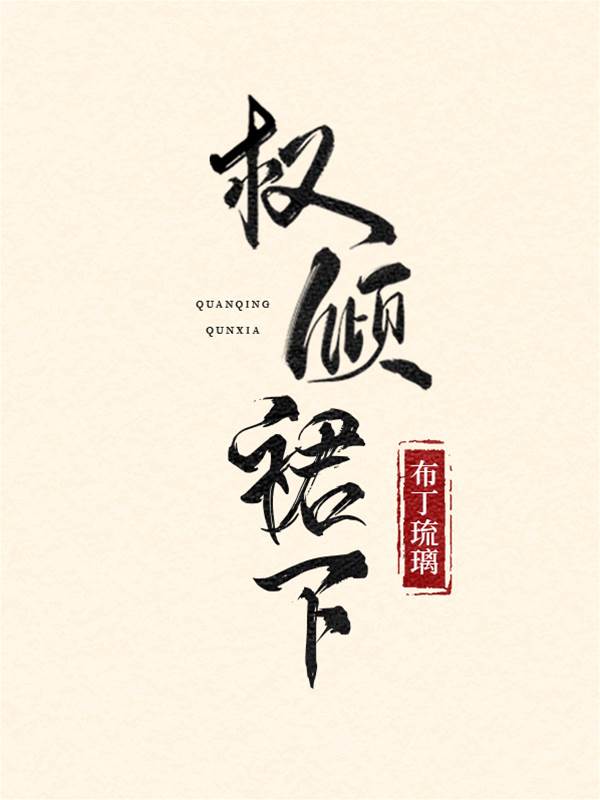
權傾裙下
太子死了,大玄朝絕了後。叛軍兵臨城下。為了穩住局勢,查清孿生兄長的死因,長風公主趙嫣不得不換上男裝,扮起了迎風咯血的東宮太子。入東宮的那夜,皇后萬般叮囑:“肅王身為本朝唯一一位異姓王,把控朝野多年、擁兵自重,其狼子野心,不可不防!”聽得趙嫣將馬甲捂了又捂,日日如履薄冰。直到某日,趙嫣遭人暗算。醒來後一片荒唐,而那位權傾天下的肅王殿下,正披髮散衣在側,俊美微挑的眼睛慵懶而又危險。完了!趙嫣腦子一片空白,轉身就跑。下一刻,衣帶被勾住。肅王嗤了聲,嗓音染上不悅:“這就跑,不好吧?”“小太子”墨髮披散,白著臉磕巴道:“我……我去閱奏摺。”“好啊。”男人不急不緩地勾著她的髮絲,低啞道,“殿下閱奏摺,臣閱殿下。” 世人皆道天生反骨、桀驁不馴的肅王殿下轉了性,不搞事不造反,卻迷上了輔佐太子。日日留宿東宮不說,還與太子同榻抵足而眠。誰料一朝事發,東宮太子竟然是女兒身,女扮男裝為禍朝綱。滿朝嘩然,眾人皆猜想肅王會抓住這個機會,推翻帝權取而代之。卻不料朝堂問審,一身玄黑大氅的肅王當著文武百官的面俯身垂首,伸臂搭住少女纖細的指尖。“別怕,朝前走。”他嗓音肅殺而又可靠,淡淡道,“人若妄議,臣便殺了那人;天若阻攔,臣便反了這天。”
52.5萬字8 22512 -
完結967 章
神醫王妃她拽翻天了
秦語穿越成炮灰女配,一來就遇極品神秘美男。 秦語道,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因為相遇是妹妹陷害,大好婚約,也不過是她的催命符。 秦語輕笑:渣渣們,顫抖吧! 誰知那令人聞風喪膽的燕王,卻整天黏在她身邊.
170.1萬字8 23384 -
完結161 章

太子妃實在美麗
尚書府的六姑娘姜荔雪實在貌美,白雪面孔,粉肌玉質,賞花宴上的驚鴻一現,不久之後便得皇后賜婚入了東宮。 只是聽說太子殿下不好女色,弱冠之年,東宮裏連個侍妾都沒養,貴女們一邊羨慕姜荔雪,一邊等着看她的笑話。 * 洞房花燭夜,太子謝珣擰着眉頭挑開了新娘的蓋頭,對上一張過分美麗的臉,紅脣微張,眼神清澈而迷茫。 謝珣:平平無奇的美人罷了,不喜歡。 謝珣與她分房而睡的第三個晚上,她換上一身薄如蟬翼的輕紗,紅着臉磨磨蹭蹭來到他的面前,笨手笨腳地撩撥他。 謝珣沉眸看着她胡鬧,而後拂袖離開。 謝珣與她分房而睡的第三個月,她遲遲沒來, 謝珣闔目裝睡,等得有些不耐煩:她怎麼還不來撩孤? * 偏殿耳房中,姜荔雪正埋頭製作通草花,貼身宮女又一次提醒她:主子,太子殿下已經到寢殿好一會兒了。 滿桌的紛亂中擡起一張玉琢似的小臉,姜荔雪鼓了鼓雪腮,不情願道:好吧,我去把他噁心走了再回來… 窗外偷聽的謝珣:……
25.7萬字8 769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