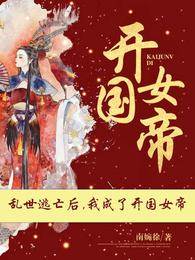《籠中雀她渣了瘋批皇帝》 第4卷 第一百七十三章“朕要召幸你”
姜姒驚愕莫名,惶然道,“陛下!”
許鶴儀手便去解腰間绦,姜姒慌忙阻攔,聲音已飽含乞求,“陛下!”
許鶴儀結微,“阿姒,你不愿?”
姜姒睫輕,想到顧念念方才還譏諷自己水楊花,可一向謹規守矩,何曾水楊花。
姜姒別過臉,聲音發抖,“我已是有夫之婦,陛下......”
許鶴儀掰正了的臉,瞳孔微沉,暗啞的嗓音克制著的暗涌,“你是孤的良媛,你已然忘了嗎?”
姜姒心中一震,他說的是“良媛”,稱的是“孤”。他這樣說話,倒似又回到東宮冊封那日。
他待好過,也有許多年。
許鶴儀眼尾泛起薄薄的紅,輕嘆道,“你跟朕十一年,朕從未過你,如今十分后悔。”
后悔又怎樣,如今是萬般不可。
姜姒費力企圖掙躲開,他卻單手扣牢,將的雙手牢牢箍在地上。
姜姒記得,許鶴儀曾給過一個十分溫的吻,便認定許鶴儀是十分溫的君子。
記得許鶴儀孤立在那棵高高的梨樹下,回眸沖桀然一笑,便認定許鶴儀是梨花一般清冷高潔的人。
他的眉眼與許之洐有幾分相像,原以為脾總是不同的。如今看來,他不過是比許之洐多了一層偽裝罷了。
他的聲音冷了下來,“阿姒,這是召幸。”
姜姒愕然著他,眸中便滾出淚來。
“朕要召幸你。”
喃喃問道,“陛下還是當年的大公子嗎?”
許鶴儀凝視著,輕而易舉便將的三重衫扯開,淡淡道,“朕是天子。”
“你若不是跟他到了燕國,早便是朕的妃嬪了。”
姜姒潸然淚下,“陛下心里,也認定姜姒是那樣的人吧?”
他手中一頓,“什麼人?”
Advertisement
“姜姒從東宮出來時,被褫奪了封號,不久便淪為了奴籍,在軍中盡欺辱。后來在西安/門外,被當眾剝了裳。蒙定國侯不棄,愿意護姜姒周全,求陛下給姜姒留一點面。”
“你在怪朕沒有護你。”
“不,我只想告訴陛下,姜姒已經十分骯臟,恐污了陛下龍。”
許鶴儀著姜姒,眸愈發深沉,“你方才問朕,如何才能不殺許之洐。”
他一頓,“倒不是完全沒有辦法。”
姜姒心里大約猜到他要說什麼,眼淚便似斷珠一般順著臉頰淌了下來。
“你留在他邊做朕的眼睛,仔細盯住他的一舉一,但若有任何不軌之心,朕便再不留他。”
實在諷刺。
最初是許之洐要回東宮做眼睛,如今幾年過去,許鶴儀又要留在燕王邊做眼睛。這世上除了裴君,再沒有人真心待自己。
這十九年,活得像個笑話。
一時失了神,茫然道,“可我已是定國侯孀,無論如何都不會再留在燕王邊。”
他的聲音亦是毫無半分愫,“巫蠱之禍是謀逆重罪,許之洐翅難逃。”
姜姒強迫自己平靜下來,“可燕王不曾僭越呀!”
“你自己思量,但今日的召幸無論如何都免不了了。”
許鶴儀說罷,已推上的抱腹,腰間的朱雀印赫然在目。
他的手在上肆意勾畫挲,他是天子,是帝王,他的召幸,姜姒不敢反抗。
姜姒咬牙忍。
想起顧念念大婚那一日,趙長姝命自己去云樓守夜。就跪在床榻之畔,那時云樓春旖旎,顧念念溫聲浪語。
那時心里苦不可言。
這麼多年過去,當真被許鶴儀召幸了,亦是苦不可言。
許鶴儀的眼眸漆如點墨,似乎帶著一慍怒,“被朕召幸,竟令你如此痛苦麼?”
Advertisement
姜姒別過臉去,他偏偏要的下頜,正視自己,“回朕。”
姜姒聲音發抖,“我不是陛下妃嬪,不該被召幸。”
許鶴儀的目驟然變得冷漠無比,“天下子,皆可為朕的人,有何該與不該?”
姜姒再次別過臉去,不愿再去看他。
跟在許鶴儀邊十一年,日日相見,竟看錯了他。
一時心如刀割,悲不自勝。
抓了厚厚的地毯。
的眼淚已然決堤而出,從前的尊重與護,原來都是假的。
他們許家的男子,皆是如此麼?
只不過有的善于偽裝,裝作無無求,芒寒正的模樣。
有的不屑于偽裝,正大明地腹黑狠。
不,也并非全然如此。
單從建始十一年三月宮變來看,許鶴儀又豈是純良君子。
再細想來,善于偽裝的,是滿腹的謀算計。
那不屑偽裝的,里卻尚有一顆良善之心。
如今許鶴儀為帝三年,早已不是當初那個克制忍的謙謙君子了。
怪不得世人皆攀權附貴,權力真真兒的能將人改變得面目全非。但若一朝得勢,實在要比那不屑偽裝的更為可怖。
也許他從都不是君子。
是自己識人不清,還是他太會偽裝,姜姒不知道。
八歲那年。
踮起腳尖手去摘梨花,可梨樹太高,夠不著。
仰著小腦袋還兀自發著愁,十八歲的許鶴儀將抱起。手摘下最歡喜的一朵,爛漫梨花,簪于髻上。
那時許鶴儀問,“阿姒,你為何喜歡梨花?”
笑得眉眼彎彎,大聲說道,“因為梨花最干凈呀!”
那一年,許鶴儀也不過剛剛弱冠。氣度高華的年了的腦袋,良久才說,“阿姒應該生活在一個干凈的地方,那里開滿梨花,也會有一個人陪著阿姒。”
Advertisement
小小的姜姒用腦袋蹭著他,“大公子會陪著阿姒嗎?”
他微笑著看著,卻再沒說什麼。
那時的姜姒太小,看不懂他眼中的緒。
姜姒閉上眸子,多年來心中對許鶴儀的敬與,已然轟塌,四分五裂。
喃喃道,“陛下再也不是姜姒心中的大公子了。”
許鶴儀一頓,挲著的臉,目森然,一言不發。
是不是從前的大公子,又有什麼所謂呢?
他淡笑一聲,片刻
從前的子只屬于許之洐,如今......如今真應了顧念念那句“水楊花之人”。
許久,他總算翻仰到一旁。見子發抖,目空,許鶴儀起了,“你放心,今日召幸不會計彤史,無人知曉。”
姜姒攏裳背過去,兩行清淚過臉頰。
他雖面清冷,但見凌地蜷一團,便想起了那個五歲時被他親手屠戮了父母親人的小孩。
他對向來全是利用,如今連的子也強要了來。
一時心里有些不忍,但不忍也不過薄薄幾分罷了。
到底是輕嘆一聲,“朕方才與你說的事,你自己抉擇,但朕不會給你們太多時間。”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387 章
腹黑毒女神醫相公
冬暖故坐著黑道第一家族的第一把交椅,沒想過她會死在她隻手撐起的勢力中.也罷,前世過得太累,既得重活一世,今生,她只求歲月靜好.可,今生就算她變成一個啞巴,竟還是有人見不得她安寧.既然如此,就別怨她出手無情,誰死誰活,幹她何事?只是,這座庭院實在沒有安寧,換一處吧.彼時,正值皇上爲羿王世子選親,帝都內所有官家適齡女兒紛紛稱病,只求自己不被皇上挑中.只因,沒有人願意嫁給一個身殘病弱還不能行人事的男人守活寡,就算他是世子爺.彼時,冬暖故淺笑吟吟地走出來,寫道:"我嫁."喜堂之上,拜堂之前,他當著衆賓客的面扯下她頭上的喜帕,面無表情道:"這樣,你依然願嫁?"冬暖故看著由人攙扶著的他,再看他空蕩蕩的右邊袖管,不驚不詫,只微微一笑,拉過他的左手,在他左手手心寫下,"爲何不願?"他將喜帕重新蓋回她頭上,淡淡道:"好,繼續."*世人只知她是相府見不得光的私生女,卻不知她是連太醫院都求之不得的"毒蛇之女".世人只知他是身殘體弱的羿王府世子,卻不知他是連王上都禮讓三分的神醫"詭公子".*冬暖故:他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欺他辱他者,我必讓你們體會
149.1萬字8.18 75123 -
完結139 章

錦衣之下
雨點打得她頭頂上的蕉葉叮咚作響,甚是好聽,胖貓蹲她肩膀上瞇著眼聽。 雨滴順著蕉葉淌入她的衣袖…… 她仰頭看向陸繹移到自己頭頂的青竹油布傘, 心中不禁有點感動,這位錦衣衛大人總算有點人情味了。 “這貓怕水,淋了雨,怪招人心疼的。” 陸繹淡淡道。 胖貓哀怨地將陸繹望著,深以為然。 “……” 今夏訕訕把貓抱下來,用衣袖替它抹了抹尾巴尖上的水珠子, 把貓放他懷中去,忍不住憋屈道, “大人,您就不覺得我也挺招人心疼的麼?” 他沒理她,接著往前行去。 傘仍遮著她,而他自己半邊衣衫卻被雨點打濕。
42.9萬字8 12926 -
完結690 章

穿越后被迫登基
一朝穿越,葉朔成了大周朝的九皇子。母親是最得寵的貴妃,外祖父是手握重兵的鎮國公,他剛出生就一躍成為了最熱門的皇位爭奪者前三,風頭直逼太子。最關鍵的是,母親同樣有奪嫡之念。寵妃+兵權+正直壯年的皇帝,這配置一看就是要完,更何況,他前面還有八個…
106.4萬字8 8694 -
完結181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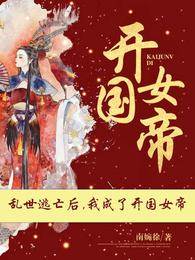
亂世逃亡后,我成了開國女帝
◣女強+權謀+亂世+爭霸◥有CP!開局即逃亡,亂世女諸侯。女主與眾梟雄們掰手腕,群雄逐鹿天下。女主不會嫁人,只會‘娶’!拒絕戀愛腦!看女主能否平定亂世,開創不世霸業!女企業家林知皇穿越大濟朝,發現此處正值亂世,禮樂崩壞,世家當道,天子政權不穩,就連文字也未統一,四處叛亂,諸王征戰,百姓民不聊生。女主剛穿越到此處,還未適應此處的落后,亂民便沖擊城池了!不想死的她被迫逃亡,開
238萬字8.18 16115 -
完結323 章

醫妃仵作鬧翻天
她出身中醫世家,一朝穿越,卻成了侯門棄女…… 從此走上了不一樣的道路。 她聞香識藥,一手銀針,技驚四座,剔骨剖腹怒斥庸醫,讓蠅營狗茍大白天下。 玉手纖纖判生死,櫻桃小嘴斷是非,誓讓魑魅魍魎無處遁形…… “姑娘?何藥可治相思疾?” 某男賴在醫館問道。 秦艽撥出剖尸刀,“一刀便可!王爺要不要醫?” 某男一把奪下剖尸刀,丟在一邊,“還有一種辦法可治!只要你該嫁給我就行。” 秦艽瞪著他魅惑的臉龐,身子一軟……
58.4萬字8 6881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