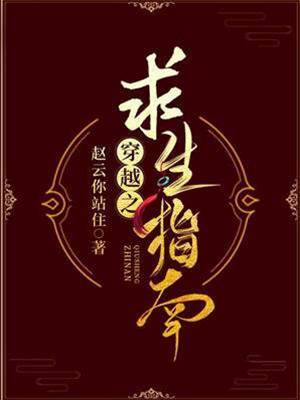《重生之嫡女不乖》 第325頁
小皇帝了親,理論上就可以親政了,攝政王會不會愿意將手中的權jiāo出來,太后會不會趁機將蘭家的兒選為皇后,都是他要防范的事qíng。
韓世昭輕聲地稟報,“蘭家那邊早就鉆網中了,只等陛下想何時收網,是私賣賜品,就足夠將其貶為庶民了;攝政王那兒,倒是一派平靜,王府里也同平日一般,并未有過多員出。”
難道皇兄對權勢真的沒有興趣?小皇帝微微瞇了瞇眼睛,出修長的食指,在案上輕輕敲了敲,“得讓皇兄盡早表明立場了。”說著笑了笑,“有些事qíng,還是讓母后出面比較好。”
提及太后,小皇帝的眸更沉了些,他的母妃,如今還不知在天涯海角,他為人子,如何能讓太后逍遙法外?
小皇帝jiāo待了韓世昭一些近期的事務之后,便擺駕去了慈寧宮。
太后正在替他看畫像,不過太后手中的畫像,都是未來的皇后人選。太后含笑道:“皇兒你自己也來瞧一瞧,看誰最你眼?”
“母后替兒臣挑便是了,兒臣相信母后的眼。”
太后滿意地瞧著小皇帝笑了,卻不說看中了誰,將畫卷jiāo給魏公公,問起他今日的起居。小皇帝恭順地一一作答,然后提到今日來此的目的,“今日皇兄同兒臣議了一回國政,皇兄直言兒臣還是略為稚了,不足以服群臣。兒臣的確是如此覺得,因此兒臣打算,大婚之后,還是由皇兄主理朝政,待兒臣掌握了臣之前,再行親政。”
太后臉上的微笑頓時凝住,沉聲問,“這是皇兒你自己的意思,還是攝政王的意思?”
小皇帝遲疑地道:“是皇兄建議的,兒臣也覺得有道理。”
Advertisement
太后的口憋了一氣,可是見小皇帝俊朗的臉上還有一團稚氣未褪,慒慒懂懂的,忽然覺得,他有這項認知,也是有好的,只是,攝政王必須除去了,小皇帝已經年,對方一定會有所行,必須先發制人。于是太后便笑道:“皇兒心中有算便好。”
母子倆又說了一話,小皇帝才擺駕回宮。待小皇帝一離去,太后立即喚來了魏公公,如此這般地叮囑一番,“切記!必須雙管齊下!”魏公公輕聲應下,退出去辦差。
次日一早,良太妃就將攝政王宣了的宮中,著聲音道:“太后……手中有了當年母妃對付端妃的證據……皇兒,咱們不能等了,必須……必須將小皇帝拉下龍椅。”
攝政王只是微微地蹙了蹙眉,淡漠地道:“母妃你想得過多了,曹清儒如今心智如同孩,葛太醫早已經不見蹤影……”
“葛太醫在太后的手中!”良太妃失控地了起來,“若是讓宗人府給證實了,母妃會怎樣,你應當很清楚!”
攝政王這才正凝神,仔細思索起來。若是當初被先帝發覺了,要如何置,全憑先帝一句話,可輕可重;但若按著律法來置,母妃的封冊就會被收回,貶為庶人,終在宮中服苦役,因而他不能不謹慎。但若說到謀位,攝政王還真沒想過。以前沒有立太子的時候,是有過幻想,聽聞立皇弟為太子,他也有過怨氣,但他不是一個喜歡與天抗命的人,謀反這種事,功的可能遠遠小于失敗,一個不慎,就會臭萬年。
況且,誰都不知道,立儲圣旨頒下之后,先帝曾找他促膝長談過一宿,指出他xing格上和行事上的幾個短,明確地告訴他,正是這些缺點,使他只能為相,不能為王。他自就崇拜父皇,盡管萬分不甘,卻仍是努力調整qíng緒,想當一名曠世賢臣,誰知兢兢業業到如今,竟被bī到這個份上。
Advertisement
良太妃見兒子遲遲不表態,急得再三催促,攝政王最后卻只給了一句話,“容孩兒再仔細思量思量。”
攝政王回到府中,就讓侍衛將王妃請到了前院書房。前院里的布署是最嚴的,攝政王妃知道王爺必定是有極重要的事要與商量,忙收拾打扮停當了過來,見到王爺一副郁結于心的模樣,心中就打了一個突,陪著小心問道:“王爺,宣臣妾來有何事?”
攝政王拉著王妃坐到自己邊,將母妃的話原原本本地告知。攝政王妃沉默了片刻,才開口問道:“那王爺打算如何呢?”
“我也不知。”攝政王擰著眉頭,“這些年我雖也在朝中培植了人脈,只是卻沒到可以篡位的地步,輕率行事,只會讓整個王府一夜顛覆。可是,我又不能置母妃不顧。”當年的事,他最先沒有參與,但后來知曉了,卻也沒有反對和阻止,“況且,母妃若是定了罪,我也……”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攝政王妃也覺得為難,只能笑著安道:“時辰不早,不如王爺先回后院用膳,總不急于這一時,陛下縱使明日便親政了,想將朝政理順,沒個兩三年,是不的。況且,不是說端妃娘娘的脈案都銷毀了麼?只憑一名潛逃的太醫的供詞,難道就能將母妃罪?咱們徐徐圖之,想辦法將太后手中的證據給毀了,只憑太后的言辭,是不能給母妃定罪的。”
攝政王聽聞之后,覺得頗為有理,便與王妃一同回了后院。才進二門,就有丫鬟喜氣洋洋地盈上來,發覺王妃也在,小臉上的笑容就是一僵。王妃眉頭一挑,向著夫君道:“孔孺人子有些不慡利,我替宣了太醫。”然后又朝丫鬟淡聲道:“太醫是如何說的。”小丫鬟只得小聲稟道:“太醫說,是脈,有一個多月了。”
Advertisement
攝政王妃的眼瞼就垂了下來,幾年未曾有喜訊,因而前兩個月,就將妾室們的避子湯停了,孔孺人就有了一個多月的子,還真是……有福氣啊。
攝政王的角勾了起來,回對大管家東方浩道:“賞孔孺人妝花緞十匹、玉如意一對,百嬰杯一套。全府下人打賞。”又看向一旁的小丫鬟,淡聲問,“此等喜訊,你為何不先報與王妃,而是在此等本王?”
小丫鬟一怔,結道:“啊,是、是、是因為……”
攝政王面一凝,冷聲道:“不敬王妃,杖二十,流放北疆。”這等想越過王妃報訊的丫鬟,必然是了孔孺人的指使,只是攝政王現在不可能去置孔孺人,但是杖責小丫鬟,而且還是由他親自置的,就是側面告誡整個攝政王府的人,不論誰,不論立了多大的功勞,也別想越過王妃去。
攝政王吩咐完畢,就背負雙手,悠然地往主院而去,攝政王妃跟在他邊半臂遠,角不自地飛揚起來,聽到喜訊卻沒有去孔孺人,也是打了孔孺人的臉了。想到王爺如此敬重自己,護著自己,可是自己卻不能為他誕下嫡子,攝政王妃的心qíng頓時又變得沉甸甸的。
……
“那就依卿家所言,選蘭慧云為皇后吧。”太后滿意地頜首道。
終于讓太后滿意了,禮部尚書及一眾員這才松了一口氣,躬退了出去,開始準備冊封大典。
待宮殿之靜了下來,太后便陷深思,放出風聲之后,原以為攝政王會立即行,哪知一晃過了兩月余,展眼秋了,攝政王那邊還是沒有一點靜,“難道他之前沒有一點準備?”
魏公公不知如何回答這個問題,垂首聽著,太后又自言自語了幾句,緩緩地道:“去……”
Advertisement
話未說完,就聽得殿外傳來焦急地腳步聲,魏公公的徒弟匆匆跑進來跪稟道:“太后,蘭國公夫人使了送信宮,言道蘭世子和蘭七公子被抓了。”
“什麼!”太后驚得騰地一下站了起來,“怎麼會……是哪里派人來抓的?”
“回太后話,是大理寺下的拘票。”
“去,立即到大理寺問清楚,到底是什麼罪名,另外,宣定國公及夫人覲見。”
“稟太后,定國公府已被重重包圍,不許任何人等出了。”
太后只得另下指令,“宣李大人、秦大人、趙大人宮。”
小太監著頭皮道:“稟太后,這幾位大人都、都被抓大理寺了。”
太后震驚得無以復加,瞪大眼睛看著眼前跪著的心腹太監,好半晌才緩緩地吐出一口氣,咬牙切齒道:“必定是攝政王!”
魏公公對此卻心存疑,“若是攝政王爺為何不直接對著陛下來,而要對著您呢?他就不怕惹怒了您麼?”
太后睜大眼睛冷笑,“他!他恐怕已經知道,哀家手中的證據都已經被毀了,本不可能將良太妃如何,才這般斬斷哀家的手足,他日后才好對付陛下。”
原本太后是讓葛太醫保留了端妃所有的脈案,可是沒有想到,葛太醫竟會毀了脈案,潛逃出京,一直追殺,卻連個人影都瞧不見,好不容易打聽到葛太醫被押解京,忙派了暗衛去劫人,到了地兒,暗衛發覺葛太醫已經被人殺死了,只得掩埋了葛太醫的尸。恐嚇良太妃,算計著攝政王為了不使當年的事qíngbào,必定會對小皇帝不利,極有可能帶兵bī宮,連救援的人都已經安排好了,只等攝政王殺了小皇帝,就帶兵殺了攝政王,扶弱的康王登基。康王的子如何,太后是最清楚的,活不過兩年了,但是康王妃年初誕下了嫡子,就能以太皇太后的份,扶稚兒登基,垂簾聽政了。
小士: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托啦 (>.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2785 章
邪君的醜妻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还他一针!人再犯我,斩草除根!!她,来自现代的首席军医,医毒双绝,一朝穿越,变成了帝都第一丑女柳若水。未婚被休,继母暗害,妹妹狠毒。一朝风云变,软弱丑女惊艳归来。一身冠绝天下的医术,一颗云淡风轻的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棋子反为下棋人,且看她素手指点万里江山。“江山为聘,万里红妆。你嫁我!”柳若水美眸一闪,“邪王,宠妻……要有度!”
512.9萬字8 45021 -
完結13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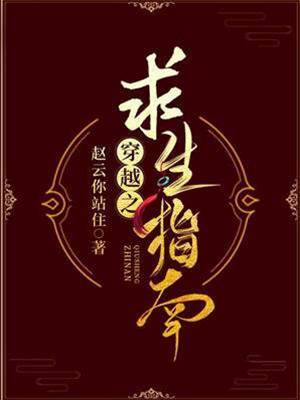
穿越之求生指南
同樣是穿越,女主沒有金手指,一路艱難求生,還要帶上恩人家拖油瓶的小娃娃。沿街乞討,被綁架,好不容易抱上男主大腿結果還要和各路人馬斗智斗勇,女主以為自己在打怪升級,卻不知其中的危險重重!好在苦心人天不負,她有男主一路偏寵。想要閑云野鶴,先同男主一起實現天下繁榮。
34.7萬字8 6919 -
完結597 章

傻妃帶崽要和離
傻子公主被迫和親,被扔到西蠻邊陲之地。所有人都認為她活不久,可沒想到,五年后……她不僅回來了,還帶回來一個奶兇的小團子,再嫁將軍府。“一個被蠻人糟蹋過的女人,還帶著一個小野種,真是將軍府的恥辱!”誰知將軍惶恐,跪搓衣板求饒:“娘子,我兒子……都長這麼大了。”
106.1萬字8.18 48686 -
連載2178 章

替姐出嫁後,錦鯉農女逆襲了
荒年,任家一車糧食就將宋九換走,成了任家傻兒子的媳婦,都說傻子兇狠殘暴還咬人,咬一口就得病幾日,世人卻不知,傻夫有三好:相貌好、身材好、體力更好。 錦鯉體質的宋九,嫁到任家就成了團寵,好事一樁連一樁,任家生活也越過越好。 隻是她這個傻夫身份卻變得不簡單,親生父母來相認,爹不疼娘不愛?沒關係,宋九護短疼丈夫。鬥極品虐渣渣,帶著傻夫發家致富,誰也別想欺負他。 宋九:“榮長隻有我能欺負。” 任榮長:“隻有媳婦能欺負我,其他人都不準欺負我媳婦。”
404.1萬字8.33 477841 -
完結51 章

讓你展示法術,你直接禁術起手?
天道網游降臨與現實融合,怪物橫行。藍星進入全民轉職的時代,通過獵殺怪物,不斷升級,獲得裝備,強化自己。 地球穿越者:薛江,在轉職當天不僅成功覺醒職業,還驚喜的發現自己開啟了禁術系統。 “叮,恭喜您提升了等級,請選擇您的禁術獎勵!” 生生不息,直到將對手燃燒殆盡的火屬性禁術:地獄炎照? 足以毀滅一座城市的大范圍雷屬性禁術:雷葬? 能夠將對手冰凍,瞬間完成控場的冰屬性禁術:絕對零度? “不玩了,我攤牌了,其實我這個入是桂!” 于是,薛江直接開啟不當人模式。 野外小怪?秒了! 遇到boss了?秒了! 地獄級領主?秒秒秒! 沒有什麼是薛江一發禁術秒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再來一發。 這個時候,就有網友質疑了: “薛江薛江,你那麼牛逼,有本事你把小日子過得還不錯的島國秒了。” 那一天,島國人民仰望著天上逐漸構成的法陣,終于想起了被支配的恐懼。
8.7萬字8 13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