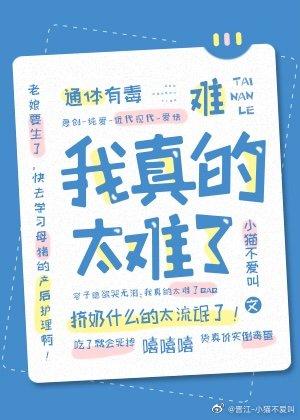《炙吻暗潮》 第1卷 第77章 時宴禮哄妻大法好
萬籟寂靜,天空灰蒙蒙。
一輛黑的賓利停在瑰園居的門口。
駕駛座的車窗搖下,冷白指骨夾著一煙搭在外面,男人冷峻的臉一般被火映得猩紅,一邊則藏匿在黑夜的影里。
而那被火映照的黑眸如一潭湖水深不見底,顯得那麼凌冽森,令人而生畏。
昨晚是趙雙條匆匆趕來告訴相佳豪喝醉了,時晏禮丟下了一桌的投資方老總直接離席。
姜晚笙的手機被秦風丟在了樓梯垃圾桶,撿到手機時,幾乎是憑著直覺,時晏禮直接上了八樓。
而吸引他推開安全通道那扇門的原因——門口的跡。
他的思緒很,很多東西在他的腦海中攪和著,覺得不對,但卻又不知道是哪里出了問題。
直到丟在副駕的手機鈴聲響起,是他的鬧鐘鈴。
七點了,家里的人兒也該醒了。
時晏禮推開了車門走了下去,他雙頰用力吸了最后一口煙了心的翻涌,將煙頭丟在地上,鞋底摁滅了星火。
再抬眸時,眼里已經恢復了平日里的清冷。
靜待了幾分鐘,直到上的煙味散去,他才朝家的方向走去。
輕輕推開了房間門,遠遠去那被窩隆起的一個小小的弧度。
他那顆堅的心一下了下來,眼里的冰霜也如春意盎然般頃刻間消融。
床上靜靜安睡的人兒呼吸極輕,白皙若冷瓷,那搭在被子外面的手腕纖細脆弱得可憐,好像稍稍用力便能將其折斷。
而那手掌心的繃帶已經溢出了跡。
就是這只的手,在昨夜承著風雨翻騰時,地抓住他的肩膀。
昨晚結束后。
懷里的人兒早已經昏睡了過去,而那手掌心的慘狀卻是令人心疼不已。
時晏禮是憑著自己的忍耐力,將手掌心的傷口理好,又給換了新的睡才將抱回到了主臥。
Advertisement
伺候好了小妻,才去將自己那一沾的白襯衫掉,洗了個冷水澡。
手掌心的氧意讓床上的人兒皺了皺眉,收回了手,殷紅的小微撅著似在不滿地嘟嘟囔囔什麼,扯過被子直接轉過了。
留給時晏禮的只有一個清瘦的背影,被子只蓋住了一半的,而那吊帶早在姜晚笙不安分的睡姿下溜到了腰間,那的蝴蝶骨,凹凸的腰線……
男人目灼灼,落在了那兩條纖細而勻稱的大長。
看似瘦弱,但攀著他腰時,又是那般的有力。
視線所之,便是那薄涼的所吻之。
冰涼的與灼熱的呼吸織在上。
夢中的人兒無意識,既是抗拒被擾清夢,又是順從著的本能朝那溫暖的懷抱去。
直到那溫熱落在了的耳垂,敏的戰栗終是化作一聲似貓般的嚀。
姜晚笙眨了眨惺忪的眼睛才看清自己所的環境,嗓音帶著剛睡醒的模糊問道:“怎麼了?”
還未等到回答,眼前便下一片影。
那雙近在咫尺的眼眸,深邃而暗涌著驚濤駭浪。
男人薄微勾,磁地說道:“早安,姜姩姩。”
只是你能想到這樣淡定說著早安的人,那指尖卻在肆意作?
人是記憶,憑著一些悉的覺,便能回憶起那些片段。
姜晚笙臉頰泛起兩道紅暈蔓延至耳后,手推搡著男人的肩膀:“別!”
“怎麼了?”時晏禮手臂撐在的兩側,饒有興致地欣賞著小妻姣好的素,挑了挑眉:“嗯?”
不好意思地別開了視線,櫻微張似言又止,半晌才輕聲道:“疼。”
許是無措,那卷而翹的睫眨了眨,在眼臉上投下了一片弧形的影,像蝴蝶的翅膀。
Advertisement
時晏禮眸底的玩味大片地漫開,直到腔發出了一陣悶悶的低笑,薄勾起一抹弧度:“抱歉。”
“難自控。”
姜晚笙第一次見時晏禮笑得這般快意,不有些看傻了眼。
但還是架不住被取笑的惱怒,掄起拳頭朝他口捶了一下,嗔道:“滾啊!”
這一拳對于時晏禮來說不痛不,但姜晚笙卻忘了自己用的是傷的手,疼痛讓倒吸了一口涼氣。
時晏禮心里一,小心翼翼地將那小手握在了手心,眉頭皺:“疼嗎?”
看著男人疚而又張的模樣,姜晚笙抿,放低了語氣寬道:“沒事的。”
為了證明真的沒事,還晃了晃小手。
實在可。
但時晏禮卻愈發疚,他埋頭在小妻的頸窩,啞聲道:“抱歉,我那晚語氣重了。”
不提到這個還好,提到這個。
姜晚笙瞬間變了臉,不知道哪來的力氣直接推開了男人,直接從床上站了起來:“時晏禮!你那天晚上兇什麼!”
時晏禮沒有一點防備,直接被一力量推到了一邊。
他平躺著,以一種難以置信的神仰視著眼前氣勢洶洶的人兒,喃了好幾句“我”……
都不好意思說出自己那晚吃了周凜城的醋。
昨夜的委屈讓姜晚笙一下惱火了起來,抬腳踹了男人的大,橫眉冷對道:“說啊!”
“嘖?”
時晏禮手擒住了那纖細的腳踝,不不慢地挑了挑眉梢,揶揄道:“姜姩姩,行啊,第二次婚姻暴力啊?”
腳踝被抓住,姜晚笙踉蹌了一下,手扶住墻壁才堪堪地穩住。
一時的惱火令口不擇言:“那又怎麼樣?要離婚嗎?”
“反正時總最近也不回家,特別熱外面的酒店,模特,我就騰了這個位置?”
Advertisement
“外面的鶯鶯燕燕那麼多都搶著時夫人這個位置不是嗎?”
長期抑的緒在此刻徹底發,姜晚笙掙開了那只手的錮。
徑直地走向柜拿出禮盒袋子朝床上的男人扔去:“給你!互不相欠!”
禮盒就這樣直接砸在了時宴禮的口。
“嘶。”他了被砸的口,而禮盒倒在床上,里面的布料已經出了一點點。
一個念頭在腦海中逐漸浮現...
他指尖輕地將袋子里折的整整齊齊的襯衫勾了出來,領口的刺繡不,一看便是生疏的手藝。
正是這樣,才讓人更加會到其中的心意。
這幾天的鬼鬼祟祟行為一下得到了答案。
時晏禮既是欣喜,也是疚,雜糅在心間,翻江倒海。
而站在床邊的人兒那漂亮的小臉板著著一慍,雙手環臂,瞧見他了過來便別開視線不去看他。
知道,話說過了。
但真的很生氣!
房間一時陷了沉默,如無聲的對峙。
時宴禮第一次低頭,為心上人。
他直起來靠在了床頭,出指尖勾住了小妻垂落在大側的小拇指,發覺沒反抗,才大膽地握住的手。
這個平日里氣勢傲然,叱咤商界的男人,此刻面對著生氣的妻子也是這般手足無措,
他將往自己的方向扯了扯,放低姿態哄道:“姩姩,我錯了。”
“你不生氣了好不好?”
“我……我只是吃醋,你和周凜城走那麼近。”
讓時晏禮承認吃醋,比殺了他還難,但老婆都要跑了?還有什麼面子可要?
周醫生?
姜晚笙想到了那通電話,確實那通電話很晚打來...
“我和周醫生的關系很單純,只是我還沒有想好要怎麼告訴你。”
我沒有做好準備,揭開老舊的傷疤,袒那些不堪。
因為……它仍在深夜作疼。
姜晚笙坐在了床邊,心里郁郁,下意識地咬了咬,萬千糾結與思慮都堆在心頭,于眉間。
頃
那骨節分明的指尖落于的眉間輕輕平,又了的臉頰,作親昵。
“笙笙,我們還有好多時間,有些話不需要一天說明白。”
時晏禮眉眼含,指骨輕蹭上的結痂作又輕了幾分,
間滾了滾,終是頃啄了啄的角,忍而又深地問道:“笙笙,不離婚好不好?”
“飯我做,錢我賺,卡你刷。”
“好不好?”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177 章

陸公子的緋聞女友
娛樂圈新晉女神南初的幕后金主被曝光——江城首富,低調神秘的陸公子。 媒體記者面前,他公然牽起南初的手:“南初是我養的。” 整個江城嘩然……人紅是非多,南初的黑歷史被人挖出時,陸公子選擇視而不見。 醫院里,醫生拿著妊娠證明:孩子六周,要還是不要。手術臺上,陸公子趕到:南初,你要弄死我的兒子,我就弄死你。 南初卻笑:一命抵一命,這樣才公平。情節虛構,請勿模仿
347.6萬字8.08 75653 -
完結809 章

替嫁傻妻:厲少寵爆全球
蘇甯暖,蘇家隱形大小姐,智商只有5歲的小傻子!傻乎乎滴代替妹妹嫁給了厲家二少爺——個醜陋,殘廢,還暴虐成性的短命鬼。 小傻子配短命鬼,絕配! 可是,這傻子少夫人怎麽畫風怎麽不對? 氣翻心機繼母,碾壓綠茶妹妹,巧削惡毒傭人,狂扁腹黑反派! 反派們壹個個痛心疾首:說扮豬吃老虎那是侮辱了蘇甯暖,她是壹個小傻子攆著壹圈反派大佬無處可逃! 厲景沈壹把把小嬌妻擁入懷中:我慣的,怎麽了?
145.3萬字8.18 230558 -
完結682 章
娛樂圈頭條
從馮家的千金,重生成家境貧困,一心一意想要憑藉美貌進入娛樂圈的新人。
151萬字8 9224 -
完結10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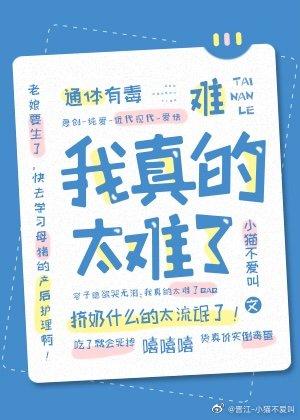
坑過我的都跪著求我做個人
容子隱是個貨真價實的倒黴蛋。父母雙亡,親戚極品,好不容易從村裏考出來成為大學生,卻在大學畢業的時候路被狗朋友欺騙背上了二十萬的欠債。最後走投無路回到村裏種地。迷之因為運氣太差得到天道補償——天道:你觸碰的第一樣物品將會決定你金手指方向所在,跟隨系統指引,你將成為該行業獨領風騷的技術大神。容子隱默默的看了一眼自己手邊即將生産的母豬:……一分鐘後,容子隱發現自己周圍的世界變了,不管是什麽,只要和農業畜牧業有關,該生物頭頂就飄滿了彈幕。母豬:老娘要生了,快去學習母豬的産後護理啊!奶牛:擠奶什麽的太流氓了!最坑爹的還是稻田裏那些據說是最新品種的水稻,它們全體都在說一句話:通體有毒,吃了就會死掉嘻嘻嘻。容子隱欲哭無淚:我真的太難了QAQ後來,那些曾經坑過容子隱的人比容子隱還欲哭無淚:我真的太難了QAQ,求你做個人吧!1v1,主受,開口就一針見血豁達受vs會撩還浪甜心攻注:1,本文架空!架空!架空!請不要帶入現實!!!文中三觀不代表作者三觀,作者玻璃心神經質,故意找茬我會掏出祖傳表情包糊你。2,非行業文!!!任何涉及各個行業內容,請當我杜撰!!!別再說我不刻意強調了,寶貝們~請睜大你們的卡姿蘭大眼睛好好看看我備注裏的感嘆號好嗎?內容標簽: 種田文 美食 現代架空 爽文搜索關鍵字:主角:容子隱 ┃ 配角:季暑 ┃ 其它:一句話簡介:我真的太難了
32萬字8 870 -
完結179 章

妥協
陸昀晏是只瘋狗。 拆了她的婚,傷了她的心。 她坐在他懷中紅著眼嬌笑。 “滿意了?” 再后來,陸昀晏死死拽著她的裙角:“歲歲,別不要我……” ——深情者被拿捏,愛能讓人低頭妥協。
28.5萬字8 18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